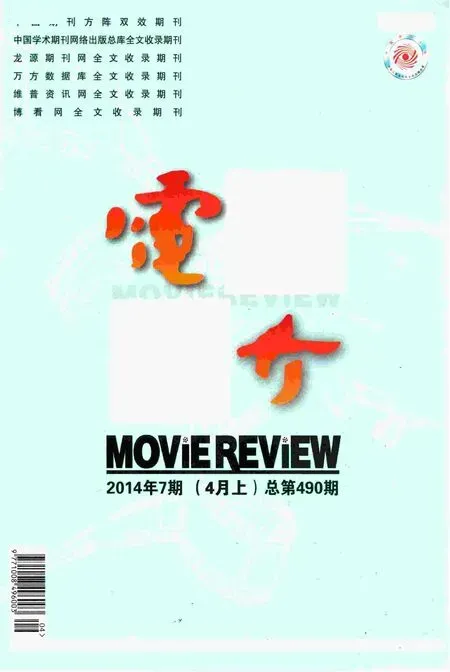賽珍珠英譯《水滸傳》評析
□文/李 新,遼寧醫學院外語教研部講師
張 宏,遼寧醫學院外語教研部教授

美國作家賽珍珠
賽珍珠,本名珀爾·布克(Pearl Sydenstricker Buck),是第一個因描寫中國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西方作家,也是將《水滸傳》推向世界的第一人。她曾被尼克松總統譽為“溝通中西方文化的人橋”。1927至1932年,賽珍珠用整整四年時間翻譯《水滸傳》(七十回本)全文,這是最早的英語全譯本。該譯本于1933年在美國紐約和英國倫敦同時出版,改書名為《四海之內皆兄弟》(All M en Are Brothers),在歐美風靡一時。然而,不幸的是,雖然賽譯本在西方享有盛譽,在中國未引起國內學術界的重視,甚至一度屢遭批判。自上世紀90年代起,中外學者開始呼吁客觀、公正、全面地評價賽珍珠的貢獻和價值。本文從生態翻譯學角度出發探究賽譯《水滸傳》,以期說明任一譯本都是其所處生態環境的產物,只有立足于譯本產生的生態環境,才能對譯者與譯本做出客觀、公允的評價。
一、賽譯《水滸傳》的生態視角
生態翻譯,是近些年發展起來的一種翻譯理論和研究方法,它受啟發于在當今社會大興其道的生態文明理論,主張從宏觀和微觀兩個視角關注翻譯活動過程的每一環節之間的聯系。生態翻譯學理論認為,翻譯生態環境是“原文、源語和譯語所構成的世界,即語言、交際、文化、社會,以及作者、讀者、委托者等互聯互動的整體。”[1]譯者是翻譯過程中一切“矛盾”的總和。翻譯就是譯者受翻譯生態環境中各種因素影響與制約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譯者不斷的進行適應與選擇。以生態學視角審視翻譯過程,譯者的重要作用表現在其與翻譯生態環境的關系問題上。譯者為何選擇這一文本進行翻譯、采用什么樣的翻譯策略、翻譯風格如何、翻譯目的是什么等等一系列問題的答案都隱藏在譯者所處的翻譯生態環境中以及譯者如何適應這一環境。從生態學視域研究并解讀賽珍珠的《水滸傳》英譯活動,不僅可以對譯者的翻譯活動作出全新的剖析,而且為這一理論的解釋力與可行性提供有力的佐證。
二、賽珍珠的雙文化身份
1892年賽珍珠出生在美國弗吉尼亞州,4個月后,隨傳教士父母賽兆祥和卡洛琳來到中國。賽珍珠一生中的前40年,除了回美國上大學四年和讀碩士學位外,基本上在中國度過。她從小和中國孩子一起玩耍、吃飯,有著和中國人一樣的飲食習慣,甚至先學會中文后學會英文。她不止一次表示,中文就是她的母語。在一位孔姓教書先生的指導下,她學習了大量中國古代經典著作,自己還偷偷閱讀許多中國小說,深受中國文化的熏陶。可以說,賽珍珠與中國人感情息息相通,在與中國朋友一起看戲時,她甚至情不自禁地為中國人大舉殲滅紅毛鬼子而感到歡欣鼓舞。近40年的中國生活經歷,使賽珍珠形成了中國式的思維方式,在文化心理上傾向于將自己看作一個中國人。正如她在一次演講中所說,“我生為美國人,從我的選擇和信仰上看,我是基督教;但是從我在一個國家生活的長短,從我的同情心和感情考慮,我是中國人。”[2]因此,賽珍珠的生活經歷使她獲得中西雙重文化背景,具有雙重文化身份。也正是東西方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構成了譯者英譯《水滸傳》的翻譯生態環境,兩種文化深植譯者骨髓,始終影響并制約著譯者的選擇與適應。
三、賽譯《水滸傳》的目的與風格
《水滸傳》是中國元末明初時代的一部百科全書,蘊含著極為豐富的中國古代文化,其中包含中國社會、歷史、政治制度、風俗習慣、禮儀和語言文化為一體的翻譯生態環境。具有雙重文化身份的賽珍珠生于美國,長在中國,精通漢語并癡迷于《水滸傳》引人入勝的故事情節和語言風格。賽珍珠在中國的生活經歷,雙語言、雙文化身份以及對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的研究,使其完全具備英譯這一中國古典文學巨著的能力;此外,該作品的政治內容對她的吸引力則更大。她十分清楚,中國歷史上的起義人士不管屬于哪一種人,也不論他們持有什么信仰,無一不喜歡《水滸傳》,毛澤東就是其中之一。翻譯之初,當時南京出售著《水滸傳》的好幾個版本,有的只有七十回,有的長達一百二十回。賽珍珠選擇的是七十回本的《水滸傳》,她認為這個版本最好,因為較長的版本結尾大多是好漢們被朝廷招安,而七十回本則自始至終貫穿著與官府反抗到底的思想。因此,譯者對《水滸傳》這一文本的選擇既是原文本對譯者素質和能力的適應與選擇,也是賽珍珠對原文本所構建的翻譯生態環境適應和選擇的結果。從賽珍珠的翻譯目的來看,她希望將一個真實的中國介紹給西方,改變西方人心目中被扭曲和丑化的中國人形象。
譯者的翻譯目的決定其采用的翻譯策略。據賽珍珠本人介紹,她說,“我盡可能做到直譯……保留原作的內容及寫作風格,甚至對那些即使在原文讀者看來也較為平淡的部分也未作任何改動……原文中的那些打油詩也照譯成英文的打油詩。”[3]因此,她幾乎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原著的表達方式和語言結構,保羅·多伊爾著的《賽珍珠》評傳中引用了評論家菲利斯·本特利對賽氏寫作風格的評述:“她追求的效果是,將中文變成對我們具有相同意義的語言。(她的文體)莊嚴、恬靜,使用透著尊貴的《圣經》體語言。賽珍珠甚至無需提高嗓門,亦能表達出最深沉和最輕松的感情。”[4]
結語
作為英譯《水滸傳》的第一人,賽珍珠無疑為東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然而無視譯本產生的特定翻譯生態環境,就將其當作翻譯技巧的反面例證大加鞭撻,則有失公允。只有立足于一定的社會歷史時期,從譯者的生活經歷、教育背景、宗教信仰等方面出發,才能系統而全面的深入研究譯者的翻譯實踐活動。對賽珍珠英譯《水滸傳》的生態解讀,有助于我們克服對文學翻譯的片面認識,不再局限于語言層面上的咬文嚼字,還原譯者從事翻譯活動的生態環境,可以幫助我們深入探究每位譯者選擇不同翻譯策略的背后原因,進而對譯者做出客觀、公正的評價。
[1]胡庚申.生態翻譯學的研究焦點與理論視角[J].中國翻譯,2011(2):5-9.
[2]馬鐵.賽珍珠英譯《水滸傳》的文化闡釋研究[D].華東師范大學.2006.
[3][4]馬紅軍.為賽珍珠的“誤譯”正名[J].四川外國語學院學報,2003(3):122-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