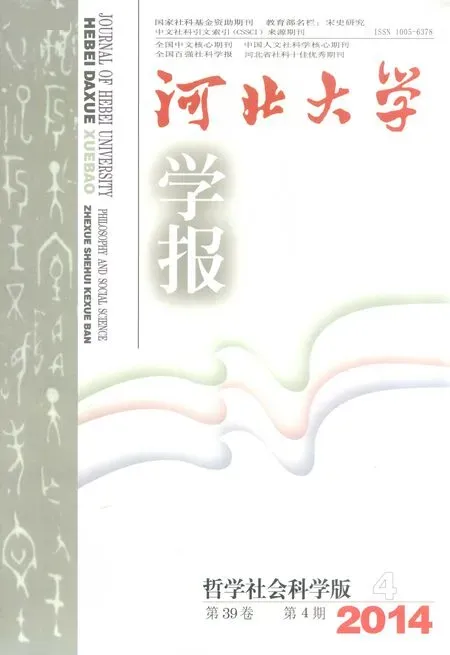宋代人地關系發展變化的幾個特點
王素美,王麗歌
(1.河北大學 文學院,河北 保定 071002;2.河北大學 宋史研究中心,河北 保定 071002)
宋代是中國古代人地關系發展的重要時期,以徽宗大觀三年(1109年)為例,全國著籍戶數為2 088萬,人口數量大約超過1億,墾田面積最高值為8億畝[1]66,兩者都是前所未有的。宋代人地關系在繼承前朝發展的基礎上又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本文試對此進行論述。
一、戰爭推進宋代人地關系的階段性變化
克勞塞維茨說“戰爭無非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2]43,而政治又與經濟緊密相連。戰爭,往往會阻礙社會發展的進程,宋代就是這樣。宋與遼、金、蒙元之間的戰爭破壞了人口和經濟發展的持續性,人地關系的發展也出現了階段性曲折變化。
北宋前期,是人地關系的恢復階段。經過唐末以來的百年紛爭,中國人口與耕地遭到了嚴重破壞。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是人地關系恢復階段。北宋建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政治環境仍然不穩定,直到景德元年(1004年),宋遼澶淵之盟簽定,才走上了真正意義上的和平發展之路。據《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九之七〇載,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全國有4 132 576戶。到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戶數增長到8 677 677,約增長了1倍多,但還未超越漢唐時期人口最高值(若以戶均五口計的話,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全國人口數量約為43 388 385口,而漢、唐時期人口數量最高值分別為59 594 978口、52 919 309口)[3]2285。同時段的墾田面積,也由3.1億畝增長到5.2億畝,增長了近68%[4]57。這些數字表明戰亂過后,北宋前期的人口與耕地正處于恢復之中。
北宋中期與北宋后期,是人地關系持續發展階段。經過前期三朝的恢復,從仁宗朝開始,宋代人口和社會經濟逐漸恢復到漢唐水平,并發展到新的高峰。仁宗皇祐二年(1050年),全國有10 747 954戶,約53 739 770口,已經相當于漢唐時期最高值[3]4037。和平安定的政治環境促進了人口的持續增長與耕地面積的擴大,到徽宗大觀四年(1110年),全國著籍戶數為20 882 258[5]2095,與至道三年相比,增長了4倍多。而墾田面積,若按照漆俠先生的推算方法,筆者將元豐五年開封府界、河北等5路的原有墾田和清丈墾田進行比較,[1]65得出全國實際墾田為9.6億畝,折今約8.5億市畝(漆先生計算的結果是8億多宋畝,折今7.2億市畝,值得商榷),近乎于至道二年的3倍,可見北宋時期耕地面積有了顯著增加。除此之外,北方諸路還修建了許多水利工程,農業生產有了保證,從而帶動了經濟發展。例如向來土曠民稀的京西路,“寶元、康定間,特輕其賦,募民墾辟。歲久,地無遺利,而民益富”[6]卷23《葛文康公神道碑》,逐步擺脫貧困落后面貌。
兩宋之交到南宋初期,是人地關系遭受嚴重破壞階段。雖然北宋中后期人口與耕地有了很大增長,社會經濟有所發展,但欽宗靖康元年(1126年)金軍大舉侵宋打破了人地關系發展進程。戰爭造成了許多地方人口減少,田地拋荒,淮河流域受到的破壞最嚴重。建炎四年(1130年),淮南“民去本業,十室而九,其不耕之田,千里相望,流移之人,非朝夕可還。”[7]615“自鄂渚至襄陽七百里,經亂離以后,長途莽莽,杳無居民”[8]880。長江以南地區也在劫難逃,如“江西一路,自經兵火殘破之后,又經旱災,人戶凋耗,雖去年稍得豐稔,人戶未盡歸業,田土荒廢尚多”[9]932。若按吳松弟先生估測,北宋末宣和七年(1125年)至南宋初紹興五年(1135年)這十年間,南方人口約減少了25%[10]359,人地關系發展嚴重受挫。到紹興十一年(1141年)宋金和議簽定后,南宋境內戰事才基本結束,人口與社會經濟才得以進入恢復階段。
紹興和議簽定后至南宋后期宋蒙戰爭前,人地關系再次進入恢復發展階段。南宋高宗政權偏安一隅,與金簽定紹興和議,暫時獲得了和平安定的政治環境。在孝宗、光宗、寧宗三朝,長江以南地區人地關系得到了恢復發展。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南宋著籍戶數為11 584 334[11]6365,除淮南、荊湖北路、京西南路外,南方其它地區已基本恢復到北宋崇寧年間水平。兩浙路、江南東西路、福建路、成都府路、潼川府路人稠地狹矛盾加劇。福建路“嶺阪上皆禾田,層層而上至頂”[12]。臺州“寸壤以上未有萊而不耕者也。”[13]7389許多地區還出現了圍湖造田高潮,“隆興、乾道之后,……陂湖之利日朘月削……三十年間,昔之曰江、曰湖、曰草蕩者,今皆田也。”[14]卷13《論圍田札子》原來人煙稀少的淮南、湖南、兩廣和四川的利州路、夔州路,也因為人口增加,大量天荒地被開墾,不同程度的緩解了地廣人稀局面。如廣南西路,北宋元豐元年時墾田不到500頃[4]57,到南宋初年,僅桂州一地墾田數就達1萬多頃[7]400。珠江三角洲流域和湖南洞庭湖地區正是在這個時候進入開發的,為明清成為全國糧食生產基地奠定了基礎。
南宋后期,人地關系發展再次遭受戰爭破壞。從理宗寶慶三年(1227年)蒙古大軍攻入利州路開始,之后的七八年間,蒙軍入蜀,四川地區遭受了有史以來最大浩劫,人口數量劇減,軍民“死傷殆盡,千百不存一二”[15]卷20《史氏程夫人墓志銘》,昔日天府之國變成人煙稀少之地,這也是南宋后期人口數量下降的主要原因。之后,福建路、廣南東路、淮南西路、江南西路、荊湖南路,也遭受了戰爭的侵擾,人口有所減少。在南宋后期的這五十年時間里,即理宗、度宗、恭帝三朝,人地關系發展再次因戰爭而受挫。
如上,宋代人地關系的發展就是這樣因戰爭的原因不斷被打斷,社會經濟也出現了同樣曲折向前發展的局面。這說明人地關系在社會經濟的發展中起到重要的甚至基礎的作用,而戰爭是宋代這些經濟關系中的重要拉力和杠桿。在整個人類社會中,我們必須認識到戰爭對人地關系與社會經濟的破壞作用,盡量避免戰爭,營造和平環境以促進人地關系與社會經濟的發展。
二、宋代人地關系呈現出明顯的地域性差異
宋代人地關系發展不但具有階段性、波動性變化的特點,因自然環境多樣、人口與耕地分布很不均衡等,人地關系也呈現出明顯的地區性差異。
南北差異。以秦嶺——淮河一線為界,在宋以前的絕大部分時間里全國的經濟重心和人口重心都在北方,無論是人口數量或是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北方都明顯的占有優勢。但“安史之亂”后,北方藩鎮割據下戰亂頻繁,出現了大規模北民南遷浪潮,南方地區人口快速增長,社會經濟也因此迅速發展。到宋太宗時期,南方人口比重超過北方,之后南北方人口比重基本保持在3∶2左右[16]397-398。根據北宋元豐年間南北方主要區域的人口與墾田數據,南方兩浙路、江南東路、江南西路、荊湖南路、荊湖北路、福建路戶數之和為6 765 986,比北方開封府、京東路、京西路、河北路、陜西路、河東路戶數5 676 597多了近20%,南方這幾路的官民田數為194 796 774畝,比北方143 175 394畝多了37%,戶均墾田數南方為30.3畝,也比北方27.7畝/戶多了2畝以上[17]68。可見,在人地比率上南方更具優勢,人地關系發展也更具潛力。
尤其是東南地區,從北宋中后期開始“吳、越、閩、蜀,地狹人眾”[18]601,元豐元年江南的人口密度為15.4戶/平方公里,已經超過河北,位居全國首位,詳見下表。南宋孝宗時,人稠地狹矛盾加劇,這些地方幾乎集聚了全國3/4的人口,長江中下游地區已然成為人口發展的重心。沉重的人口壓力,促使農業生產走向集約化,而且手工業和商業也得到了發展,社會經濟商品化水平明顯高于其它地區。
如上可見,宋代南北方地區在人口比重和人地比率上的發展態勢已經不同于以往,南方人地關系發展勢頭超過北方。

宋代各區域人口密度(戶/平方公里)
東西差異。宋代人地關系的發展不但具有南北差異,東部與西部地區之間也有很大差異。漆俠先生對宋代經濟發展西不如東問題曾做具體論述,他認為“如果以峽州為中心,北至秦嶺,南達海南島這一南北線的右側,包括成都府路、利州路、梓州路、夔州路、荊湖南路的西部以及廣南西路”,為宋代的西部地區,除成都府路的人口堪與東方諸路相比之外,其余諸路都地廣人稀,農業生產落后[1]76。人地關系發展也存在這樣的東西差異。經五代戰亂后,宋代西部關中地區已經完全喪失了漢唐時期的人口與經濟發展優勢,因此,若把漆先生所劃的這條分界線向北延伸,即將太行山——巫山——雪峰山串連成線,北宋元豐年間,此線以東至大海的這片區域視作東部地區,即開封府、京東路、河北路、淮南路、兩浙路、江南東路、江南西路、荊湖南路、福建路、廣南東路等10個行政區域,因為地勢海拔較低,平原廣闊,生存環境較為適宜,平均人口密度較高,約為10.9戶/平方公里;此線以西至北宋西部邊界的這片區域視作西部地區,即京西路、陜西路、河東路、湖北路、成都府路、利州路、夔州路、廣南西路、梓州路等9個行政單位,地勢海拔較高,多高山峽谷少平原,平均人口密度較低,約為5.5戶/平方公里,詳見上表。又據《文獻通考·田賦考》中所記載的元豐年間的墾田數據,東部地區每平方公里平均墾殖指數約為310畝;西部地區每平方公里平均墾殖指數約為123畝(梓州路因多為山地,難以頃計,無法計算墾殖指數)[17]68。由此可見東部與西部地區在人口密度和土地開發利用上的巨大差距,西部的人地關系發展水平明顯不如東部地區。
此外,成都府路和潼川府路雖然也位處西部,但豐厚肥美的成都平原為人口和經濟發展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一直人煙稠密。到南宋末期蒙軍進攻前,這兩路的人多地少矛盾突出,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堪與東部江浙、福建等地媲美,是有別于西部其它地區的一個特殊區域,并且人口和耕地分布出現了由盆地底部向盆地邊緣遞減的狀況。這就是說,同是西部地區,也有同中有異的情況,不可一概而論。
如上,宋代人地關系發展的南北差異說明了漢唐以來以北方為人口和經濟發展重心的格局被扭轉,南方人地關系出現蓬勃發展勢頭。長江中下游地區人多地少矛盾非常突出,中國由此進入了以南方地區開發為重點的新時期。宋代人地關系發展的東西差異,造成了東部與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差距。東部地區人稠地狹,促使人們不斷改善生產工具,提高生產技術,精耕細作式生產,從而使人多地少矛盾得到緩解,經濟得到發展,社會不斷進步。西部地區地廣人稀,由于勞動力匱乏和生產技能低下,人們刀耕火種,生產力發展水平遠遠落后于東部地區。無論宋代還是今天,東西差距依然非常明顯。西部地區、西北地區應不斷學習和借鑒東南地區的經驗并依據自身的區域特點調整人地關系,積極實行改造。
三、自然環境與宋代人地關系的雙向交互影響
所謂自然環境對宋代人地關系的交互影響,是說自然環境的開發與利用對宋代人地關系的發展產生了正面作用,又造成了負面影響。如何合理改造與利用自然條件,是人地關系發展的關鍵性問題。
人們對自然環境的改造和利用,促進了經濟發展。因為人在人地關系中具有主動性,而人類主觀能動性的增加主要表現在對自然環境改造、利用能力的增強和對地理環境認知水平的提高,所以無論是地少人多地區,還是地廣人稀地區,人口數量的增長和生產技能的提高都提升了人類開發、改造自然的能力,推動了人地關系發展。
首先,在地少人多的地區,宋代人為了緩解生存壓力,除了控制生育、限制人口數量、移民外遷外,最主要的措施就是想盡辦法擴大耕地面積,改良土壤,提高耕作技藝,優化農作物品種,調整種植結構、提高復種指數等。例如江浙、福建等地,生活在山區丘陵地帶的人們除了營建梯田外,還推廣麥作,引進占城稻等適宜當地種植的糧食物種,不但豐富了農作物種類,還實行稻麥復種、稻稻復種,將農業生產普遍提升到兩年三熟制或一年兩熟制。在平原或沿湖、濱海地區居住的人們,除了精耕細作外,還創建圩田、沙田、淤田等,不但擴大了耕地面積,獲得了旱澇保收的肥沃良田,還大大增加了糧食產量。并且,人們充分利用靠山或沿海的地理條件,因地制宜,發展山區經濟作物種植業、采礦業、手工業和商業等,或進行海外貿易,既解決了農業剩余人口問題,又推動了地區經濟發展。
其次,在地廣人稀地區,雖然崎嶇復雜的地理環境和干旱少雨的氣候加大了人們生存和發展的難度,但勞動力的增加和入遷移民帶來的先進技術,使西部地區開發得以擴大。例如廣南西路,通過屯田、營田方式,許多宜農荒地得到了開墾。占城稻、豆、麥等物種的傳入,使兩廣糧食產量明顯增加,到了南宋廣南西路已有大量余糧輸往福建等地[19]。在高山絕壑的地區,修建了許多水利工程。如紹興年間,雷州太守何庚興修水利,建造堤堰,使四千余頃東洋之田變成膏腴沃壤[20]卷82。以往播種之后,不管不顧的生產方式也發生了重大變化,人們開始培育秧苗,實施田間管理,為農業生產注入更多人力。雖然西部地區未能徹底轉變原始落后、地廣人稀局面,但在中國古代經濟發展史上卻具有重要意義。漆俠先生曾對此評價說:“宋代經濟除在全國各地區繼續發展外,有一個較為明顯的趨勢是向湘江以西的湘西和廣南西路這一西南方向發展”[1]78。只要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合理開發利用資源與環境,人地矛盾就會得到緩解,生產就會發展,社會就會進步。相反,則人地關系就會趨向緊張。
人與環境關系矛盾的緊張趨向。人口的增加,資源的過度索取和不合理利用給生態環境造成了沉重壓力。例如,開發山區,濫砍濫伐,引發了水土流失問題。針對宋代的林木毀壞情況,當時學者感嘆曰:“昔時巨木高森,沿溪平地竹木亦甚茂密。雖遇暴水湍激,沙土為木根盤固,流下不多,所淤亦少,開淘良易。近年以來,木值價高,斧斤相尋,靡山不童,而平地竹木亦為之一空。大水之時,既無林木少抑奔湍之勢,又無包攬以固沙土之積,致使浮沙隨流奔下,淤塞溪流,……由是舟楫不通,田疇失溉。”[21]卷上《淘沙》此外,圍湖、圍海造田行為,容易堵塞河流,使湖泊失去蓄水功能,擾亂當地氣候,增加了洪澇災害的發生幾率。長江流域,在唐代平均18年發生一次洪澇災害,宋代增加到平均每5、6年一次[22]445。太湖流域由于圍湖造田,導致水系紊亂,洪澇災害每2、3年發生一次[23]307。可見,人們不合理的生產活動是宋代以來自然環境惡化、災害頻發的一個重要原因。
由此可見,宋代人口數量的增長緩解了中國地廣人稀局面,江浙、福建、四川成都等地在人口壓力下,人的主觀能動性被進一步激發,從而推動了南方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但在人類謀求發展、積極改造自然的行為背后,由于不合理的開發和利用,使人與自然關系走向緊張,與前朝相比,宋代災害發生頻率的增加,就證明了這一點。
綜上所述,在宋代,無論是人口規模還是耕地數量,或是生產力發展水平,都因人地關系的復雜性呈曲折向前發展的特點,但它畢竟已超越前朝,引領后代。其人地關系演變所呈現出的新特點,開啟了我國人地關系發展的新時代。正如馬克思所說,“資本的祖國不是草木繁茂的熱帶,而是溫帶。不是土壤的絕對肥力,而是它的差異性和它的自然產品的多樣性,形成社會分工的自然基礎,并且通過人所處的自然環境的變化,促使他們自己的需要、能力、勞動資料和勞動方式趨于多樣化。社會地控制自然力以便經濟地加以利用,用人力興建大規模的工程以便占有或馴服自然力,這種必要性在產業史上起著最有決定性的作用。”[24]561宋代人口重心和經濟重心轉移到長江中下游地區,標志著宋之前以北方地區緩慢開發為重點的傳統農業時代的結束,及宋朝以后以長江中下游地區為重心的南方新農業經濟的開始。江浙、福建等地沉重的人口壓力和民眾為解決人多地少矛盾所做出的各種努力,可以說為明清以來新經濟因素的萌芽奠定了基礎。雖然東西部差距越來越大,但人地關系發展的步伐卻明顯加快,地區開發規模不斷擴大,有力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同時,也給人們諸多警示。人們在違背自然規律情況下的盲目開發和不合理利用,也會造成人口與環境關系的緊張,給日后環境惡化埋下了隱患。雖然宋代人地關系有宋代自己的特點,但就某種意義上來說,卻代表了整個中國乃至世界人地關系發展史上引人關注的一般意義和普遍意義。
[1]漆俠.中國經濟通史·宋代經濟卷[M].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9.
[2]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第1卷[M].上海:商務印書館,1978.
[3]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M].北京:中華書局,2004.
[4]馬端臨.文獻通考[M].北京:中華書局,2006.
[5]宋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7.
[6]周麟之.海陵集[M].臺北:文淵閣四庫全書,1986.
[7]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M].北京:中華書局,1956.
[8]洪邁.夷堅志[M].北京:中華書局,1981.
[9]李綱.李綱全集[M].長沙:岳麓書社,2004.
[10]吳松弟.中國人口史:第三卷[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
[11]徐松.宋會要輯稿[M].北京:中華書局,1981.
[12]范成大.驂鸞錄[M].臺北:文淵閣四庫全書,1986.
[13]陳耆卿.嘉定赤城志[M].宋元方志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0.
[14]衛涇.后樂集[M].臺北:文淵閣四庫全書,1986.
[15]虞集.道園學古錄[M].臺北:文淵閣四庫全書,1986.
[16]程民生.北方經濟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7]程民生.宋代地域經濟[M].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
[18]秦觀.淮海集箋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9]王麗歌,姜錫東.宋代福建與兩廣地區的糧食生產與調運[J].中國農史,2011(1):54-63.
[20]李賢.明一統志[M].臺北: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
[21]魏峴.四明它山水利備覽[M].臺北: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
[22]吳華林,沈煥庭.我國洪災發展特點及成災機制分析[J].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1999(4):445-451.
[23]楊世倫,陳吉余.太湖流域洪澇災害的形成和演變[J].地理科學,1995(4):307-314.
[2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