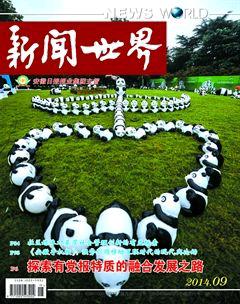淺析《愛彌兒》對當下生命教育的啟示
張旭 朱玲玲
【摘 要】本文就盧梭的教育哲理巨著《愛彌兒》中的生命教育思想進行淺要探析,試圖取長補短,理順當下生命教育的教學邏輯順序,突出生命教育的教學重點,豐富和完整生命教育的意義,促進生命教育的完備。
【關鍵詞】《愛彌兒》 生命教育 自然生命 人文生命
《愛彌兒》是盧梭的經典教育哲理巨著,以自然主義教育理念著稱,對后世教育思想理論的發展有著顛覆性的影響。不僅如此,書中無處不在的生命教育理念也啟迪人們追尋更加完備的生命教育,實現生命的完整與健全,進而擁有更加完美的人生。
一、《愛彌兒》內容概要
《愛彌兒》是法國啟蒙思想家、文學家、教育家讓·雅克·盧梭(1712-1778)所著,是其通過描述對愛彌兒的教育過程來反對封建教育制度、闡述他的資產階級教育思想的教育巨著。書中描述了盧梭扮演的教師對他構造出的學生——愛彌兒進行的有關成長每一階段的教育全過程。全書共分為5卷,主要包括體育教育、感官教育、智育教育、道德教育和愛情教育等幾個方面,重點表達了其自然主義教育主張,即人生來是自由的、平等的、性善的,只有在自然狀態下,每個人才能充分享受這份天賦的權利,所謂的文明社會正是人們失去自由、平等、善良的枷鎖。因此,為了改變這種不合理的狀況,他主張對兒童進行適應自然發展過程的“自然教育”,培育資產階級理性王國的“新人”。
整部著作中,盧梭在論述教育思想和追求的同時也折射出生命教育思想,這對學生的成長過程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愛彌兒》中的生命教育思想
1、生命的定義及生命教育的內涵
(1)生命的定義。伴隨著人類的發展,生命的含義也不斷豐富。在教育學里,生命,既指生物學意義上的肉體自然生命,亦指經濟學意義上的經濟生命,同時更加意味著精神領域的精神價值生命和社會生命。鄭曉江教授指出,“人不僅僅有自然生命,更有血緣的、人際的社會生命,還有精神的超越生命”。①這種區別于自然生命的精神價值生命、社會生命統稱人文生命,因而完整的生命,是自然生命與人文生命的統一。
(2)生命教育的內涵。“生命教育”的概念是1968年美國學者杰·唐納·華特士針對美國社會出現的毒品泛濫、藥品濫用以及艾滋病蔓延等諸多危及生命的不良現象首次提出并實踐的,緊接著又被澳大利亞、日本以及我國港澳臺等國家及地區逐漸推廣和發展。而區別于西方國家在教學中對預防艾滋、防范暴力、藥品濫用、性混亂等直接給予自然生命以預防和教育,亞洲的日本、我國的港澳臺和大陸地區,生命教育的內涵偏則偏重于對受教育者的心靈教育。
生命教育是指在教導學生獲取生命意識、保全自然生命的基礎上,幫助其發覺生命意義,發揮生命價值,助其成為身心健康、生命價值和意義得以實現的完整生命體的教育。從生命的構成來看,生命教育也就是讓學生的自然生命和人文生命和諧統一發展的教育,就是自然生命教育與人文生命教育的結合;具體來說,自然生命教育就是針對生命載體的教育,包括生命安全、飲食安全、交通安全、健康知識以及人的生和死的教育;人文生命教育包括生命的價值、意義、人生觀、生命觀及生命質量提升等的教育。②
2、《愛彌兒》中生命教育思想的體現
《愛彌兒》中,教師的教學實踐是隨時隨地、輕松自由地使愛彌兒獲取知識、啟發心靈的過程。具體來說,其中的生命教育思想主要體現在以下三點:
(1)“以生為主”的自然生命教育理念。《愛彌兒》中盧梭倡導的是“以生為主”的教育。他認為,“自愛始終是很好的,始終是符合自然的秩序的。由于每一個人對保存自己負有責任,因此,我們第一個最重要的責任就是而且應當是不斷地關心我們的生命”。③“如果他對生命沒有最大的興趣,他怎么去關心它呢?因此為了保存我們的生存,我們必須要愛自己”,“從這種情感中將直接產生這樣一個結果:我們也同時愛保持我們生存的人”。④他十分重視兒童的自然生命保存,并由此發揮人文生命的力量,愛人愛己,這與自然生命教育對生命安全、人的生與死的教育理念完全一致。
(2)“長篇巨幅”的人文生命教育傾向。盧梭除了在愛彌兒年幼時期給予的保存自然生命健康的體育教育外,隨著愛彌兒年齡的增長,他逐步在精神領域予以相應的教育內容,更加突出了自然生命保全之后,加強人文生命教育的重要性。并且,盧梭偏重于對愛彌兒內心價值世界的挖掘。這與生命教育中所倡導的關注自然生命的保全、強調人文生命的完善和升華不謀而合。并且,盧梭的教學設計也有著明顯的人文生命教育的傾向。他帶領愛彌兒來到鄉村,讓他在日常瑣事中感受生命、接受教導,這種圍繞著讓學生體驗生存感覺、培養生命意識、擁抱生命瞬間的課程設計都是在自然生命教育之后,強調人文生命教育的重要體現。
(3)“大寫的人”的最終培育目標。《愛彌兒》中盧梭通過教學設計,讓愛彌兒學會自己感受生命的生存感、需要感,明晰生命價值,進而對生命形成更高層次的理解、保護、尊重和創造,并最終成為“大寫的人”;而這,正是生命教育所期盼實現的教學培養目的。
三、《愛彌兒》對當下生命教育的啟發
1、當下生命教育實施現狀
在以“快”、“忙”為標簽的時代,人們失去了思索生命的時間,對生命的概念也逐漸變得模糊,加之近年來,國內外社會對踐踏生命的報道層出不窮,對生命、生命的方向、生命的價值與意義的探討,一度有所扭曲,生命教育的開展迫在眉睫。而在我國,生命教育事業生長的土壤仍然十分貧瘠,具體體現在:
(1)生命意識扭曲。早在2003年一篇題為《當代大學生生命意識狀況調查報告》的文章中就曾指出,當問及“遇到不順心的事情時有無自殺念頭”時,有32.20%的學生選擇了“有”,其中有6.80%的學生經常有自殺念頭;當問及“遇到他人冒犯時有無殺人念頭”,有34.60%的學生選擇了“有”,其中7.40%的學生經常有殺人的念頭。⑤大學生,作為高知群體,理應對生命有最起碼的認識與尊重,然而這一調查數據以及為人們熟知的“馬家爵案”、“清華朱令案”、大學生跳樓自殺等的發生都在不斷提醒教育工作者,當下學生的生命意識逐漸變弱,生命觀被不斷扭曲。
(2)引入時間短暫。相較于早在上世紀60 年代就開始將生命教育列為學校教育科目的美國、澳大利亞和日本,我國直到上個世紀90年代,才真正開始生命教育歷程,其中以港臺地區較為卓越。如臺灣,經過多年的探索,不僅在生命教育素材、網站建設上卓有成效,而且還舉辦了生命教育博覽會,成立了生命教育委員會,并將2001年確立為“生命教育年”。而大陸地區生命教育引入時間則較短。2004年遼寧省啟動了中小學生命教育工程,同年,上海市出臺《上海市中小學生命教育指導綱要(試行)》,而后的十年,國內其他部分省份和地區才陸續開展生命教育。
(3)開課現狀不容樂觀。由于“重學分輕育人”的教育思想根深蒂固,時至今日大陸開設生命教育課的學校較少,而部分開設生命教育課程的學校在教材建設、師資配備等方面尚未形成體系,生命教育一般僅穿插在安全教育、思想政治、心理健康等課程之中,生命教育被嚴重地弱化。并且由于傳統的以分數為考核標準的教學理念的影響,生命教育的教學成效往往被分數代替,如2005年復旦大學增設“生命教育”為2個學分的選修課。試圖通過修學分的方式來引導學生學習,這不僅扭曲了生命教育的教學意義同時也易使學生產生以通過考試為學習目的的錯覺。而任課教師由于受教學任務的局限,顛倒了以學生為主、將生命自由與成長還給學生的教學理念,使得教學缺乏自由、創新和實際成效。
2、《愛彌兒》對當下現狀的啟示
《愛彌兒》中充滿著盧梭的寄托,它讓自然主義教育理念生根發芽,同時其中包含的生命教育思想也促進了人們對其教育價值的不斷探討。但愛彌兒的結局并不圓滿,或許盧梭是在發泄他對所處時代的不滿,但這種發泄落于現實中則必須避免。因而,聯系現狀辯證地看待《愛彌兒》中的生命教育歷程,對推進當下生命教育走向完備具有重要意義,具體表現在:
(1)教學起點的糾正。盧梭以體育為教學起點,有利地保全了愛彌兒的自然生命,但他把自然生命與人文生命相分離的思想是不理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認為,人具有生存、享受和發展三個需要,三者之間是同時并存的。具體到生命教育教學中,生存需要即對生命的需要,是對自然生命和人文生命并存的需要。只有讓受教育者感受并擁有生命的需要,才能激發起其滿足發展需要的動力,才會讓享受需要成為可能;只有讓受教育者對生命具有需要,才能承擔起生存與發展;只有讓受教育者對生命加以肯定,才能在生存和發展的時候享受生命,最終獲得生命的健全和完整。因而在生命教育中,應全面的、從生命發展的全局進行教育,將自然生命教育與人文生命教育同步教學,糾正以自然生命教育為先的錯誤順序。
(2)教學重點的把握。在生命教育教學中,對生活能力的培育即自然生命教育,對生命能力的培育即人文生命教育,而目前生命教育的現狀就是人文生命教育處于次要地位并收效較差。這一點盧梭早在《愛彌兒》中就告誡我們要將生命教育的重點置于人文生命教育上,這必須是教學的重點。并且,他很好的用書中的教育體驗告誡到,學生應成為教學的主體,整個教學過程應以學生的實際需要和期望的效果為主,把生命教育的教學解放還給學生自己。
(3)教學終點的重塑。生命教育應以實現受教育者生活能力的保全、生命能力的健全、生命意義的完全與實現為終極目標,使受教育者的自然生命與人文生命真正完全與實現。□
參考文獻
①鄭曉江,《從生命教育興起的背景看中國生命教育的特色》[J].《思想教育理論》,2007(10):8-13
②何煥好,《論大學生人文生命教育與團隊心理訓練》[J].《華章》,2010(16):99
③劉莎莎,《從〈愛彌兒〉中探索盧梭的生命教育理念》[J].《阿壩師范高等學院學報》,2009(4):92-94
④盧梭三著,陳惟和等 譯:《盧梭民主哲學》[M].九州出版社,2004:261-262
⑤連淑芬、魏傳承,《當代大學生生命意識狀況調查報告》[J].《思想理論教育》,2007(2):61-65
(作者:張旭,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碩士研究生導師,副教授;朱玲玲,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2012級馬克思主義哲學專業研究生)
責編:姚少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