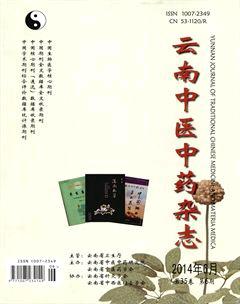乳腺癌術后中醫證型研究進展
貢麗婭 陳紅風
關鍵詞:乳腺癌術后;中醫證型;綜述
中圖分類號:R7379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7-2349(2014)06-0087-03
隨著醫學的發展,手術因其“祛邪”作用的直接性、快速性以及“根治”性,已成為針對乳腺癌實體腫瘤的首選治療方法。中醫藥參與乳腺癌的治療,已從古代重視乳巖的辨證,發展為現代重視乳腺癌術后的辨證,中醫藥在提高手術耐受性,改善手術、術后放化療及內分泌治療的副作用,提高患者生活質量以及預防術后復發轉移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辨證論治是中醫學的精髓,中醫證候規范化、標準化是中醫現代化的趨勢,是中醫現代化研究的重中之重。近年來,中醫“證”及證候規范化的研究已成為中醫界研究的熱點。乳腺癌術后中醫證型及證候標準化的研究,目前尚處于起步階段,已有學者從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進行了探索。廣東省中醫院林毅教授等根據多年臨床實踐提出將乳腺癌分圍手術期、圍化療期、圍放療期及鞏固期的分期辨證體系[1]。中醫藥參與乳腺癌的治療主要集中在圍手術期、圍化療期、圍放療期以及術后長達5年的鞏固期的治療,這就使仍以“實體腫瘤”治療為主旨的現行標準、規范遠滯后于臨床。乳腺癌術后是中醫藥參與治療較長的一個時期,乳腺癌術后辨證所使用的證候名稱及其概念都缺乏明確的內涵和外延,缺乏客觀的、量化的、可操作性強的證候分類標準,乳腺癌術后辨證分型不統一已經成為阻礙中醫藥參與到乳腺癌治療中的瓶頸問題。下面就乳腺癌術后中醫證型研究作一綜述。
1采用傳統中醫辨證研究
乳腺癌是全身疾病,中醫的整體觀和辨證論治在指導乳腺癌的中醫藥治療,尤其是乳腺癌術后的治療中越來越顯示出其特色。辨證論治是中醫學診治疾病的精髓,證是辨證論治的前提和基礎,是連接中醫理論和臨床診療體系的橋梁,長期以來,有關證候及證型規范化的研究一直是中醫界研究的主要方向和熱點。
劉勝等[2]參照鄧鐵濤主編《中醫證候規范》[3]及中國中醫研究院廣安門醫院主編《中醫診療常規》[4]的診斷標準,將407例乳腺癌術后患者進行辨證分型規律探析,臨床辨證為氣陰兩虛證384例(9435%)及沖任失調證331例(8157%)為多,氣血兩虛證22例(5141%),肝氣犯胃證79例(1941%),而氣陰兩虛伴沖任失調證型313例(7690%),亦有三證并存的情況。徐杰男等[5]參照湖南中醫學院中醫診斷研究所主編的《中醫病證治法術語》[6]及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頒布發行的《中醫病證診斷療效標準》[7]的診斷標準,將241例乳腺癌術后患者辨證為氣陰兩虛證者122例占5062%,氣血兩虛證者82例占3402%,沖任失調者138例占5726%,肝氣犯胃證者17例占705%,多證兼夾者112例。吳雪卿等[8]依照鄧鐵濤主編《中醫證候規范》[9]及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頒布《中醫病證診斷療效標準》[7]的診斷標準對108例乳腺癌術后患者進行辨證分型,氣虛證81例(7500%),陰虛證77例(7130%),血虛證25例(2315%),沖任失調證57例(5278%),肝氣郁結證37例(3426%),肝腎陰虛證22例(2037%),氣虛證、陰虛證二證相兼60例(5556%),氣虛證、陰虛證、沖任失調證三證相兼34例(3148%),從臨床研究來看,乳腺癌術后患者證情較復雜,常常出現多證相兼。
周家明等[10]觀察了117例乳腺癌術后經過放、化療的患者,根據中醫辨證分為肝郁氣滯證(8974%)、氣血虛弱證(5812%)、瘀血阻滯證(5556%)、津虧內熱證(4488%),其中有不少患者身兼數證。唐漢鈞等[11]對乳腺癌術后患者288例進行臨床觀察,認為術后辨證分5型:肝郁氣滯型;肝腎虧虛型,沖任不調型;脾失健運,氣血虧虛型;肺腎虧虛型,氣陰不足型;毒邪蘊結型。劉燕珠等[12]對乳腺癌術后68例患者辨證論治為肝郁氣滯型、氣血虛弱型及痰熱凝結型。劉艷紅等[13]對40例乳腺癌術后經放療、化療后的患者進行中醫辨證分型為肝氣郁結型、脾虛痰濕型、氣陰兩虛型及瘀熱型。萬華等[14]提出乳腺癌術后以腎氣不足、沖任失調、肝脾腎虛為本,以肝氣郁結、脾失健運、氣滯血瘀、痰凝結毒為標的觀點。王淑斌等[15]總結了賈占清教授的治療經驗,指出手術對乳腺癌患者生理、心理的打擊較大,可能會出現氣血雙虧的情況。陳麗等[16]通過文獻研究總結乳腺癌術前及術后的辨證分型,認為術后多出現脾氣虛、陰虛、氣虛血瘀水停型,以虛證為主。陳光群等[17]將100例乳腺癌術后患者辨證分型為脾胃虛弱78%、沖任失調48%、肝氣郁結23%、氣陰兩虛17%、瘀血內阻17%、痰濕8%。其中2證相兼65%,3證相兼13%。吳繼萍等[18]對105例乳腺癌術后患者的中醫證型進行研究,結果顯示乳腺癌主要涉及肝、脾、腎3個臟器,其中脾腎氣虛型28例,脾腎陽虛型15例,脾腎陰虛型25例,氣陰虧虛型37例。endprint
關鍵詞:乳腺癌術后;中醫證型;綜述
中圖分類號:R7379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7-2349(2014)06-0087-03
隨著醫學的發展,手術因其“祛邪”作用的直接性、快速性以及“根治”性,已成為針對乳腺癌實體腫瘤的首選治療方法。中醫藥參與乳腺癌的治療,已從古代重視乳巖的辨證,發展為現代重視乳腺癌術后的辨證,中醫藥在提高手術耐受性,改善手術、術后放化療及內分泌治療的副作用,提高患者生活質量以及預防術后復發轉移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辨證論治是中醫學的精髓,中醫證候規范化、標準化是中醫現代化的趨勢,是中醫現代化研究的重中之重。近年來,中醫“證”及證候規范化的研究已成為中醫界研究的熱點。乳腺癌術后中醫證型及證候標準化的研究,目前尚處于起步階段,已有學者從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進行了探索。廣東省中醫院林毅教授等根據多年臨床實踐提出將乳腺癌分圍手術期、圍化療期、圍放療期及鞏固期的分期辨證體系[1]。中醫藥參與乳腺癌的治療主要集中在圍手術期、圍化療期、圍放療期以及術后長達5年的鞏固期的治療,這就使仍以“實體腫瘤”治療為主旨的現行標準、規范遠滯后于臨床。乳腺癌術后是中醫藥參與治療較長的一個時期,乳腺癌術后辨證所使用的證候名稱及其概念都缺乏明確的內涵和外延,缺乏客觀的、量化的、可操作性強的證候分類標準,乳腺癌術后辨證分型不統一已經成為阻礙中醫藥參與到乳腺癌治療中的瓶頸問題。下面就乳腺癌術后中醫證型研究作一綜述。
1采用傳統中醫辨證研究
乳腺癌是全身疾病,中醫的整體觀和辨證論治在指導乳腺癌的中醫藥治療,尤其是乳腺癌術后的治療中越來越顯示出其特色。辨證論治是中醫學診治疾病的精髓,證是辨證論治的前提和基礎,是連接中醫理論和臨床診療體系的橋梁,長期以來,有關證候及證型規范化的研究一直是中醫界研究的主要方向和熱點。
劉勝等[2]參照鄧鐵濤主編《中醫證候規范》[3]及中國中醫研究院廣安門醫院主編《中醫診療常規》[4]的診斷標準,將407例乳腺癌術后患者進行辨證分型規律探析,臨床辨證為氣陰兩虛證384例(9435%)及沖任失調證331例(8157%)為多,氣血兩虛證22例(5141%),肝氣犯胃證79例(1941%),而氣陰兩虛伴沖任失調證型313例(7690%),亦有三證并存的情況。徐杰男等[5]參照湖南中醫學院中醫診斷研究所主編的《中醫病證治法術語》[6]及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頒布發行的《中醫病證診斷療效標準》[7]的診斷標準,將241例乳腺癌術后患者辨證為氣陰兩虛證者122例占5062%,氣血兩虛證者82例占3402%,沖任失調者138例占5726%,肝氣犯胃證者17例占705%,多證兼夾者112例。吳雪卿等[8]依照鄧鐵濤主編《中醫證候規范》[9]及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頒布《中醫病證診斷療效標準》[7]的診斷標準對108例乳腺癌術后患者進行辨證分型,氣虛證81例(7500%),陰虛證77例(7130%),血虛證25例(2315%),沖任失調證57例(5278%),肝氣郁結證37例(3426%),肝腎陰虛證22例(2037%),氣虛證、陰虛證二證相兼60例(5556%),氣虛證、陰虛證、沖任失調證三證相兼34例(3148%),從臨床研究來看,乳腺癌術后患者證情較復雜,常常出現多證相兼。
周家明等[10]觀察了117例乳腺癌術后經過放、化療的患者,根據中醫辨證分為肝郁氣滯證(8974%)、氣血虛弱證(5812%)、瘀血阻滯證(5556%)、津虧內熱證(4488%),其中有不少患者身兼數證。唐漢鈞等[11]對乳腺癌術后患者288例進行臨床觀察,認為術后辨證分5型:肝郁氣滯型;肝腎虧虛型,沖任不調型;脾失健運,氣血虧虛型;肺腎虧虛型,氣陰不足型;毒邪蘊結型。劉燕珠等[12]對乳腺癌術后68例患者辨證論治為肝郁氣滯型、氣血虛弱型及痰熱凝結型。劉艷紅等[13]對40例乳腺癌術后經放療、化療后的患者進行中醫辨證分型為肝氣郁結型、脾虛痰濕型、氣陰兩虛型及瘀熱型。萬華等[14]提出乳腺癌術后以腎氣不足、沖任失調、肝脾腎虛為本,以肝氣郁結、脾失健運、氣滯血瘀、痰凝結毒為標的觀點。王淑斌等[15]總結了賈占清教授的治療經驗,指出手術對乳腺癌患者生理、心理的打擊較大,可能會出現氣血雙虧的情況。陳麗等[16]通過文獻研究總結乳腺癌術前及術后的辨證分型,認為術后多出現脾氣虛、陰虛、氣虛血瘀水停型,以虛證為主。陳光群等[17]將100例乳腺癌術后患者辨證分型為脾胃虛弱78%、沖任失調48%、肝氣郁結23%、氣陰兩虛17%、瘀血內阻17%、痰濕8%。其中2證相兼65%,3證相兼13%。吳繼萍等[18]對105例乳腺癌術后患者的中醫證型進行研究,結果顯示乳腺癌主要涉及肝、脾、腎3個臟器,其中脾腎氣虛型28例,脾腎陽虛型15例,脾腎陰虛型25例,氣陰虧虛型37例。endprint
關鍵詞:乳腺癌術后;中醫證型;綜述
中圖分類號:R7379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7-2349(2014)06-0087-03
隨著醫學的發展,手術因其“祛邪”作用的直接性、快速性以及“根治”性,已成為針對乳腺癌實體腫瘤的首選治療方法。中醫藥參與乳腺癌的治療,已從古代重視乳巖的辨證,發展為現代重視乳腺癌術后的辨證,中醫藥在提高手術耐受性,改善手術、術后放化療及內分泌治療的副作用,提高患者生活質量以及預防術后復發轉移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辨證論治是中醫學的精髓,中醫證候規范化、標準化是中醫現代化的趨勢,是中醫現代化研究的重中之重。近年來,中醫“證”及證候規范化的研究已成為中醫界研究的熱點。乳腺癌術后中醫證型及證候標準化的研究,目前尚處于起步階段,已有學者從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進行了探索。廣東省中醫院林毅教授等根據多年臨床實踐提出將乳腺癌分圍手術期、圍化療期、圍放療期及鞏固期的分期辨證體系[1]。中醫藥參與乳腺癌的治療主要集中在圍手術期、圍化療期、圍放療期以及術后長達5年的鞏固期的治療,這就使仍以“實體腫瘤”治療為主旨的現行標準、規范遠滯后于臨床。乳腺癌術后是中醫藥參與治療較長的一個時期,乳腺癌術后辨證所使用的證候名稱及其概念都缺乏明確的內涵和外延,缺乏客觀的、量化的、可操作性強的證候分類標準,乳腺癌術后辨證分型不統一已經成為阻礙中醫藥參與到乳腺癌治療中的瓶頸問題。下面就乳腺癌術后中醫證型研究作一綜述。
1采用傳統中醫辨證研究
乳腺癌是全身疾病,中醫的整體觀和辨證論治在指導乳腺癌的中醫藥治療,尤其是乳腺癌術后的治療中越來越顯示出其特色。辨證論治是中醫學診治疾病的精髓,證是辨證論治的前提和基礎,是連接中醫理論和臨床診療體系的橋梁,長期以來,有關證候及證型規范化的研究一直是中醫界研究的主要方向和熱點。
劉勝等[2]參照鄧鐵濤主編《中醫證候規范》[3]及中國中醫研究院廣安門醫院主編《中醫診療常規》[4]的診斷標準,將407例乳腺癌術后患者進行辨證分型規律探析,臨床辨證為氣陰兩虛證384例(9435%)及沖任失調證331例(8157%)為多,氣血兩虛證22例(5141%),肝氣犯胃證79例(1941%),而氣陰兩虛伴沖任失調證型313例(7690%),亦有三證并存的情況。徐杰男等[5]參照湖南中醫學院中醫診斷研究所主編的《中醫病證治法術語》[6]及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頒布發行的《中醫病證診斷療效標準》[7]的診斷標準,將241例乳腺癌術后患者辨證為氣陰兩虛證者122例占5062%,氣血兩虛證者82例占3402%,沖任失調者138例占5726%,肝氣犯胃證者17例占705%,多證兼夾者112例。吳雪卿等[8]依照鄧鐵濤主編《中醫證候規范》[9]及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頒布《中醫病證診斷療效標準》[7]的診斷標準對108例乳腺癌術后患者進行辨證分型,氣虛證81例(7500%),陰虛證77例(7130%),血虛證25例(2315%),沖任失調證57例(5278%),肝氣郁結證37例(3426%),肝腎陰虛證22例(2037%),氣虛證、陰虛證二證相兼60例(5556%),氣虛證、陰虛證、沖任失調證三證相兼34例(3148%),從臨床研究來看,乳腺癌術后患者證情較復雜,常常出現多證相兼。
周家明等[10]觀察了117例乳腺癌術后經過放、化療的患者,根據中醫辨證分為肝郁氣滯證(8974%)、氣血虛弱證(5812%)、瘀血阻滯證(5556%)、津虧內熱證(4488%),其中有不少患者身兼數證。唐漢鈞等[11]對乳腺癌術后患者288例進行臨床觀察,認為術后辨證分5型:肝郁氣滯型;肝腎虧虛型,沖任不調型;脾失健運,氣血虧虛型;肺腎虧虛型,氣陰不足型;毒邪蘊結型。劉燕珠等[12]對乳腺癌術后68例患者辨證論治為肝郁氣滯型、氣血虛弱型及痰熱凝結型。劉艷紅等[13]對40例乳腺癌術后經放療、化療后的患者進行中醫辨證分型為肝氣郁結型、脾虛痰濕型、氣陰兩虛型及瘀熱型。萬華等[14]提出乳腺癌術后以腎氣不足、沖任失調、肝脾腎虛為本,以肝氣郁結、脾失健運、氣滯血瘀、痰凝結毒為標的觀點。王淑斌等[15]總結了賈占清教授的治療經驗,指出手術對乳腺癌患者生理、心理的打擊較大,可能會出現氣血雙虧的情況。陳麗等[16]通過文獻研究總結乳腺癌術前及術后的辨證分型,認為術后多出現脾氣虛、陰虛、氣虛血瘀水停型,以虛證為主。陳光群等[17]將100例乳腺癌術后患者辨證分型為脾胃虛弱78%、沖任失調48%、肝氣郁結23%、氣陰兩虛17%、瘀血內阻17%、痰濕8%。其中2證相兼65%,3證相兼13%。吳繼萍等[18]對105例乳腺癌術后患者的中醫證型進行研究,結果顯示乳腺癌主要涉及肝、脾、腎3個臟器,其中脾腎氣虛型28例,脾腎陽虛型15例,脾腎陰虛型25例,氣陰虧虛型37例。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