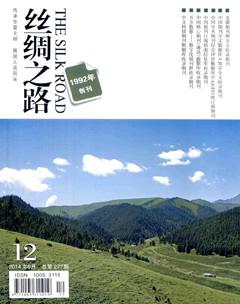杜維明:我不承認有“新儒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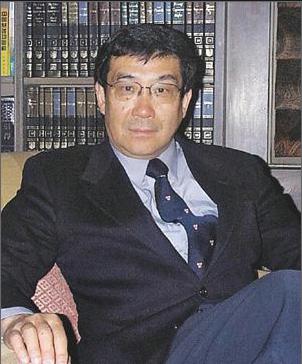
哈佛大學教授、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國際儒學聯合會副會長杜維明幾十年如一日,關懷闡發儒家傳統的內在體驗和顯揚儒學的現代生命力,著重詮釋儒家傳統,確立了對儒家精神價值作長期探索的為學方向。他被稱為當代“新儒家”的代表,可是他本人卻反對“新儒家”這樣的稱謂,到底是所為何故?
《檢察風云》:清末民國時期,有一批知識分子很特別,比如章太炎、熊十力,他們很早就參加了辛亥革命,然而后來卻又走上一條返歸傳統的道路。
杜維明:他們的情況比較復雜,沒有那么簡單,特別是章太炎。他的民族主義情緒非常強,他反滿,事實上強烈反儒家,突出佛教和莊子。但他又是國學大師,小學大師,是魯迅的老師。有一些很有趣的故事,他結婚的時候,孫中山也來參加。他要行古禮,戴個大帽子,結果一行禮的時候,帽子就掉了下來,大家哄堂大笑。他所代表的自然是一個很特殊的傳統。這個傳統是從乾嘉學派樸學慢慢發展出來的一個傳統,現在有些學者說要恢復學術典范,也是這樣一個傳統。
不要完全從章太炎那邊說,他太復雜了。他既參加革命,又有佛教和道家的理念,又和儒家傳統有著非常復雜的情結。但我們看在西方受到人文主義很深影響的白壁德,還有“學衡派”的湯用彤、梅光迪、吳宓、陳寅恪等等,確實是學貫中西。湯用彤在哈佛念書,在哲學系念梵文,對中國哲學、西方哲學和印度哲學,都有很深的造詣。陳寅恪那是更不用說了。我們現在重新發現他們。但在五四時期,他們完全被忽視。他們的觀點現在看來確實是比較高明。
梁漱溟就不同。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去看過他好幾次。后來我和湯一介等人一起發起中國文化書院,他是書院導師。那次他的講話使我非常受感動。他八十多歲的老人不愿意坐下,站著,聲如洪鐘,完全不用稿子,思路非常清晰,講了一個多小時。
《檢察風云》:梁漱溟的精神確實是讓人非常震撼。現在大家也談得很多了,在“文革”前后,梁漱溟、熊十力、陳寅恪、馬一浮等傳統知識分子,特別是新儒學的這幾位代表人物所表現出的堅持信仰、不妥協的態度讓人非常感動。可是像金岳霖這樣的新道家卻是自覺地(并非違心)將自己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思想全部推翻了,還有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更是不要說了,這是個老話題,這種區別您覺得有沒有什么內在的原因?而馮友蘭晚年的轉變也讓人困惑,新儒家內部的區別是否也很明顯?
杜維明:這種現象賀麟也有啊。剛剛講到新儒家的這批人,其實很復雜,每個人的情況都有些差別。
熊十力在去世前,記憶力已經很不好了,看他的《存齋隨筆》中有些重復的地方可以看出來,他還在努力地奮斗,使他的那些理念還能夠堅持下來。
馮友蘭變化大,跟“文革”有關,江青找過他,然后寫出《論孔丘》,認同斗爭哲學。我也到他家去看過他幾次。《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七冊他又從斗爭哲學回到他的和諧觀,就是《貞元六書》的理念。他從張載“必和而解”出發最終走向四句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1982年,我們請他到夏威夷參加首屆國際朱熹哲學研討會,然后他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榮譽博士學位。實際上晚年的時候他已經轉回儒學。
在我看來,他們中間最突出的一個學者其實是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的馮契教授。他提出智慧說。我覺得他最大的貢獻就是將中國古代哲學儒家修身哲學與馬克思主義實踐論中間的復雜關系做了一些梳理。他的手稿在“文革”時候全部散失,他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重新憑記憶來寫,寫了幾百萬字,唯一沒辦法重新來寫的就是他關于美學的文章。這一代儒者,他們做了什么工作?就是試圖將西方文化在當時中國有很大影響力的核心價值與儒家的基本精神結合起來。你也可以說儒家經過了一個西化的過程,這是他們的努力。
我覺得新儒學這個概念其實是不能夠成立的,為什么呢?我們不會說現在的基督教是新基督教,佛教是新佛教,為什么會有新儒學這個名詞?西方在討論宋明儒學的時候,用了一個術語是“New Confucianism”,現在說新儒學,就變成“New New Confucianism”。
新儒學這個名詞的提出是在1987年,方克立組織了一個非常大的研討會,叫“海外新儒家研討會”,40多位學者、18個單位參加了這個會,主要研究新儒學的十家。為什么說“新儒學”的“新”有問題呢?假如有新儒學,就會有后新儒學,新新儒學,每一代的儒家和儒學都會有區別。
而我一直希望能用“儒學的第三期發展”這個概念。雖然這個概念也有爭議,但我認為這是完全能夠站得住的說法。第一期是儒家從山東曲阜的地方文化發展成中原文化的主流,一直到漢末;第二期從宋明儒學發展到東亞文明的基石,一直到十九世紀;第三期是你剛剛講到的晚清禮崩樂壞之后。我們要思考儒學的第三期發展前景,到底它還有沒有發展的可能性?如果進一步發展,那絕對不僅是從中國,也要從東亞和全世界來考量,因為全球化的關系,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的一部分。
對我來說,一個大問題是往前看的十年,儒學能否成為受美國思想界重視的思想潮流。日本的京都學派、日本禪宗經過幾十年的努力已經達到了這樣的程度,那么儒家有沒有這種可能性?當代重要的思想家能否和儒家進行對話?所以這樣講起來,“新儒學”的“新”是大有問題。在這個意義上,我不承認有新儒學,它都在儒學第三期發展中。
《檢察風云》:您認為儒學要發展,必須要有世界的眼光來看儒學,是這樣的嗎?
杜維明:這是兩個問題。一是作為一個地方知識,儒學能否有普適的意義,成為具有全球意義的地方知識。這個地方知識是限定在東亞還是具有全球意義。從地方變成全球這是一個課題。二是你把它發展成全球意義的知識,它能沒有全球視野嗎?不可能。不是說就從世界眼光來看儒學而已,它需要地方的全球化,也需要全球的地方關注。這兩方面要互補。
《檢察風云》:您剛才也談到儒學也有很多問題,從儒家經濟圈看來,傳統的家族企業、儒家經營模式雖然也取得了成功,但常常也會遺留下大量的問題,比如資產的流失以及企業的透明度,比如職業經理人的引入,您覺得這種經營模式的成功和當時的時代背景有沒有直接的關聯?在現代環境中是否還有比較大的競爭力?
杜維明:有些在中國出現的情況在日本正好沒有。日本是長子制度,日本家族的負責人就是一個經理。所以日本許多家族企業,比如三菱和姿生堂,它都是國際大企業,沒有出現這個問題。韓國也是。中國浙江溫州一帶,家族企業是中小企業,而韓國都是國家支持的大企業,比如三星、現代、SK等等都是。
中國的問題可以體現儒家文化的一個側面,但不是儒家文化的全部。我們在浙江成立了一個“儒商與東亞文明”的研究中心,就在浙江大學,他們現在有一個大的計劃,主要來研究家族企業的發展前景、長處和問題。
很多美國最大的企業也是家族企業。比如《紐約時報》。不能說家族企業了就一定很糟糕。你剛才說的企業的資產流失也是實情。企業傳代也是。家族企業要傳到第二代也很不容易,而家族企業的理念能否貫穿維持,兩三代都很難說。
此外,儒家非常注重家庭,但是也容易造成一種狹隘的家族主義。儒家非常注重教育,但教育可能不能成為人格全面發展的機制,卻成為了進身之階,教育對年輕人造成很大的壓迫感。這些我覺得都需要從不同的方面來理解,一方面是同情的理解,另外是批判的認識,同時進行。樂觀派認為中國文化比西方要好得多,這是狹隘的文化主義和民族主義。另一方面,只有中國會出現的聲音,說中醫是偽科學,甚至要去掉中醫,沒想到你要去中醫化,韓國卻在申請漢醫的非物質遺產。這些事情很有趣。
如果將現在和二十多年前相比,我覺得中國的危險更大了,維持社會安定最基本的價值,比如誠信,都在面臨最大的危機。實行市場經濟之后,各個方面都被市場化,包括媒體和學術,這非常危險。孔子認為兵(安全)、實(經濟)和誠信是維持一個社會穩定的三個重要因素,其中,兵沒有實重要,實沒有誠信重要。我們沒有一個西方意義上的市民社會,但多元的傾向越來越明顯,各個不同的社會力橫向的溝通也變得可能。企業、媒體、政府、學術和各種不同的職業團體能不能夠發展出一個平臺,對國家出現的重大問題以負責任的態度來進行討論,進行公共論理,并使這些論理成為政策設定重要的參照。
采訪:河西
編輯:薛華 icexue032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