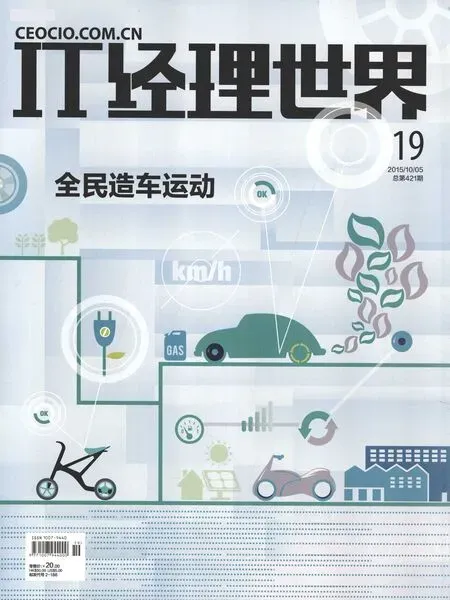谷歌的OKRs&海爾的二維點陣
胡泳+郝亞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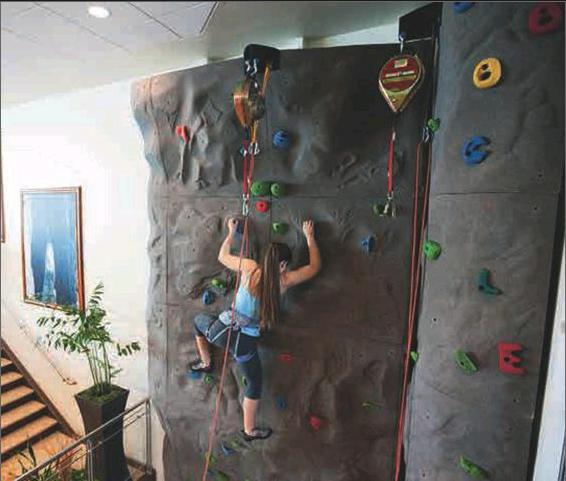
德魯克在《后資本主義社會》一書中對知識經(jīng)濟和知識社會做了大膽且相對精準的預言。其中,他認為管理的主要職能就是對知識進行組織,并使其具有生產(chǎn)力。而組織的任務是破壞穩(wěn)定,“組織必須有條理地放棄它所做的一切作為其結構的一部分”。德魯克受到了熊彼特“破壞是創(chuàng)造”理論的影響,知識社會同工業(yè)社會的最大區(qū)別在于社會進步的驅動因素是“創(chuàng)新”,而非工廠、制造這樣的生產(chǎn)因素,也就是說人類社會開始從生產(chǎn)力驅動步入管理驅動階段。
所謂管理驅動,就是如何把知識用于創(chuàng)新的過程。其中,如何兼?zhèn)渲R的長遠效果和組織的短期利益,就是我們常說的“績效”。我們在談論績效的時候,根本是在談論某種“監(jiān)督”機制。但是,德魯克認為,“在歷史上,工人可以被‘監(jiān)督……事實上,知識雇員不能被監(jiān)督”。衡量一個知識員工的標準應該是,他是否可以最大化自己的知識能力,這樣的前提是允許員工可以自由地使用知識這個工具。
谷歌的OKRs(Objectives and Key Results,目標與關鍵結果)管理被當下很多企業(yè)所推崇,有些人甚至神化其為沒有管理的管理模式。在我們看來,OKRs的最大優(yōu)點恰恰是可以較大限度地實現(xiàn)員工自治。從組織自治到員工自治,需要跨越一個鴻溝,即如何把組織的目標和員工的知識內化。我們之所以不斷倡導解放員工,意義在于員工只有通過追求知識才能認識自己。只有在認識自己的過程中,組織目標介入并和個人知識進行高度調和,最終才能形成組織知識。
作為生命體,組織也具有個體知識,也需要認識自己。遺憾的是,囿于傳統(tǒng)組織架構的限制,組織之上還有一個超然的“理性”君臨天下,“知識”與“工作者”并沒有像德魯克所預言的那樣進行完美結合。尤其在未來保證組織目標實現(xiàn)而實行的各種績效考核中,“技能”、“技巧”占據(jù)了更重要的位置,從近些年興起的各種職場培訓便可窺見一斑。
員工不敢提出德魯克所希望的更大的目標,因為他們害怕自己當下的能力會讓自己失去高績效,從而也因此失去了吸收新知識的機會。
OKR的核心依然是“目標”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谷歌的OKRs受到了新型組織的格外推崇。作為一家只雇用世界上最聰明員工的互聯(lián)網(wǎng)公司,谷歌是如何化“管理”為無形的呢?
OKRs的理念根源可以追溯到德魯克的目標管理(MBO)。上世紀70年代,德魯克的信徒安迪·格魯夫提出“HOM(High Output Management)”。同一時期,甲骨文也發(fā)明了MOKRs(Mission, Objectives, and Key Results)。
1999年,風投機構KPCB的合伙人約翰·杜爾(曾經(jīng)在英特爾工作過),作為谷歌的董事,把這套流程帶給了早期的谷歌。
首先,要設定一個“目標”(Objective),這個目標務必是確切的、可衡量的,例如不能籠統(tǒng)地說“我想讓我的網(wǎng)站更好”,而是要提出諸如“讓網(wǎng)站速度加快30%”或者“融入度提升15%”之類的具體目標;然后,設定若干可以量化的“關鍵結果”(Key Results),用來幫助自己實現(xiàn)目標。
由于谷歌的成功,OKRs方法在Linkedin、Zynga等公司風靡。后來,谷歌在所有它所投資的企業(yè),都要專門進行OKR系統(tǒng)的培訓和實施。
美國密蘇里大學的助理教授孫黎和北京師范大學的助理教授趙向陽在合寫的《企業(yè)內部創(chuàng)業(yè)“反脆弱”四原則》一文(刊載于《中歐商業(yè)評論》2014年7月刊)中認為,“OKR是一個簡單的指導性績效導向工具。每個谷歌的員工、團隊或項目都會自主地提出自己的OKR。項目團隊制定大的目標,在團隊成員中分解成子目標,并設置優(yōu)先級。目標導向使每個員工知道當前的主要和關鍵任務是什么。在每個季度結束之后,同事之間需要相互進行評價。評分高低并不與薪酬或晉升和待遇直接掛鉤,而更多的是給員工一個復盤反思的機會:這個季度工作完成的如何?哪些未完成?下一階段應設置哪些工作重心?在高自由度的谷歌,這種方式能夠保證員工相互協(xié)作,共同向著一致的標桿直跑。”
和傳統(tǒng)KPI相比,OKRs更加適合于追求內部創(chuàng)業(yè)的企業(yè),因為它是自下而上的(比如,60%的“目標”最初來源于底層。不同于傳統(tǒng)KPI的自上而下),更加看重過程的激勵手段,可以讓員工把更多的注意力轉向創(chuàng)新,“因為創(chuàng)新項目在初期往往是靠無定向的、自由探索或試錯的方式來推進的”。
提高創(chuàng)新容錯率,并不代表員工可以漫無目的、隨心所欲。“目標”依然是管理的核心,也是自治的前提。
人力資源顧問徐圣語在一篇介紹OKRs的文章中談到,“相對于傳統(tǒng)的KPI方式,OKRs將工作重心從‘考核回歸到了‘管理。以前績效管理整天圍繞著‘考核轉,離數(shù)字、公式很近,離目標、管理很遠;OKRs搖身一變,把大家的目光轉移到了真正重要的事情上來。”
這種轉移,第一,對于員工而言,OKRs化被動為主動,讓員工敢想、敢干。以前的操作方式,由于直接涉及利益,目標設定變成上下級斗智斗勇、爾虞我詐的談判過程,員工有想法也不一定提。剝離了直接利益因素之后,員工只要認為有利于公司發(fā)展,就會“敢為人先”。
第二,對于企業(yè)目標而言,OKRs化單項發(fā)送為主動鏈接,加強了企業(yè)目標的牽引效果。通過目標公開、透明管理,讓員工的思想和步伐跟得上公司、團隊目標;此外,一旦目標公示,在群眾的火眼金睛下,哪個員工會消極怠工呢?這也為peer-review提供了良好的基礎。
二維點陣的核心是開放
對于創(chuàng)新公司或者新型知識型組織來說,OKRs或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但是對于處于轉型期間的傳統(tǒng)制造業(yè)公司而言,完全依賴于自下而上的績效考核機制并不現(xiàn)實。
首先,員工的知識水平有著較大差異。按照德魯克的觀點,制造業(yè)的員工掌握的更多是特定領域里的技能,缺少較為完整的更高層次的知識體系。這和他們長期處于流水線或者管理鏈條中的某一個環(huán)節(jié)中有很大關系,也就是說他們面對市場的機會很少。
第二,傳統(tǒng)組織轉型意味著“倒退”,這種“倒退”并非全面潰敗,而是基于未來局勢的戰(zhàn)略調整。企業(yè)要做的就是努力保持一個相對穩(wěn)健的市場表現(xiàn),一方面提升內部轉型的動力,一方面打消外界(包括股東)的質疑。
所以,在到底是自上而下,還是自下而上的選擇上,張瑞敏直接提出了用戶標準說。市場是檢驗績效的最好方法,每一個人每一個經(jīng)營體都要被用戶考核。而在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對于用戶的理解顯然更加豐富。傳統(tǒng)的市場占有率、銷量指標代表了交易價值,成交量是硬指標。同時,產(chǎn)品的創(chuàng)新應該是以用戶需求為導向的,網(wǎng)絡時代的用戶需求是建立在大量的交互價值之上的。比如小米的用戶為小米貢獻的絕不僅僅是手機這個有形產(chǎn)品的銷量,還包括了小米商城的下載量,小米周邊產(chǎn)品的銷量,更重要的是小米的口碑。
海爾的創(chuàng)新之處在于將交互價值和交易價值統(tǒng)一在了一個叫做“二維點陣圖”的體系中。這張圖的含義是,要把產(chǎn)品賣給有名有姓的用戶,并了解他的需求。這和單純的賣產(chǎn)品有了天壤之別。
其中,橫軸代表了傳統(tǒng)的KPI指標,不同的是,這個指標不是由領導層指定,也不是由員工自己提出,而是由市場來決定。海爾對內部產(chǎn)品的市場定位是“引領”,就是要超出競爭對手一大截,成為整個細分產(chǎn)品領域里的引領者。但是,“引領”的指標不能靠傳統(tǒng)的“售賣”模式完成,而是要體現(xiàn)出縱軸上的用戶價值(網(wǎng)絡用戶的數(shù)量)。海爾的某款冰箱一上市就有了很不錯的銷量,但依靠的依然是線下渠道“返點”模式,這個產(chǎn)品的經(jīng)營體負責人在周六的干部大會上被嚴厲批評。
僅僅去買產(chǎn)品的人叫消費者,不單買你的產(chǎn)品,還能和你進行信息互動,并產(chǎn)生情感聯(lián)系的才是用戶。互聯(lián)網(wǎng)無疑是產(chǎn)生用戶的最好場所。因此,張瑞敏在內部會議上無數(shù)次強調,海爾需要的是交互價值。這就產(chǎn)生了縱軸。
二維點陣同樣適用于海爾對小微的考核上。小微和孵化平臺之間簽署對賭協(xié)議的時候,橫軸和縱軸都是考量標準。一方面,張瑞敏在逼著海爾人觸網(wǎng)。另一方面,這也是讓海爾堅固的內部自行開放的催化劑。對于不懂網(wǎng)絡的傳統(tǒng)制造業(yè)的員工來說,最好的辦法就是請來懂網(wǎng)絡的人。
可以看出,海爾的二維點陣圖最終的目標是讓海爾形成開放的文化和員工的自治機制。對于過渡期的傳統(tǒng)企業(yè)而言,這是一個相對合理的績效考核體系,兼顧了市場需求和創(chuàng)新動力。
無論是谷歌的OKRs還是海爾的二維點陣,都是對傳統(tǒng)KPI的有效調整。OKRs更注重員工的自主創(chuàng)新性,追求自下而上。海爾的二維點陣追求的是傳統(tǒng)企業(yè)對互聯(lián)網(wǎng)規(guī)律的適應性,不再以“上/下”為推動力,而是統(tǒng)一由市場來決定。
兩者的一致之處在于將組織目標和個人的知識能力相融合。新型知識型組織的員工素質較高,他們對網(wǎng)絡有獨到的見解,同時有自己的知識體系,組織只要給他們發(fā)揮的空間即可。對于傳統(tǒng)型組織而言,員工更多掌握的是技能。換句話說,當他們離開生產(chǎn)線之后,很可能會一無是處。這并非德魯克眼中的知識員工,而是更加接近于藍領工人。最安全的方法,莫過于將組織轉型的目標和個人架構自己知識能力的途徑結合起來,讓他們面對這個瞬息萬變的互聯(lián)時代,用一種和自己的過去完全決裂的方式獲得生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