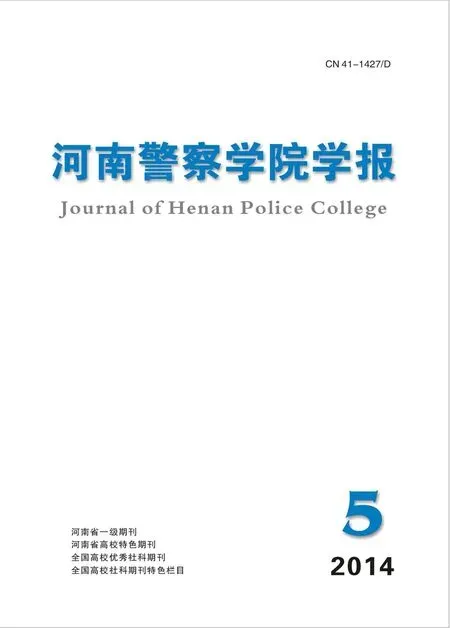論反腐體系科學化視野下的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刑事治理對策
張遠煌,操宏均
(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北京100875)
近幾年關于企業家犯罪現象的研究報告顯示,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形勢嚴峻,如2012年民營企業家涉及腐敗犯罪罪名共計53例,占民營企業家涉案總罪名數251例的21.1%;①其中,職務侵占罪15例、行賄罪8例、挪用資金罪7例、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7例、受賄罪(共犯)4例、貪污罪(共犯)3例、挪用公款罪(共犯)3例、單位行賄罪3例、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各2例、私分國有資產罪1例。參見張遠煌、陳正云主編:《企業家犯罪分析與刑事風險防控(2012-2013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1~12頁。2013年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案件86例,占民營企業家犯罪案件總數的24.4%;民營企業家涉嫌腐敗犯罪共117人,占民營企業家涉案總人數的24.9%。②參見北京師范大學中國企業家犯罪預防研究中心:《2013年中國企業家犯罪分析報告》,http://www.criminallawbnu.cn/criminal/Info/showpage.asp?showhead=Q&pkID=42388。同樣的,追蹤記錄中國企業家群體變化的權威機構胡潤百富近期發布的《胡潤百富榜——中國富豪特別報告》也明確指出,貪污賄賂犯罪,是中國富豪出問題的最主要原因。③參見胡潤百富:《胡潤百富榜——中國富豪特別報告》,http://www.hurun.net/zhcn/NewsShow.aspx?nid=2502。令人遺憾的是,盡管當前國家反腐力度不斷加大,以及一些“老虎”、“蒼蠅”也相繼被打掉,并且中共中央也于2013年12月26日出臺了《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2013-2017年工作規劃》,但是實踐表明,當前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問題并沒有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理論研究也相對匱乏。④無論是官方發布的相關報告,如最高檢的工作報告以及關于反貪污賄賂工作情況的報告,中紀委工作報告,等等,還是學術界研究狀況,如在中國知網、谷歌學術等網站,以及新聞媒體以及百度、搜狐、騰訊等互聯網站,都鮮有關于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問題的研究與報道,凸顯這一研究領域的“蒼白化”。因此,如何促進中國民營企業家與民營經濟借力市場經濟改革的大好時機,持續健康成長與發展,是因應時代新要求的一項重要課題。
一、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的認識誤區
毋庸置疑,官員、國有企業家等“國”字頭、“公”字頭人員歷來是反腐敗犯罪的重點對象,因為無論是在建國初期的《懲治貪污條例》(1952),還是79刑法乃至現行刑法關于腐敗犯罪的法律條文中,這些人員始終是其規制的對象。盡管相關條文中也涉及“非公”身份人員的腐敗犯罪問題,然而與之相比,卻多因處于“拉攏腐化”的附屬位置而難以成為反腐斗爭的主要目標。正是這種一以貫之地重視反“公有”腐敗的導向,使得人們已經對腐敗犯罪形成了“腐敗——公職”的思維定勢。另外,客觀上來看,中國民營經濟序幕是在1992年才拉開的,這樣由于先天歷史積淀不足,且又長期處于政府“父愛式”監管之下的發展模式,使得民營經濟長期以來游走于社會生活的邊緣,進一步拉大了民營與腐敗之間的關聯。時至今日,中國的民營經濟得到了蓬勃發展,腐敗犯罪也發生了變化,這就要求我們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發展觀來審視這些新情況、新問題,誠如習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發表演講所言:“不能身體已經進入21世紀,腦袋還停留在過去。”①參見習近平:《順應時代前進潮流促進世界和平發展》,http://www.gov.cn/ldhd/2013-03/24/content_2360829.htm。
(一)誤區一:民營企業家是被忽略的腐敗犯罪主體
正是由于人們一般認為“腐敗是權力的濫用……‘腐敗’這一術語常常用以表示政治家和公職人員對公權力的濫用”[1],腐敗犯罪更多被貼上了“身份犯”的標簽,即以特殊身份作為客觀構成要件要素的犯罪[2]。與此相對,民營企業家更多被賦予的是以“私有”、“自負盈虧”為表征的非公身份,這種人為的身份劃定導致人們理所當然地將民營企業家排除在腐敗犯罪之外。考察世界各國刑法典,不難發現,多數國家在規制腐敗犯罪時,也多有“公”身份之限定的規定,如日本現行刑法在其分則第25章“腐敗犯罪”(汚職の罪)(即第193條至第198條)幾個條文中多有“公務員”、“特別公務員”之主體身份的限定;②有關日本刑法典相關規定,請參見日本國法務省網站 http://law.e-gov.go.jp/htmldata/M40/M40HO045.html。德國刑法在其分則第30章“職務犯罪”(Straftaten im Amt)(即第331條至第358條)有關腐敗犯罪的條文中,也多有公務員(Amtstr?ger)這樣的限定,③有關德國刑法典相關規定,請參見德國法律網站http://www.gesetze-im-internet.de/englisch_stgb/index.html。等等。不可否認,盡管各國刑法在規定腐敗犯罪時,也多數涵蓋了包括民營企業家在內的任一個體或者單位實施行賄犯罪行為的情況,但是,由于我們社會普遍存在著這樣的一種視行賄方為弱者進而對其產生同情之心的普世情結,即一般認為在行賄與受賄這一矛盾體中,受賄一方往往因為掌握公共權力,在資源利益分配中處于主導地位,而行賄方往往處于受支配地位,屬于弱勢一方,容易得到人們的同情[3]。這樣就會使處于賄賂犯罪對合犯④對 合犯,也稱對行犯、對應犯、對向犯,是指基于二人以上的互相對向行為構成的犯罪。參見高銘暄、馬克昌主編:《刑法學》(第4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81頁。一端的行賄方往往能夠獲得民眾的容忍。加之,在司法實踐中普遍存在“重受賄輕行賄”的現實狀況,⑤有人統計,2004年至2008年,全國檢察機關共立案偵查受賄案件45046件47297人,而立案偵查行賄案件僅為10201件11699人,約占立案偵查受賄案件的27% ,二者比例嚴重失調,大量行賄案件未被立案查處。參見肖潔:《行賄犯罪查處的困境與解決途徑》,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10年第8期。進一步淡化了包括民營企業家在內的行賄者作為腐敗犯罪主體的身份。
然而,實踐表明,腐敗犯罪并非政府官員、國有企業家等“公有”身份人員的“專利”。因為腐敗犯罪的本質特征就是將公共權力與相關利益進行了對價處理,即權力的權利化,實際上就是變公益為私利的過程。由此可見,腐敗犯罪更多與權力相關,而非主體的身份。民營企業家作為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新生階層,其參與社會經濟生活的廣度與深度都是空前的,這為其實施腐敗犯罪提供了大量的機會。誠如1939年美國著名犯罪學家薩瑟蘭提出白領犯罪之前,人們幾乎一直都認為犯罪是窮人的“專利”,而與白領等社會上層人士聯系不大,但事實表明,“違法犯罪行為是相對平均地分布于社會各個階層的”[4]。如薩瑟蘭調查研究的70家公司,所受的裁決(當然包括刑事的、民事的和行政處罰類的)總數是980個,平均違法記錄則為14次,每家公司至少都曾經因為違法行為受到過1個或者1個以上的裁決,最多的達到50個裁決。并且這70家公司中有60%曾經被刑事法庭判決有罪,平均每家公司約有4個有罪判決[5]。自薩瑟蘭以降,白領犯罪已經獲得普遍認可,成為犯罪學研究中的顯學。由此可見,隨著社會的發展,一些傳統犯罪學理論在解釋一些新的犯罪現象時難免會出現蒼白無力的窘境。此時不應固執己見,而應該“消除所謂知識的高貴起源問題,讓作者專橫的立場自行消失”[6]。當前民營經濟領域高發的腐敗犯罪狀況已經表明,異軍突起的中國民營企業家群體,已經打破了公職人員“壟斷”腐敗犯罪的局面。
(二)誤區二:對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危害性認識不足
對于腐敗犯罪造成的危害,尤其是公職人員腐敗犯罪所造成的危害,通過天文數字的涉案金額、落馬官員的級別等信息我們往往可以較為直觀地感受到其造成的破壞程度大小。加之,普通民眾愈發增長的“納稅人”意識,進一步促進其形成“尸位素餐腐敗分子實施的腐敗行為即是對自己繳納稅款非法占有”的觀念,直接拉近了人們對這些公職人員腐敗危害的認識,因為這簡直就是赤裸裸的剝削。與之相比,一般人普遍認為,一方面民營企業家會對自己企業的財產格外小心;另一方面民營企業家對自己企業財產的處置,如挪用、支取、贈與他人等,實際上是對自己的私有財產行使處分權,并不會涉及普通民眾的相關利益,即便是其確實存在損人利己的行為,往往也僅僅局限于特定人或者個別人員,而不會形成公職人員腐敗是對所有納稅人犯罪的局面。所以從人們最樸素的公平正義情感上來看,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因為“危害較小”而較為容易獲得人們的諒解。
然而,事實表明,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也會造成十分巨大的損失,如美國著名經濟學家Andrei Shleifer和Robert W.Vishny早在1993年就指出,“……從私營部門的角度來看,腐敗就等于榨取,其對企業發展的損害遠大于稅捐等合法手段”,①參見 Andrei Shleifer and Robert W.Vishny.“Corruption”,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06,No.3,(August,1993),pp.599-617。而美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CSIS)近期發布的研究報告《腐敗的代價》(The Costs of Corruption)則無疑是對這一論斷的進一步強化,他們指出:“作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一種負擔,其私營部門的腐敗正在增長,每年至少耗費5千億美元,是2012年所有對外援助資金的三倍。”②參見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The Costs of Corruption,(Feb 21,2014),available at http://csis.org/publication/costs-corruption。除了這些經濟上較為直觀的損失之外,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對社會造成的間接損失也不容小覷,因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就意味著對規則、法治與誠信的強調,而腐敗則意味著對既有規則、法治的突破和見利忘義,破壞了法的權威性與安定性,造成了事實上的不公平,扭曲了民營企業激勵機制,即非法方式比合法方式更容易達到贏利的目的,導致劣幣驅逐良幣,進而助長了弄虛作假等不良社會風氣的盛行。使守法的企業家處于競爭劣勢,破壞了游戲規則,破壞了社會誠信的價值基礎,從而導致市場的惡性發展。從這方面講,民營企業家犯罪與國有企業家犯罪沒有太大區別。
二、當前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形勢③本部分有關企業家腐敗犯罪數據,來源于北京師范大學中國企業家犯罪預防研究中心先后發布的2012年、2013年中國企業家犯罪分析報告,具體內容參見http://www.criminallawbnu.cn/criminal/info/Q_index.asp。
在進行分析之前,首先需要明確本文關于“腐敗犯罪”的指涉。盡管古今中外人們關于腐敗犯罪的界說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是“僅僅斷言不會有一種具有普遍約束力的、到處適用的、內容一致的犯罪概念是不夠的,犯罪學自己必須對怎樣理解犯罪提出一條準則。只有這樣,犯罪學家才有可能求得一種最低標準,以便在必須估計哪里可能出現問題方面有一致意見。否則,他們就缺少一種坐標系和指南針,從而不能在疑團莫釋的汪洋大海中游向彼岸”[7]。同時,為了便于與國有企業家腐敗犯罪進行比較研究,以及“貪污、職務侵占、賄賂、挪用”等行為已經被人們當然列入腐敗犯罪的現實。因此,本文的腐敗犯罪也限定在這些方面。具體而言,本文的腐敗犯罪主要指涉我國《刑法》第八章“貪污賄賂犯罪”(第三百八十二條至第三百九十六條)以及相關章節中規定的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第一百六十三條)、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第一百六十四條第一款)、對外國公職人員、國際公共組織官員行賄罪(第一百六十四條第二款)、職務侵占罪(第一百八十三條、第二百七十一條)、挪用資金罪(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二百七十二條)。
(一)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數量急劇攀升
最近兩年的《中國企業家犯罪分析報告》(以下簡稱《報告》)顯示,從企業家腐敗犯罪絕對數據上來看,無論是國企案例數、人數,還是民企案例數、人數,2013年較2012年有所增加。但是,從國企、民企腐敗犯罪的人數、案例數分別占的百分比來看,國有企業家腐敗呈現出萎縮樣態,而民營企業家犯罪呈現出“蒸蒸日上”的態勢(如下表1、圖1所示)。

表1 2012、2013年度企業家腐敗犯罪數量統計情況

圖1 2012年、2013年企業家腐敗犯罪統計表
由此可見,國有企業家腐敗犯罪實際上出現了絕對犯罪數量有所增加但是所占百分比卻下降的情形,并且下降幅度高達15個百分點左右。與之相反,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則絕對犯罪數量與所占百分比同步增長,并且增長幅度高達十幾個百分點。這種下降與增長幅度的鮮明反差進一步說明,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正以“蜂擁之勢”出現。
上述現象表明,當前企業家腐敗犯罪依舊形勢嚴峻,尤其是國有企業家腐敗犯罪絕對數量有所增加與黨的十八大大力推進反腐力度不無關系。有人統計,自黨的十八大以來,落馬國企廳官就多達30名[8],但是其所占百分比較大幅度下降的事實也進一步說明,在當前的高壓反腐態勢下,確實對有些“心懷鬼胎”的國有企業家起到了震懾作用。而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穩步攀升”,絲毫不受當前高壓反腐態勢的影響,這種現象進一步印證當前的反腐體系仍然存在民營主體缺位的現實。
(二)民企與國企企業家腐敗犯罪側重點迥異
在企業家腐敗犯罪中,盡管國企、民企都涉及貪污、侵占、賄賂、挪用等腐敗犯罪,但是基于國企、民企企業家身份差異,按照腐敗犯罪過程中的財物流向,不難發現,國企企業家腐敗犯罪中多集中表現為“吸收型腐敗”,即財物流向犯罪分子個人,而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多表現為多種方式齊頭并進,其中“輸出型腐敗”(即財物從犯罪分子個人向外流出)占有相當比例。這從2013年企業家犯罪報告調查得到印證,2013年國企企業家腐敗犯罪共涉及6個罪名,具體而言,受賄罪(56人次)、貪污罪(39人次)、挪用公款罪(22人次)、私分國有資產罪(5人次)、行賄罪(3人次)、職務侵占罪(3人次)。與之相對,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也共涉及6個罪名,其中,挪用資金罪(39人次)、職務侵占罪(36次)、行賄罪(23次)、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19次)、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10次)、單位行賄罪(9次)。上述數據顯示,國企企業家涉及6個罪名中有4個罪名就屬于“吸收型腐敗”,即受賄罪、貪污罪、私分國有資產罪、職務侵占罪,并且觸犯這4個罪名合計103人次,占總數128人次的80.5%;而民營企業家涉及6個罪名中有3個罪名就屬于“輸出型腐敗”,即行賄罪、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單位行賄罪,并且觸犯這3個罪名合計為42人次,占總數136人次的30.9%,挪用型腐敗犯罪占總數136人次的28.7%,“吸收型腐敗”(職務侵占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占總數136人次的40.4%。
由此可見,國企與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表現方式上存在著巨大差異,即國企企業家腐敗犯罪集中于“吸收型腐敗”,而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形成“吸收型腐敗”、“輸出型腐敗”、挪用型腐敗三足鼎立的格局。進一步分析發現,國企企業家腐敗犯罪樣態的高度集群化,即“吸收性腐敗”,這無不與其具有的特定權力緊密相關。一方面,“國”字頭企業的特殊背景使其無需為企業運行資金不足等問題而四處奔走,同時,相關行業壟斷地位的賦予也使其具備“含著湯匙出生”的無限優越感。另一方面,“國”字頭企業實際控制人嚴重缺位導致了企業內部人員控制局面。因此,其之所以集中于“吸收性腐敗”無不是權力市場化的結果。與之相比,新興民企多數“本小利微”,除了面臨激烈的市場競爭淘汰風險之外,時常出現資金運行不足融資難等困境,加上有關行業、項目設定的準入門檻較高、資質要求較為苛刻,使得一些本來就處于羸弱的民企在短期無法提供自身硬實力的條件下,就只能通過“花錢買準入證”的方式來進行,所以在腐敗犯罪方式上就會多出現“輸出型腐敗”與“拆東墻補西墻”的挪用型腐敗。盡管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中“吸收型腐敗”也占有較高比例,與其說是在進行權力對價交易,還不如說是由于長期的“輸出”使得其一旦逮著了“兜售”手中權力的機會,便斷然不會輕易放過。總之,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的形態既有明顯的體制因素,也包括民營企業的自身行業特點,導致犯罪類型多元化。
(三)同質性企業家腐敗犯罪存在差異化懲罰
就企業家腐敗犯罪所涉及的相關罪名來看,盡管刑法對有些犯罪行為在罪名與刑罰設置上存在較大差異,但是就罪質而言其實并沒有什么不同。如貪污罪與職務侵占罪,受賄罪與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挪用公款罪與挪用資金罪,等等。因此,從本質上來看,如果實際出現的犯罪情形相當,如涉案金額相當、造成損失相當等,那么在科處刑罰上就不能因為行為人國企、民企身份而出現較大的差異。2013年報告顯示,在國有企業家腐敗犯罪中,挪用公款罪判決8人中,7人提及了挪用的數額,最低數額為4.7萬元,最高數額為377萬元,平均挪用金額為166.6萬元。挪用數額為4.7萬元的企業家免予刑事處罰,挪用數額為69萬元與78.6萬元的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6個月和有期徒刑5年6個月;挪用數額大于一百萬元的4位企業家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2年10個月至10年不等。而在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中,挪用資金罪判決11人涉及涉案金額,最低金額為16萬元,最高金額為9900萬元,平均涉案金額為76.5萬元。11人分別被判處1年到7年6個月不等的有期徒刑。挪用資金罪涉案金額與判處刑期之間存在統計學意義上的相關關系(r=0.491,p < 0.001),犯罪所得對刑期的解釋率為24.1%。也就是說,國企企業家挪用377萬元公款,獲得的刑罰是10年有期徒刑,而民營企業家挪用9900萬元資金,其獲得刑罰的最大值也僅僅是7年6個月的有期徒刑。這種情形在貪污罪與職務侵占罪、受賄罪與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等對比中也較為普遍。由此可見,同質性的企業家腐敗犯罪,在司法實踐中往往會因為行為人主體身份是否“國有”而出現巨大差異的懲處結局。
三、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刑事法治對策
(一)企業家腐敗犯罪刑事法治當以制度性誘因為出發點
從法治理念上來講,我國憲法規定公私財產要平等保護,尤其是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要進一步提升民營企業的地位。我國刑法的原則之一就是“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從這方面來講,要想切實做好企業家刑事風險防范工作,就要樹立民營企業、國有企業在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價值觀念。然而,民營企業在我們國家現階段實際上還是處于劣勢地位,政府監管比較嚴厲,存在制度性的打壓因素,即制度性陷阱。例如,我們統計的民營企業家犯罪2012年、2013年比重最大均為融資犯罪,究其原因,民營企業沒有多少可以選擇通過合法途徑獲取資金的渠道,大型商業銀行、國有銀行貸款對民營企業的門檻很高,而民營企業需要大量資金迅速向外擴張,他們只能向社會募集。但是這種募集方式我們國家沒有現成的制度來對其加以規范和指導,募集本身風險就很大,一旦出現資金斷裂,就會引起相應的不良社會反映,觸犯刑法中的這些罪名。這些罪名雖然不是專門為民營企業家設立的,但國有企業家很少會觸犯這些罪名。從立法的角度來講值得反思,立法的初衷雖然沒說該罪名只針對民營企業家,但實際運行過程中,我們這些罪名基本上成為民營企業家“專用”。在這種制度環境下,如果單純在刑法層面來強調國有企業的腐敗犯罪與民營企業的腐敗犯罪要同等打擊,并不合理。因此,基于民營企業處于制度劣勢的現狀,如果僅僅著眼于法理而忽視了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的一些制度性成因,可能在我們的觀念、刑事立法、刑事司法方面會走向錯誤的方向。
(二)強化民企保護,樹立公私財產平等保護的反腐刑事法治理念
觀念是行動的先導,誠如人們常常說道,提出一個問題往往比解決一個問題更重要。因為“有什么樣的思想,就有什么樣的行為”(查·艾霍爾語)。在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治理中,刑事法治作為一條重要的路徑選擇,也必須以科學的刑事法治觀念作為指引。考察我國當前的刑事法治觀念依據,不難發現,一方面,當前我國《憲法》在第十二條、第十三條分別確立了公共財產、私有財產不可侵犯,這種并列式的分條規定模式無不體現國家在憲法層面對兩種不同性質財產同等重視的價值取向。另一方面,在現行刑法中,更是開宗明義將“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列為我國刑法三大原則之一。應該說,這種通過根本大法和基本法律雙重規定的形式,已經足以體現出國家對公、私兩種不同性質財產同等重視的觀念導向。然而,事實上國有與民營企業家腐敗犯罪的差異化刑事處遇,使得這種公私平等對待的觀念更多流于形式,難以發揮憲法作為部門法之母法的引領功能,同時也架空了刑法基本原則在具體刑法立法和刑事司法中的指導、制約意義。因此,“想要借規范來規整特定生活領域的立法者,他通常受規整的企圖、正義或合目的性考量的指引,它們最終又以評價為基礎”[9],這勢必要求立法者和司法工作人員在具體刑事立法、司法實踐活動中應該時刻堅守與強化這一理念。
(三)積極推動反腐敗刑事立法科學化
一方面,反腐敗犯罪罪刑配置應該均衡化。當前我國刑法中規定的相關腐敗犯罪在同質犯罪間,普遍存在罪刑設置失衡狀況。如《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條第一款①《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條第一款(挪用資金罪)規定:“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挪用本單位資金歸個人使用或者借貸給他人,數額較大、超過三個月未還的,或者雖未超過三個月,但數額較大、進行營利活動的,或者進行非法活動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挪用本單位資金數額巨大的,或者數額較大不退還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在規定非公領域挪用型腐敗犯罪時設置了兩個法定刑幅度,并以“三年有期徒刑”為分界點,而《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條第二款①《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條第二款(挪用公款罪)規定:“國有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國有單位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和國有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國有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以及其他單位從事公務的人員有前款行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四條的規定定罪處罰。”在規定公有領域挪用型腐敗犯罪時,其設置的兩個法定刑幅度(依據《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條②《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條(挪用公款罪)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進行非法活動的,或者挪用公款數額較大、進行營利活動的,或者挪用公款數額較大、超過三個月未還的,是挪用公款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挪用公款數額巨大不退還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是以“五年有期徒刑”為分界點,即便是針對較為嚴重的挪用行為也存在天壤之別,如民營企業家“挪用本單位資金數額巨大的,或者數額較大不退還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據舉輕以明重的原則,民營企業家挪用本單位資金數額巨大不退還的,面臨的最高刑罰也就是十年有期徒刑,而國企企業家“挪用公款數額巨大不退還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在國家將“非公經濟”提高到與“公有經濟”同等重要地位的情形下,一方面,刑事立法作為反腐敗系統工程中的一個重要抓手,另一方面,包括腐敗犯罪在內的一切犯罪都源于社會矛盾,與現實的社會結構和運行狀態緊密相連。因此,在犯罪必然存在的語境下,刑罰并不能完全消滅腐敗犯罪。所以為了發揮刑罰功能最大化,就必須順應時代發展的現實要求,全面梳理現行刑法中腐敗犯罪刑事立法罪刑失衡部分,防止因為刑罰投入不足而變相放縱犯罪或者投入過剩而貶損刑罰價值的情形,通過刑法的“立、改、廢”消解其反腐敗犯罪刑事立法不科學的地方。
另一方面,反企業家腐敗犯罪刑罰設置應該增設資格刑與加重罰金刑。企業家腐敗犯罪在一定程度上與其具有相關資質和經濟實力是密切相關的,并且其作為商業帝國的主宰者,其背后還有強大的企業實體作為經濟支撐和犯罪保護膜。這些無疑為其進行腐敗犯罪提供了重大的支撐,因此,要實現刑罰預防行為人再犯的功效,就有必要對行為人的生產資格和經濟實力進行剝奪。盡管我國現行《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條、《商業銀行法》第二十七條、《會計法》第四十條等③相關法律條文,請參見《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條、《商業銀行法》第二十七條、《會計法》第四十條。對公司的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的資格進行了限定性規定,但是由于其過于原則性以及不分輕重的“一刀切”模式,加之日益繁雜的經濟實體樣態,已經極大突破公司法關于“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的羅列,所以公司法這一規定更多體現的是一種宣誓意義,即對污點職員的管理崗位排斥。考察域外刑事立法,不難發現對于腐敗犯罪設置資格刑成為主流,如德國刑法第70條用了較多篇幅對“職業禁止”做了詳細規定[10],法國刑法典在第131-6條規定“禁止簽發支票以及使用信用卡付款,最長期間為5年”、在第131-39條對涉案企業有永久性或者最長5年的禁業規定、對企業募集資金、發布廣告等行為也都有較為詳細的禁止規定[11]。鑒于資格刑對于包括腐敗犯罪在內的一些犯罪的防治功能,以及結合企業家腐敗犯罪的特殊之處,很有必要在我國刑法中對腐敗類犯罪設置資格刑。具體來講,對于企業家腐敗犯罪,可以考慮除了對行為人本人實施永久性或者一定期限的商業活動禁止外,對于參與犯罪的企業也可實施諸如吊銷營業執照、責令停業整頓等懲處,這樣才能從根本上剝奪行為人實施腐敗犯罪的條件。同時兼顧激發市場經濟主體創新能力和防止因為犯罪標簽而出現“一竿子打死”的局面,對于適用資格刑的,可以根據其行為、后果等多方面綜合因素考慮建立復權制度。④復權是指對宣告資格刑的犯罪人,當其具備法律規定的條件時,審判機關提前恢復其被剝奪的權利或資格的制度。參見馬克昌主編:《刑罰通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716頁。鑒于企業家腐敗犯罪中較為突出的牟利特性,從法經濟學的角度出發,完善現有腐敗犯罪罰金刑規定較為粗疏的現狀很有必要。一方面,應該適當提高腐敗犯罪罰金刑,通過直觀的“成本大于收益”設計阻止行為人再犯;另一方面,在罰金刑的適用上應該對自然人犯罪和單位犯罪適當區分,拉開單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的罰金刑距離[12]。
(四)反腐敗犯罪刑事司法公正化
首先,強化反腐打擊力度,尤其是對有些企業家實施的惡劣行賄犯罪的打擊。毋庸置疑,民營企業的制度劣勢地位,會在一定程度上逼迫一些民營企業家基于企業求生本能而實施行賄犯罪等違法行為,但是實踐中也不乏部分民營企業家為了獲取資源、利潤而不擇手段的情形。加上,在我國刑事司法實踐中,一直存在著“重受賄、輕行賄”客觀事實。事實也表明,行賄犯罪作為腐敗犯罪鏈條上的重要一環,其危害性絲毫不亞于受賄、貪污等行為。鑒于此,2014年4月24日,“最高檢”召開全國檢察機關反貪部門重點查辦行賄犯罪電視電話會議,向公眾釋放出“加大懲治行賄犯罪力度”的信號。司法機關應該以此為契機,深挖腐敗犯罪線索,果斷排除辦案干擾阻力,重點查處行賄次數多、行賄人數多、行賄數額大、獲取不正當利益巨大、行賄手段惡劣、造成嚴重后果等社會危害性更為突出的行賄犯罪案件,對于一些惡劣的行賄行為,要果斷出擊,自首①近期有學者主張應取消我國刑法對行賄罪設置的特別自首制度,即規定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代行賄行為的,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具體內容參見劉仁文、黃云波:《建議取消行賄犯罪特別自首制度》,載《檢察日報》2014年4月30日,第3版。、檢舉揭發等不應該成為行賄者的“免罰金牌”,對于不構罪的行賄行為,應該發揮檢察機關法律監督職能,通過出具檢察建議、拓展職務犯罪預防功能等途徑防患于未然。
其次,處理具體企業家腐敗犯罪時,最大限度確保公平正義。一是嚴格執行國家統一的立案標準,切實杜絕人為拔高腐敗犯罪入刑門檻。目前,司法實踐中確實存在一些所謂的遠遠高于腐敗犯罪法定基準數額的“內部標準”,嚴重破壞了法律的統一性,使一些本來應該受到刑法制裁的腐敗分子游離于法網之外,變相鼓勵腐敗分子采用“少吃多餐”的犯罪手法,使得刑法毫無威懾力可言。二是根據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要求,用好刑事司法裁量權。不能因為企業家及其所在企業對當地經濟發展貢獻大,就隨意減免其罪責,而應該在法律和政策的框架內予以考量。具體來講,對于確實具備自首、立功、積極退贓、沒有給國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損失等從輕情節的,應該合理地予以從寬處理;對于行為人具有涉案數額巨大、造成巨大損失等惡劣情節的,應該從重處罰。三是盡量均衡個案裁量之間的協調關系。利用當前司法機關法律文書全面上網和不定期發布指導性案例為契機,針對我國刑法中腐敗犯罪量刑幅度規定過大的現實,要求司法人員在具體的企業家腐敗犯罪案件裁量時,不能出現類似腐敗犯罪案件刑罰懸殊的情形。
[1](加)里克·斯塔彭赫斯特,(美)薩爾·J.龐德.反腐敗:國家廉政建設的模式[M].楊之剛譯.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1.
[2]張明楷.刑法學(第四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96.
[3]周麗萍.行賄不止,腐敗何已?[J].廉政瞭望,2006,(2).
[4]張遠煌.犯罪學(第二版)[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92.
[5](美)E.H.薩瑟蘭.白領犯罪[M].趙寶成等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7:12~26.
[6](法)米歇爾·福柯.知識考古學[M].謝強,馬月譯.北京:三聯書店,2003:42.
[7](德)漢斯·約阿希姆·施奈德.犯罪學[M].吳鑫濤,馬君玉譯.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0:73~74.
[8]李天銳.十八大后30名國企廳官落馬[J].廉政瞭望,2014,(6).
[9](德)卡爾·拉倫茨.法學方法論[M].陳愛娥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94.
[10]德國刑法典[M].徐久生,莊敬華譯.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4:37~38.
[11]吳平.《法國刑法典》中的資格刑規定述評[J].行政與法,2002,(10).
[12]張遠煌,操宏均.偽劣商品犯罪防控對策探析[A].趙秉志.刑法評論(2012年第2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