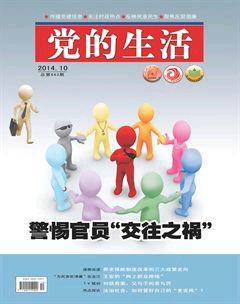監管之道話“三圈”
邢丹

9月24日,國家發改委原副主任、國家能源局原局長劉鐵男涉嫌受賄一案公開審理。從相關報道的情況看,貫穿于劉鐵男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的行賄受賄行為,呈現出典型的“圈子腐敗”特征,也使得劉鐵男“三圈”內的一些成員因此“一損俱損”。
發人深省的是,這樣的情況絕非特例。
據《中國新聞周刊》報道,全國政協原副主席蘇榮是十八大后首個被查的“副國級”官員,其涉嫌違紀違法行為的主要問題多發生在擔任江西省委書記期間。蘇榮的落馬,揭出江西官場權力尋租、政商勾結的一些黑幕。江西官員私下談論中一個廣為流傳的說法是:蘇榮被查后所交代的問題至少牽涉數十名江西現任官員,其中包括大約20名廳級以上干部。
在窩案高發、串案迭出的現實情況下,如何凈化官員“三圈”,已成為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話題。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制度反腐專家任建明曾提出一個疑問:“那么多高級干部因為腐敗問題而落馬,并且都已經‘病情較重。人們不禁要問,為何一出就是大案、窩案?預防機制到哪里去了?”
近些年,對于官員的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該不該納入監督范圍,存有一些爭議。持贊成態度的觀點認為,凈化官員的“三圈”,單靠其自身努力顯然遠遠不夠,作為對干部監督負有管理職責的各級組織,必須積極作為。持質疑態度的觀點則認為,作為公民,官員的隱私權也應當得到尊重,組織不應干涉其私人生活,打擾其私人空間。況且官員的社會交往對聯系群眾、廣交朋友、調整身心等方面具有不可否認的積極作用。若有負面影響和消極作用,則是領導干部個人自律問題,應由自己承擔責任。
湖南省委黨校黨建部教授冷福榜認為,因為一些官員的“圈子”確實存在許多不健康、不純潔、不上進的東西,不但有必要加強監督與管理,而且應當理直氣壯。“其意義在于,有利于及時發現問題,糾正遏制腐敗之風。”
任建明認為:“官員的個人交往應該納入監督和管理的范圍,這是毫無疑義的。因為如果官員掌握的權力不正當地發揮影響,就會給一些企業、人士帶來不正當利益。所以,對官員的交往,特別是官員和企業人士間的交往,應該嚴格監督管理。”
“我認為造成自己腐化變質墮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改造。但監督機制沒有很好地落實和嚴格執行,也是一個客觀原因。”因受賄罪落馬的海南省東方市委原副書記吳苗在接受審訊時如是說。
有評論指出,形成于計劃經濟時期的干部監督模式,是為監督領導干部的工作圈而設計的。在當時條件下,領導干部在生活圈、社交圈出問題的很少。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隨著經濟成分、利益主體、生活方式、價值取向的日趨多樣化,人們的對外交往逐步增加,在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出問題的領導干部越來越多。
某省巡視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員認為:“近些年的干部監督存在三個突出問題。一是上級監督如同‘霧里看花,監督權時隱時現。二是同級監督普遍‘縮手縮腳,監督權軟弱無力。三是群眾監督好像‘水中望月,監督權形同虛設。從巡視工作所反映的情況看,干部監督的積極性和有效性往往來自于群眾,在加強對領導干部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監督的過程中,應該讓廣大群眾真正成為監督主體。靠組織監督干部八小時以外的情況是不現實的,根本管不過來。要相信‘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這句話,無數群眾的眼睛可以構成一張嚴密的社會監督網絡,及時發現領導干部‘三圈的異常表現。”
時事評論員曉理認為,讓群眾真正成為監督主體的條件目前已經“水到渠成”——其一,黨中央反腐敗的堅定態度,讓許多觀望者有了參與反腐敗的愿望,并樂于付諸行動;其二,以智能手機為代表的即時信息傳播工具的普遍應用,給群眾提供了開展監督的必備條件,使實時監督成為可能;其三,隨著民主、法治意識的深入人心,社會公眾的是非判斷力必然“水漲船高”,“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狹隘心理會不斷淡化;其四,黨務政務信息公開、官員重要信息公開,已經成為大勢所趨的時代潮流,不可回避,無法阻擋。
在公眾監督方面,國外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鑒。譬如,在以色列,為增強公權運行的透明度,民間成立了旨在監督政府的“第三只眼”組織,專門曝光官員的不法行為,致力于提高政府及其工作人員的廉政水平。
“監督領導干部的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必須抓住發現問題的切入點。從現實情況看,在領導干部操辦婚喪嫁娶事宜或者遇有其他家庭重要事件時,比如家人住院、老人壽誕、孩子升學、喬遷新居等等,能比較充分地反映其‘三圈情況。因此,應當進一步完善領導干部個人重大事項公開制,同時注重研究探索針對這些時間節點和重要事項的監督措施。對于那些只具有象征意義的所謂監督制度,應當從可操作性和實效性的角度思考改進,不能搞花拳繡腿的假把式。”哈爾濱市紀委一位中層干部這樣認為。
如何改進監督方式,從而增強監督的有效性,是實際操作中的一個難點。一些黨建學者圍繞這個問題提出了各種建議,歸納起來大致有這樣幾個方面:一是變在工作中監督為走出辦公室監督,采用下發監督卡、設立舉報箱、舉報電話以及談話、走訪、調查等方式,主動掌握官員“三圈”交往中的異常情況線索。二是切實執行告誡談話制度。對于群眾反映的問題,應當及時對相關干部進行談話提示,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并做好《領導干部“三圈”談心談話記錄》。三是推行公開承諾,要求領導干部就八小時以外可能出現違紀問題的相關事項,向單位組織和干部群眾做出公開承諾。
一位長期從事組織工作的退休干部認為,近些年對干部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的考核已經普遍實行,但流于形式、隔靴搔癢的問題尚難以解決。在以法治思維反腐敗的大趨勢下,應當在依法的前提下積極探索切實可行、行之有效的方式。譬如,中紀委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全面推行廉政風險防控管理及行政權力、公共服務公開透明運行,積極推廣“制度+科技”等預防腐敗經驗,這應當是與時俱進的一個基本方向。
公務員回避制度為“防止以權謀私”和“阻斷人情關系”提供了制度保證,但如何才能落到實處、收到實效,是操作中的一個難點。目前,回避的主要形式有親屬回避、公務回避、地域回避。
“在三大回避制度中,地域回避、任職回避的制度設計不可謂不精致,而公務回避的制度設計卻粗糙不堪。”上海市委黨校教授陳保中曾通過《學習時報》闡明自己的觀點。他舉例說,比如《公務員法》僅以“利害關系”、“其他可能影響公正執行公務”等諸如此類模糊術語作為法定公務回避的條件,遠未涵蓋其他更值得討論的情形,如朋友關系、偏見因素、接受吃請及其他單方面接觸行為等。
國家行政學院社會和文化教研部教授程萍在《人民論壇》雜志刊文指出,中國有著幾千年來形成的人情文化。“在人情文化成為社會主流文化的背景下,公務員回避制度雖然明確地就親屬關系、地域關系對公職的影響做了制度約束,但親屬關系之外的同學、師長、朋友等社會關系,仍然是一張難以撕破的人情網,這需要引起重視。”
那么,國家公職人員在任職回避范圍上能否周延到同學、老鄉、戰友、老部下等特殊關系,一些地方正在進行探索。如上海市高級法院與上海市司法局聯合規定,案件承辦法官與當事人的律師,有夫妻、父母、子女或同胞兄弟姐妹關系,或有同學、師生、曾經同事等關系可能影響案件公正審判的,必須自行申請回避。
據《中國青年報》報道,截至2014年3月5日,在十八大后掀起的反腐風暴中,有22名省部級以上高官落馬。值得注意的是,這22只“老虎”都有在同一省份或同一領域長期工作的經歷,同地任職的平均時長達31年。
有評論指出,在同一地域或系統工作時間長,難免形成盤根錯節的人脈關系網絡。這樣的關系網絡,在一些貪腐官員那里經常演變成為利益網——官員與官員之間、官員與富商之間形成利益共同體,相互輸送利益,成為政商同盟。
那么,怎樣才能瓦解已經抱成團、結成盟的“官場圈子”?中國人民大學反腐敗與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暉教授認為,正所謂“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要根據腐敗同盟的結構特點來促進分化、精準打擊。
“突破腐敗同盟的有效路徑之一,就是完善官員的輪崗轉崗制度,對掌握豐裕政治資源和經濟資源的官員,實行大跨度、高頻率的科學化輪崗轉崗制度,分解腐敗同盟的向心力,促使其碎片化。”毛昭暉說。
對于干部交流制度的未來,國家行政學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認為,隨著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干部任命的規范化、制度化應當成為主流。相應地,干部交流制度也會與時俱進,做出相應的改善和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