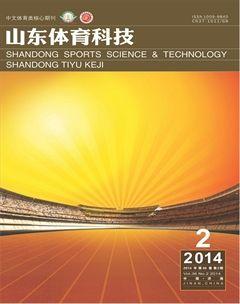基于美、澳經(jīng)驗探析法律在推動女性參與精英體育中的作用
劉向應 張海茹
摘要:從世界范圍看,女性參與體育運動的機會已經(jīng)大大增加,這種增長大多歸功于近年來各國法律以及國際法所做出的一些改變。根據(jù)美國、澳大利亞兩個國家的實踐,探析法律在推動女性參與高水平競技體育過程中的作用。研究發(fā)現(xiàn),盡管各國的法律和官僚機制還存在進一步改進的空間,但婦女在精英體育中的參與度確實有所增加,應該以此來審視依賴法律的“自由女權(quán)主義”在推動女性參加體育運動機會中所起到的所謂決定性作用。
關(guān)鍵詞:法律;自由女權(quán)主義;精英體育;女性
中圖分類號:G80-05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9840(2014)02-0022-04
收稿日期:2013-12-09
作者簡介:劉向應(1963-),男,講師,研究方向體育教育訓練學。
奧運會、世界杯足球賽等國際大賽能夠團結(jié)分裂的國家,融合差異的文化,創(chuàng)造持久的標志性圖像……這其中,女性參與高水平的競技比賽也是很多人所期待和預期的。雖然目前女性參與精英體育的數(shù)量還不能等同于男性,但是從參加夏季奧運會的女性運動員的比例可以發(fā)現(xiàn):1980年有21.5%的參賽運動員是女性,到了2004年雅典奧運會這一數(shù)字變成了41.7%;冬季奧運會也有著類似的增長,從24.4%上升到38.3%[1]。隨著女性參與體育運動和大型國際賽事地逐漸增多,一些國家也開始把此歸功于國家和國際的法律做出地改變和推進。但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目前學術(shù)研究較少關(guān)注或分析諸如法律這樣的具體的國家行動的作用。本文旨在從這一角度出發(fā),來研究法律以及相關(guān)的行政政策是如何影響女性參與精英體育的。
法律,尤其是立法、司法手段是社會變革、社會再造過程中非常重要的要素,也是一個自由民主社會基本原則的具體體現(xiàn),還是自由女權(quán)主義的重要特征。自由女權(quán)主義活動家們推崇的是法律和政策層面的變革,這種變革可以或明或暗地禁止、限制或者形成女性的機會、女性選擇的權(quán)利,自由女權(quán)主義十分崇尚促進婦女權(quán)利的法律[2]。他們希望,一旦政策改變,一些有利于實現(xiàn)性別平等和提高女性地位的元素就有可能實現(xiàn),起到一種所謂的疫苗的功能。比如一項研究專門把1963年到1997年之間62個國家和地區(qū)處理有關(guān)工資的性別差異的法律進行了梳理,得出的結(jié)論就是這些法律的出臺對提高女性的收入和降低工資的性別差距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目前來講,要了解對女性參與精英體育產(chǎn)生影響的法律,主要是要參照一些國際上有關(guān)性別平等的原則性文件,特別是在《奧林匹克憲章》中以及聯(lián)合國“關(guān)于終止一切形式的歧視的公約”。目前,效果比較顯著的案例主要是以下兩個國家——美國和澳大利亞。就美國而言,本研究選擇“第九篇”(“TITLE IX”)作為個案進行分析,這是一項于1972年頒布的教育修正案,是針對在教育機構(gòu)背景下禁止歧視女孩、減少女性運動機會的一個法律文件。相反,澳大利亞1984年《性別歧視法案》的第42條,則可以解釋為是在允許體育運動機會上的性別歧視的存在。不同于自由女權(quán)主義過分信賴法律作為推動社會執(zhí)行力的立場,本研究將討論法律作為改變女性參與精英體育的一種社會變革的主要手段的局限性。
1國際性的法律原則或聲明:奧運會和聯(lián)合國的考察
目前,恐怕沒有哪個領(lǐng)域比現(xiàn)代奧林匹克運動更加明顯地體現(xiàn)出體育、法律與性別之間的關(guān)系了,特別是國際奧委會更是有權(quán)直接負責解釋、倡導體育運動的性別平等。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是一個國際性的非政府組織、非營利性組織,它作為奧林匹克運動的監(jiān)管機構(gòu),負責解釋和執(zhí)行官方的奧林匹克憲章。當然,國際奧委會章程是逐漸才認識到需要借助法律文件來禁止體育當中的性別歧視。1884年,顧拜旦復興奧運會并編寫了《奧林匹克憲章》作為治理規(guī)則。當時,他宣稱奧林匹克運動是“莊嚴的,是以國際主義為基礎(chǔ),旨在提高人類(男性)的運動崇尚,以忠誠為手段,以藝術(shù)為支持,以女性的掌聲作為獎勵”。16年以后,女性才被允許參加奧運賽事,而且一直到1928年還不允許參加田徑比賽這項最古老的奧運會比賽。而直到1988年,《奧林匹克憲章》第28條才要求國際奧委會立文批準女性參加比賽。事實上,“批準”這樣的規(guī)則就沒有出現(xiàn)在對男性運動員的規(guī)定中。最后,是在2004年《奧林匹克憲章》明確禁止性別歧視。第4條中提到:體育實踐是個人的人權(quán)。每一個人都要有參與體育實踐的可能性,不應該有任何形式的歧視,在奧林匹克精神中,需要的是相互了解與友誼情誼,需要團結(jié)和公平競賽的精神。第5條則直接針對性別歧視問題:任何形式的歧視,無論是對國家、對種族或者出于宗教、政治、性別以及其他原因,與奧林匹克運動都是極不匹配的。
國際奧委會修訂憲章之前和修訂之后的這些憲章內(nèi)容其實一直都被詬病為缺乏適當?shù)膱?zhí)法機制,但這也是作為非營利性組織的國際奧委會的結(jié)構(gòu)性缺陷,因此,雖然國際奧委會可能會通過國際性的體育規(guī)章強調(diào)性別平等,但是它沒有任何禁止具體參加奧林匹克國家的辦法,沒有手段來解決或者制裁性別平等失敗的案例。目前來講,這些國際奧委會的命令的有效性最終還是要依靠國際奧委會成員國對《奧林匹克憲章》的理解、解釋和執(zhí)行的愿望。也就是說,雖然國際奧委會所處的位置是國際體育規(guī)章最主要的官方機構(gòu),但是還有公認為國際慣例、國際法律來直接解決女性參與體育運動規(guī)定的問題,比如《聯(lián)合國海洋法公約》關(guān)于消除對女性歧視公約中就規(guī)定:各締約國應該采取一切適當?shù)拇胧龑ε缘钠缫暎⒈WC女性與男子享有平等的教育的權(quán)利,特別是要確保在男女平等的基礎(chǔ)上,女性有同樣的機會參加體育運動,接受體育教育。目前已經(jīng)有180多個國家簽署“關(guān)于終止一切形式的歧視的公約”。雖然所有的國家都簽署了這一正式的約束性的規(guī)定,但是就像國際奧林匹克憲章的實施一樣,還是沒有國家因為違反規(guī)定而被追究責任。
2“第九篇”:美國的經(jīng)驗
美國體育在很多方面的做法都值得贊同和學習,特別是在精英體育這個層面。在1900年的巴黎奧運會上就有美國的女運動員參賽,這是第一次向女性開放的奧運會,女性體育在精英體育這個層面的蓬勃發(fā)展,部分要歸功于美國女運動員的積極參與。美國的女性通常在年紀很小時便開始參與體育運動,然后經(jīng)過小學和中學的體育教育系統(tǒng)學習訓練。學校主要是作為向運動員提供訓練場地的載體,以及充當一個過濾器,把高水平的運動員輸送到下一個更高級別的比賽中,也就是說,最好的初中運動員會被送到高中隊,而最有運動能力、技能最熟練的那些運動員則會升入到大學水平中去競爭。高校則往往作為專業(yè)運動員、職業(yè)運動員的訓練基地。同時,還具有選拔潛在奧運健兒、訓練奧運選手的大本營的功能。正因如此,大學中的女性體育運動參與對精英層面的美國女運動員的參與和成功影響非常巨大。考慮到這需要一個龐大而充滿活力的基礎(chǔ),所以一般一個體育運動的參與者最終要成為精英運動員,成為職業(yè)運動員,通常要有15到20年的時間,而在這樣的一個時間段里,需要教練特別是明星教練的支持,以及相應的體育設(shè)施、體育獎學金、體育比賽機會等等,所以高中體育、大學體育和精英層面的體育比賽之間的聯(lián)系是十分明確的。比如在2012年倫敦奧運會,美國的女運動員參加了26個大項,其中一大半都是由美國大學生體育協(xié)會(NCAA)來負責支持的,美國大學生體育協(xié)會則名副其實地成為美國大學競技體育最大的監(jiān)管機構(gòu)。單就美國大學的體育課程而言,奧運會女子比賽項目中的一半以上都有出現(xiàn)在美國的大學中,并有專門的女運動員從事訓練。
美國女性體育運動之所以有高參與率以及在國際體育賽事中的成功表現(xiàn),最重要一點便是受到1972年通過的《教育法第九篇修正案》(簡稱“第九篇”)的有效介入。這個法律被認為是關(guān)于女性、體育以及平等機會的核心法律。“第九篇”中提到:任何一個美國人都不應該因為性別的理由,被排除在參與、享受教育計劃以及聯(lián)邦財政援助的福祉之外,或者受到歧視。這一法律通過以后,緊接著的問題便是體育和經(jīng)濟是否應該被包含在教育機構(gòu)范圍內(nèi)以受到該法律的保護呢?答案是肯定的。
從1972年開始,美國絕大多數(shù)涉及到婦女和體育的法律及行政規(guī)章都與“第九篇”有關(guān),聯(lián)邦行政機構(gòu)如衛(wèi)生、教育和福利部、民權(quán)辦公室,都分別明確了教育機構(gòu)要遵守該項法律。這些法規(guī)包括了為男女運動員發(fā)放獎學金的規(guī)定,還有教育機構(gòu)要基于性別平等來設(shè)置課程的規(guī)定以及學校如何適應和衡量不同性別學生興趣和能力。
這些規(guī)定也導致了一些重大的起訴以及美國國會法案,并且通常都是嘗試限制或減少“第九篇”中這種對平等的指令。例如,可不可以以經(jīng)營收入來生產(chǎn)體育?也就是說,一些通常是男性主導的體育比賽如籃球和橄欖球,它們可以通過門票收入來維持成本,那么它們是否可以免除在適用“第九篇”規(guī)定的機構(gòu)之外呢?如果一所學校獲得了很大一筆的私人捐贈來支持這個學校的男性主導的體育運動,那么它必須要再提供一個類似的贊助女運動員的項目嗎?還有,男運動員在“第九篇”的規(guī)定下,能不能起訴因為一些機構(gòu)為了維持性別平衡而削弱對男子運動員的支持?什么類型的執(zhí)法機制是可行的并且有效用的呢?這許多的問題已經(jīng)給美國聯(lián)邦法院處理性別平等與體育的案例積累了足夠長時間的先例,但很少有被梳理清楚的,他們?nèi)匀皇橇艚o未來的訴訟。
雖然目前女性參與體育運動的機會依然無法與男性完全平等,但是在“第九篇”出臺后的40多年時間里,女性參與有組織的體育運動的參與率已經(jīng)大大增加,1971年,美國高中田徑代表隊中只有7%的女性運動員,而如今這一比例已經(jīng)超過了40%;在大學水平的女性,參與人數(shù)更是超過了高中[3]。雖然“第九篇”是一個有爭議的立法,但它仍然被許多人認為是能夠促進美國女性體育運動興趣的提升,并在一些國際高水平的競技比賽中取得佳績的最主要的貢獻因子。
3“第42條”:澳大利亞的經(jīng)驗
在澳大利亞,婦女參與精英體育的形態(tài)演變是由官僚體系、法律行動等因素共同主導的。目前澳大利亞加入的兩個國際公約,主要是簽訂于1994年布萊頓婦女與體育宣言,以及1998年的溫德和克呼吁行動。而在1983年7月28日,澳大利亞成為了“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的締約國成員,按照締約規(guī)定,簽署國要采取積極的措施以確保性別平等。第二年,澳大利亞就通過了性別歧視法。這個聯(lián)邦反歧視法包括了很多備受爭議之處,特別是關(guān)于女性體育運動的問題。雖然該法律第42條規(guī)定,如果以性別的理由排除一個人參與任何競技性的體育運動,都將是不合法的。但是法律中也規(guī)定了一些例外情況,比如其中一個例外條款便是“可以不讓12歲以上的人參與對力量、耐力或體質(zhì)有較高要求的運動項目”;這種表述被很多人批評是在暗指女性太嬌嫩,太容易受傷,也無法勝任激烈的身體競爭,帶有對女性刻板的負面思想的意識形態(tài)。
在現(xiàn)實中,“第42條”規(guī)定有一些活生生的受到挑戰(zhàn)的例子,最著名的例子發(fā)生在2001年。這個案件涉及一名成年女性職業(yè)拳擊手,路易斯·費茉莉,她申請正式的拳擊注冊被拒絕,而拒絕的理由就是因為她的性別。法院的判決理由是拳擊手注冊登記的法規(guī)是專門針對男性拳擊手的。在路易斯·費茉莉接下來的官司中,她認為性別歧視法應該對所有形式的婦女歧視生效,應該禁止性別歧視,“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所載權(quán)利目的是適用于整個澳大利亞,并且保障婦女們在與男性平等的基礎(chǔ)上被對待,澳大利亞應該強制性的取消這樣的歧視性法規(guī)和其他阻止男女平等活動的行動壁壘。審判結(jié)束時,法庭駁回了路易斯·費茉莉的起訴,禁止她注冊成為拳擊手,隨后路易斯·費茉莉又提起上訴,但同樣也被駁回。表面上,這一決定僅僅是依據(jù)“婦女的力量、體能和體質(zhì)”而做出的。然而,這種決策實際上受到了這項法規(guī)在立法前的一場討論的影響頗大。在之前的一場討論中,新南威爾士州體育部長曾說:“根據(jù)這項立法,女性將不會被允許作為拳擊手,無論是業(yè)余的還是職業(yè)的,部分原因是因為在我們這個社會根本沒有幾個人會接受兩個女性相互攻擊的景象,此外,婦女在這項運動中所承擔的風險也會比男性更多,其中一個風險就是女性會變成怪胎,甚至可以說是古羅馬血腥競技以體育競賽所做的某種偽裝”。
這種情緒表達出一種理念,就是至少有一部分立法機關(guān)是在保護女性的女子氣質(zhì),甚至是從女性本身考慮的這一問題,為的是防范那些威脅到女子氣質(zhì)的東西把女性變成“奇觀”、“怪胎”。通過拒絕路易斯·費茉莉的申訴,澳大利亞當?shù)卣赃@樣一種方式來防止女性參與到體育運動中,他們的理由是廣大市民還沒有準備好觀看一場侵略性強、充滿暴力和力量的女人之間的表演。
這樣的思想觀點表明澳大利亞法律的意圖以及社會變革的欲求都是十分明確的。該法案旨在禁止基于性別的歧視,包含覆蓋了澳大利亞社會生活的各個領(lǐng)域,但體育除外。因為在這樣一個舞臺上,人們會認為平等可能成為“不女人”的代名詞。澳大利亞的法律以這樣的一種方式勸阻、而不是非常明顯地防止女性參與一些體育運動。當然,我們也不能就此定論,因為男女平等參與體育的裁決往往比較復雜,充滿變數(shù)。比如雖然女性已經(jīng)被禁止從事拳擊以及澳式橄欖球這樣的比賽,但她們已經(jīng)獲準參加如草地保齡球這樣的體育活動,這些裁決表明要想得到“第42條”一句蓋棺定論的話,至少現(xiàn)在還不是最佳時機。
不論有沒有一個具體的具有潛在負面影響的法律,還是隨之而有的法院的司法解釋,澳大利亞女運動員在代表國家出戰(zhàn)的國際精英體育賽事中還是取得了很大成功的。澳大利亞在英聯(lián)邦運動會上的成績一直名列前茅,女運動員共參加了200多次不同比賽,一共贏得過百枚的獎牌。澳大利亞參加了自1912年以來的歷屆奧運會,在1948年到1996年之間,澳大利亞代表團中平均只有26%的女運動員,但卻贏得了澳大利亞75%的獎牌[4]。澳大利亞女運動員在國際高水平競技比賽中的表現(xiàn)一直都十分突出,尤其是在游泳比賽方面,澳大利亞女子游泳運動員總是不斷挑戰(zhàn)世界紀錄,收獲獎牌。
非政府組織和政府行政機構(gòu)在促進澳大利亞女子體育方面充當了排頭兵和引路人的角色。“婦女體育澳大利亞”(Women Sport Austrialia)是該國最大的非政府體育組織之一,致力于女子體育的進步。實際上,這個非政府組織是一個宣傳機構(gòu),它不以營利為目的,目的只是為了加強體育運動和健康生活的環(huán)境建設(shè),讓女性有更多的機會和途徑參與到體育和娛樂活動中。它試圖通過倡導政策變革,發(fā)起健康體適能課程方案以及研究具體項目來實現(xiàn)它的這些目標。“婦女體育澳大利亞”與兩個政府體育組織合作密切,分別是澳大利亞體育委員會和澳大利亞體育學院(ASC和AIS)。
1989年澳大利亞體育委員會法案正式提出,作為澳大利亞政府的一個分支,澳大利亞體育委員會作為澳大利亞體育系統(tǒng)的基石。為了實現(xiàn)國家體育政策,澳大利亞體育委員會也是將目光聚焦在兩個方面:1)基層體育參與;2)精英運動員的開發(fā)。從一開始,它就把婦女與體育平等納入到整個國家體育計劃中,這個國家體育計劃則與國內(nèi)和國際上的非政府組織一起解決諸如體育團體的合并、體育中的性騷擾、運動訓練指導、場館設(shè)施改善、資源質(zhì)量以及提高女性在領(lǐng)導崗位上的人數(shù)等問題。
與澳大利亞體育委員會相配套的則是澳大利亞體育學院,它專門負責提供獎學金,使運動員可以專注于運動訓練和體育發(fā)展。在其它國家女運動員還要因為生計在工作學習之余訓練時,澳大利亞的許多精英運動員卻可以得到必要的資源支持,并可以將大量的精力投入到訓練當中。2006年,澳大利亞體育學院提供了35個單獨的方案,向大約700名運動員提供獎學金,涵蓋了26個運動項目。而且,在澳大利亞最強的620名奧運代表國成員中有一半以上都是現(xiàn)任或前任的AIS的運動員[5]。澳大利亞體育學院就是以這樣一種結(jié)構(gòu)和組織框架,以這樣一種方式,在一個運動員年齡很小時就識別其成為精英運動員的潛力,并把他(她)注冊到澳大利亞體育學院的培訓計劃中。
這樣一種框架的結(jié)果就是彌補了“第42條”法規(guī)造成的體育參與的性別歧視,特別是12歲以上的女性,澳大利亞體育領(lǐng)域這種行政體系和結(jié)構(gòu)很好地促進了本地青少年廣泛地參與體育,也為精英女性運動員參與成人的國際體育比賽提供了一種手段。因此,法律和國家的官僚體系、行政結(jié)構(gòu)結(jié)合起來進行,可能首先鼓勵女性早期即12歲之前廣泛的參與到體育運動之中,然后隨著年齡的增長再根據(jù)對女性氣質(zhì)的傳統(tǒng)觀念,根據(jù)體育運動項目的實際特點來過濾、篩選有選擇的參與到更加專業(yè)、更精英的運動中。
4結(jié)論
研究表明,盡管經(jīng)歷了立法、失敗以及消極的解釋等等一系列的問題,或者是缺乏具體的關(guān)于體育的性別平等的法律法規(guī),實施女性參與體育運動、參加精英體育賽事的方式和途徑還是很多的,并且在許多情況下呈現(xiàn)出了蓬勃發(fā)展的跡象。雖然自由女權(quán)主義追求性別平等的倡導和努力也帶來了女性參與體育機會的增多,但現(xiàn)實情況卻存在很多阻礙做出這樣選擇的因素。例如,以目前的法律策略來解決男女體育平等的問題,往往是以一種“并行”的態(tài)度來要求男性和女性的進步和改善。這樣一來,像澳大利亞的“性別歧視法”就應該受到批評,因為男女運動員應該被允許互相競爭。在一些體育比賽中,女性的條件和表現(xiàn)也有可能優(yōu)于男性,因此,這里面本身就有一種先入為主的人為傳統(tǒng)觀念,即女性在參與體育比賽上的品質(zhì)是劣于男性的。此外,我們還可以質(zhì)疑自由女權(quán)主義這種親“法”策略,比如女性與女性之間的差異: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希望以同樣的方式打球,或者都希望參加國際比賽。自由女權(quán)主義的策略要求一個國家的運動隊要性別平衡,但這種機械式的強求,反而忽略了女運動員真正的偏好。依賴法律的重點不在于只集中在法律本身上,過分的集中于具體的法律,希望以此提高女性參與體育的機會,只會把這種希望變得更大、更抽象。法律也有一個時效性問題,隨著法律的出臺和世界的發(fā)展變化,像美國“第九篇”已經(jīng)導致多次的起訴以及一般公眾對法律的誤解,所以法律帶來的也不全都是積極的推進女性參與精英體育的作用。相反,如在澳大利亞那般的官僚機構(gòu)(澳大利亞體育委員會和澳大利亞體育學院),它們和非政府組織一起,盡管沒有集中于法律問題,但也確實地提高了女性參與體育運動與參加精英體育的機會。
參考文獻:
[1]Buren J, King B, and Lopiano D. 100 Women – 100 Sport[M]. New York: Bulfinch,2004.
[2]趙明.女權(quán)主義法學的性別平等觀對中國立法的啟示[J].婦女研究論叢,2009,(3):10-15.
[3]National 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 (NCAA) NCAA Year-By-Year Sports Participation 1982–2001[R].NCAA, 2002.
[4]Australian Sports Commission (ASC) .Australian Sports Commission Overview: Our mission is to enrich the lives of all Australians through sport. [EB/OL].2006-10-27. http://www.ausport.gov.au/asc/index.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