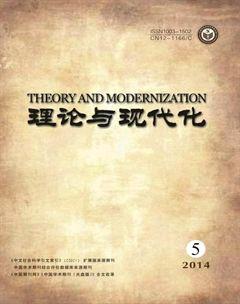論先秦儒家政治倫理思想中的“和”與“分”
康宇
摘 要:“和”與“分”是先秦儒家政治倫理思想中的重要范疇。在政治生活中,“和”可具體化為“人和”、“政和”與“共和”,“分”可操作化為“名分”、“職分”等。“和”、“分”看似一對相對立的范疇,實則彼此間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它們擁有共同的理論基礎、相似的人性假設以及一致的客觀效果。它們是先秦儒家“道德理想主義”與“倫理中心主義”思維理念的集中體現。其內含的真知灼見,對當代社會政治文明建設亦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
關鍵詞: 政治倫理;先秦;和;分
中圖分類號:B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1502(2014)05-0056-07
先秦時期,儒家政治倫理思想得到了迅速發展。自孔子提出“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確立了儒家德治思想的基本理念后。孟子、荀子先后又做了發揮,創造出“為政以德”、“德法并重”等一系列統治道德規范原則。進而,建構出以“仁義”為核心,強調以德為尚、民為邦本的“王道”倫理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和”與“分”兩個范疇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先秦儒家“和”與“分”范疇內涵及其在政治倫理思想中的運用
在先秦儒家看來,“和”是一種形上本體。《中庸》上說:“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即“和”是天地萬物的根本,與“道”有著異曲同工之妙。自然世界與社會人事都應遵循“和”的規律與指向。但對于普通個體而言,“和”又可落實為一種道德品質。“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人際關系和諧是禮法有效應用的根基,是社會秩序穩定、安寧的保障;“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君子與小人的重要區別是,君子能“以和待人”,寬容處事但不隨波逐流,小人則恰恰相反。《中庸》也講:“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所謂 “中節”是說由對道德準則的恰當把握而完全符合,即“和”是個體行為、語言的標準,是個體內在道德修養與社會外在倫理控制共同要達到的效果。
如何實現“和”呢?先秦儒家設計的路線是:其一,每個人都要“安分守己”,自覺固守自己所處的等級地位,并完成自己應盡的責任。如孔子總結的那樣,“道之將行也與,命也”(《論語·憲問》),“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論語·堯曰》)只有知命、安命,人們才能不違背已有的等級區分,在“無爭”中“盡倫盡責”,以達到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自身的諸多和諧。其二,在“和”的過程中,要做到“和而不同”、“和而不流”。“和”不是“同一”,而是對立中的統一,它應建立在差異性的基礎上。故荀子提出“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荀子·子道》)的關系原則。同時,也不要因為“和”,為取悅他人和世俗而不斷改變自己的立場,不講原則。若“入流”,只能“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孟子·盡心下》)。
當“和”這一范疇具體化于政治倫理思想時,先秦儒家將之轉化為“人和”的社會管理理念、“政和”的政治制度安排,以及“共和”的奮斗理想。
“人和”指的是人際關系的和諧。孟子認為,“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孫丑下》) “人和”之所以會被看作比天時、地利更有價值、更為寶貴的要素,是因為它對于調節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緩和社會矛盾,避免社會發生過多的動蕩,保障社會生產的正常發展,促進社會穩定,起到了不可忽視的積極作用。[1]荀子的說法更為直接,“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荀子·王制》) “和”是規范人們行為的尺度,也是社會管理的目的。只有“貴人和”,人際交往、社會秩序方可和諧。
為了實現“人和”,統治者要做出表率,“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論語·子路》)只有君主禮、義、信,臣民才能敬、服、情,從而一個人們共同遵守特定行為規范,價值標準統一一致,情感相互依賴,少有矛盾沖突的“人和”社會才能實現。對于普通百姓而言,“人和”的標準就是要做到忠與信:為人“忠而有信”(《論語·學而》),處事“言必信,行必果”(《論語·子路》),言行相符。這樣才能達成彼此間相互信任、理解寬容、共同促進的和諧社會局面。孔子曾教導他的弟子說:“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論語·學而》)顯然,“人和”雖然是“王道”的目的,但它需要受到“禮”的節制。這里的“禮”,廣義地講是指典章制度,或曰一切社會規范及相應的節文儀式,狹義地說就是道德規范。荀子也強調:“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荀子·勸學》),“禮也者,貴者敬焉,老者孝焉,長者弟焉,幼者慈焉,賤者惠焉。”(《荀子·大略》)社會管理需要“人和”,但必須在“禮”的范圍內行事。究其原因,禮是先秦儒家哲學形上本體“仁”的具體體現與外在表達,“克己復禮為仁”(《論語·顏淵》)。“和”最終也是要實現“仁”的意義,故“人和”與“禮”之間也形成了內在聯結。
“政和”是說,社會秩序穩定,階層和睦,國治天下平的政治和諧狀況。孔子強調德治,孟子倡導仁政,其目的均是為了達成“政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孟子·公孫丑上》)。對于先秦儒家來說,將道德作為政治的根本綱領,并且要以統治者自身的道德去感化百姓,是政治倫理的客觀要求。若想鞏固統治,維護良好社會秩序,執政者必須以德服人,通過愛民、利民,征服民眾之心,“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威行,夫是之謂道德之威”(《荀子·強國》);以道德教化作為政治的手段,以仁愛之心獲得百姓認同和自覺擁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孟子·離婁上》)
在實踐中,首先要明確“民貴君輕”。所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離開了民,君只能成為孤家寡人。君主只有利民、惠民,使民眾安居樂業,才可能真正讓社會和諧穩定。所以當子張請教孔子如何從政時,孔子要他“尊五美,屏四惡”,即尊崇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以惠民為首,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摒棄不教而殺、不戒視成、慢令致期、出納不吝,不進行教化而一味誅殺的暴政、虐政行為。孟子主張制民以產,省刑罰、薄稅斂,君主與民同樂。荀子要求“天立君以民”——君主是天為民興利除害所立,君主要時刻為民眾著想,愛護萬民,養育眾生。其次要構建“天下為公”的社會。“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禮記·禮運》),在這樣的社會里,君主講仁政,臣子秉公執法,百姓講誠信,天下一家、安寧和平。此外,社會還要形成選賢任能的賢能政治制度。孔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論語·子路》)孟子說:“尊賢使能,俊杰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愿立于朝矣。”(《孟子·公孫丑上》)荀子強調:“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荀子·君道》)顯然,賢能的任用已然是社會政治和諧的保障。至于如何去做,先秦儒家將之總結為:以德才兼備為賢能標準,官吏要積極薦賢舉能,國家要善于用才,大膽提拔人才,信任賢能。
“共和”準確地說是一種政治理想:社會乃是一個大同世界,“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諸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禮記·禮運》)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間“協和萬邦”。“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論語·顏淵》),“四海之內若一家”(《荀子·王制》)。在“共和”中,人自身、人與自然、人與家庭、人與社會間和諧共生,儒家天人合一、內圣外王的理想,得以充分實現。
與“和”相對,“分”范疇在先秦儒家視閾中也存在多重含義。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代表了等級“區分”;孟子說:“水信無分于東西,無分于上下乎?”(《孟子·告子上》)代表了認識論上的“差分”;荀子說:“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代表了社會角色意義上的“分工”;等等。而在政治倫理思想中,“分”這一范疇有著特定的指向——“名分”。
第一,“名分”指代著“君子”與“小人”的不同。“君子也者,小人之成名也”(《禮記·哀公問》),君子是尚德而成就美名的人,他志于道、重于行,有強烈的責任意識。“小人”是道德貧乏的人,其追求的是外在感官的滿足。“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論語·里仁》),“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孟子·滕文公上》)。對于“小人”來說,“君子”是他們道德的榜樣,所以在社會階層劃分上,君子為尊、小人為卑也就順理成章了。孔子說:“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論語·衛靈公》)在政治權力分配上,君子應為“勞心者”,小人應為“勞力者”。“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荀子·富國》),“德”與“力”間理應是“役”與“被役”的關系。“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論語·憲問》),對于“義”與“利”追求的不同,決定了君子與小人之間存在“上”、“下”的區分。因此,二者間有著本質的階層差異。
第二,“名分”突顯著“大人”與“小人”的差異。“大人”是先秦儒家所構建的理想人格模式。“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孟子·告子上》),“大人”重精神氣節,有獨立的道德意志,“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修身于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孟子·盡心上》)成為“大人”需要個體發揮仁義禮智之“心”充實自己,達到“正己而物正者也”(《孟子·告子上》)。與之相比,“小人”缺少“心”的思維能力,常用感官去認識外物,故只能受外物的蒙蔽。所以在社會職分排位上,“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義也。”(《孟子·滕文公上》)由于所具德性的不同,“大人”居于社會上層,“小人”只可居于社會下層。“大人”與“小人”的資質不同直接決定了其社會等級之分。
第三,即使是在“庶人”中,同樣存在“名分”。先秦儒家將“庶人”界定為地位低下的“民”階層,“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孟子·萬章下》)。“民”階層的特點是個體德才能力并非出眾,但卻構成了社會的主體。因此孔、孟、荀等十分重視對之進行德性培養,諸如“有教無類”(《論語·衛靈公》),“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孟子·盡心上》)等,并且進一步對“民”進行了類別劃分,提出“四民”說—— “士”、“農”、“工”、“商”。“四民”雖共屬“庶人”階層,但卻有著等級序列差異。“士”居“四民之首”,“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孟子·離婁下》),士雖然社會身份低于“大夫”,但潛在著向上流動至社會管理階層的可能性。“農”、“工”、“商”分屬三種性質不同的行業,這不僅是一種職業分工,更內含著等級上的區分。“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窌倉廩者,財之末也”(《荀子·富國》),也就是說,“農”為本,“工商”為末。
因為“四民”的等級位置不同,所以他們各自需盡的倫理義務亦有差異。“士”的角色要求是“學習道藝”,以成就德性、立身入仕為目標;“農”以生產勞動為業,其定位是“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論語·顏淵》);“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荀子·王霸》),“工”、“商”關乎 “力”,為“君子所役”,其要完成的主要任務是遵守社會秩序。對此,荀子做了總結:“故仁人在上,則農以力盡田,賈以察盡財,百工以巧盡械器,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盡官職。夫是之謂至平。”(《荀子·榮辱》)無論是“盡田”、“盡財”、“盡械器”還是“盡官職”,都有一個共同的責任——“盡分守職”。
二、作為政治倫理范疇的“和”、“分”關系及內涵剖析
在先秦儒家政治倫理思想中,“和” 與“分”看似一對相對立的范疇,實則彼此間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
首先,“和”與“分”有著共同的理論依據——天人同構。“天”是最高的倫理“本體”,其內含著“天道”,規定著萬物的運行規律;“人”是倫理的載體與道德行為的實際執行者,他所遵循的“人道”是人行為的客觀規律和人應當遵守的道德規范。“天”規定著“人”,“天道”制約著“人道”。天人之間彼此和諧是人自身得以順利發展,倫理世界秩序得以維護的根本保障。“天道”、“人道”在根本上是相通的,可外顯為“誠”,“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孟子·離婁上》)。而 “誠”又體現在“良心”上,“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中庸》),“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孟子·盡心上》)。“良心”是“天德”,在政治生活中可轉化為人倫規范與制度規則,它是天道與人道的統一。
然而,當“良心”落實于具體行為個體時又會出現“化性起偽”的可能,“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是性偽之分也。”(《荀子·性惡》)這種“性偽”實際上讓人與天在“合”的同時,又走向了“分”。此外,另一種情況同樣導致了“天人相分”,即“道”是普遍的,而作為天與人溝通樞紐的“禮”既是普遍的,又是具體的。“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荀子·禮論》)“道”是最基本、最基礎的原則,它無法被改變或者被否認。“禮”是具體的,其內在精神內核是“分”,它允許在各種關系和不同情境中出現不同的表現“道”的形式,它與特定的社會文化環境緊密聯系,或者受其制約。“道”需要諸多不同形式的“禮”做為體現,只有這樣才能符合道德情境與道德文化多元性和復雜性的要求。既然個體所習得的“禮”存在不同,那么形式上的“天人相分”也就具有了內在的合理性。
無論是“天人合一”還是“天人相分”,其基礎皆是人與天的對應。因此,“和”與“分”在本質上具有同根性。所以孔子、孟子在強調天道與人性同一時,又堅信個體對天道的感知、體悟差異是社會中政治地位尊卑上下之“分”的源泉,“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論語·憲問》),“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孟子·離婁下》)。荀子在大講天與人的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不同時,也強調“無性則偽之無所加,無偽則性不能自美。性偽合,然后成圣人之名”,“性偽合而天下治”(《荀子·禮論》),“分”的最終走向仍是“和”。
其次,“和”與“分”有著相似的人性假設指向。對于人性論問題,孔子提出“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的論斷,認為人具有共同的本性,但在后天發展中人性彼此不同。孟子進一步深化了孔子的看法,指出“人性善”是人的先驗本性,良知、良能是人心先天就具備的。由此,他提出“人性善”的理論假設。因為“人性善”,所以君主推行“善政”便會容易受到普通民眾的認同,“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于掌上”(《孟子·公孫丑上》)。而“為政以善”的直接結果,必然是臣民之和、天下之和,“為善必王”,天下必治。
與之不同,荀子將人性預設為“惡”。他說:“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矣”(《荀子·性惡》)。既然人性本惡,那么若任其發展不加約束,則人人均會趨利避害,造成社會動蕩不安。所以必須制定禮法,結合道德教育,使人“去惡從善”。踐行于政治生活中就是“以禮定分”:“ 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也”(《荀子·富國》)。故“禮”可以作為“道德之極”、“人倫盡矣”的規范體系,維護社會良性運行、和諧政治倫常秩序。以善德為基礎的“禮”,通過“分”確定了階層等級差別,從而使社會能夠實現“與天地同理,與萬世同久”(《荀子·王制》)的理想治世與萬物和諧的局面。由此可見,由“性惡”推出的“分”,絕非側重于突顯個人權利、義務的意義,而是從“和”的維系著眼,旨在追求社會有序與政治穩定。“和”與“分”對于人性假設的出發點雖不相同,但最終的指向均以道德維護政治,以確保“道統”的正常延續。
最后,“和”與“分”有著一致的客觀效果——“群”觀念的確立。荀子說:“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人具有社會性,它使人與人之間可以溝通、理解,形成“群”的合力。而在“群”的力量幫助下,人們可以戰勝自然,生存發展。從“和”的視角看,個人要有對整體利益負責的精神,對群體做出積極貢獻的意識。直接的做法即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衛靈公》)。通過推己及人的方式,達成人與人之間關系和諧,共同向上。要讓個體認識到,自己的尊嚴與價值只有在集體中才能得到最充分的突顯與保障,個體與個體間必須協同努力,以“群”之“和”促進社會發展。
從“分”的角度上講,則是人能“群”,因為有“分”,“分”定而“群”立。正是因為有“分”,人群秩序方得以確立,個體間方可和諧相處,“故人生不能無群,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故宮室不可得而居”(《荀子·王制》);因為有“分”,人的心理欲望得以控制,安于社會現實,“人倫并處,同求而異道,同欲而異知,生也。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異也,知愚分。勢同而知異,行私而無禍,縱欲而不窮,則民心奮而不可說也。如是,則知者未得治也,知者未得治則功名未成也,功名未成則群眾未縣也,群眾未縣則君臣未立也。無君以制臣,無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縱欲。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矣”(《荀子·富國》);因為有“分”,人的主觀能動性才能得到充分發揮,進而與他人和平共處,“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荀子·富國》)。
可見,通過“分”人際關系、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保持了協調、和諧,社會群體得到了統一,從而形成強大的力量,去戰勝外界,滿足人類整體的需要,“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荀子·王制》)從而使理想中的“政通人和”真正實現。
為了讓“和”與“分”的倫理觀念徹底地貫徹,先秦儒家在設計君主制度時頗下了一番功夫。從“分”出發,他們先確立了“禮”與“法”兩種社會控制方式。“禮”側重于禮義、道德規范等;“法”側重于刑罰等強制性手段。禮法各有自己獨立的調控范圍對象,“夫禮將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大戴禮·記禮察》)之后,他們明確了社會分層的意義。通過不同個體身份地位的差異,將世人以“禮”劃分為“貴賤有等,長幼有差”;通過德能衡量,劃定個體在社會大體系中應有的職分,“德以敘位,能以授官”(《荀子·致士》)。并且還制定出“禮賢下士”、“選賢舉才”、“使賢任能”的人才選拔制度。此外,他們還設定了社會利益分配制度。孔子說:“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論語·季氏》)這里的“均”即是按“差等”原則進行分配的一種形式。荀子講:“上賢祿天下,次賢祿一國,下賢祿田邑,愿患之民完衣食。”(《荀子·正論》)物質財富的分配一定要符合名分等級,等等。
從“和“出發,他們一再強調“尊卑有等”、“群而相宜”、“分而有序”等政治原則。所謂“尊卑有等”,即個體必須有“親親”、“尊尊”的意識:堅守家族內明確的親疏遠近、長幼順序,明確各自的道德義務,做到父慈子孝、夫義婦順;嚴格劃分國家政治領域中的尊卑貴賤等級秩序,不可逾越。同時讓“親親”與“尊尊”互通,使得“忠”、“孝”達成有機聯系,促成社會親如一家,但又等級分明。“群而相宜”是說,個體與社會相互和諧,群己關系融洽。個體要知道自己的生存與發展離不開群體的力量,故群體利益高于個人利益;群體的力量大小取決于社會是否有“分”,“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大利也”(《荀子·富國》)。“分而有序”要求“農農、士士、工工、商商”,每個人各盡其職,讓社會成為一個相互依賴、相互補充的整體。做為社會統治者、管理者的“德者”、“智者”、“能者”,與做為社會被統治、被管理的“小人”和諧相處、其樂融融。
為什么“和”與“分”兩個貌似不相關的范疇,在先秦儒家政治倫理中會形成如此緊密的聯系?剖析其本質,可以看出:“和”實際代表著一種道德理想主義,“分”實為倫理中心主義的體現。“和”是儒家一直追求的理想境界,是其政治倫理的內在精神;“分”是道德的現實實踐,是其政治倫理的外在表現。正如孔子、孟子、荀子等設計的那樣,人們在踐行“分”時,必需明確內在“和”的走向;奉行“名分”、“職分”時,必須以維護“人和”、“政和”、“共和”為目標。當然,“和”與“分”之間也存在張力。所以孔子等也強調,遵循“和”的原則并非一味求同,要在“分”中不斷培養人們“和”的意識。顯然,他們已經意識到社會強制性不只是被動地給定條件,而是主動地具有創造性的工具。如果沒有了“和”,“分”就成為空泛的形式主義,缺少了“和”的“分”也極易失去靈魂,從而破壞人類的美德情感。“和”與“分”的關系,可以用“理一分殊”的說法做出極好的解釋。“和”是普遍的、基本的原則,它無法被改變或否認,而“分”是具體的,是在復雜社會實存中不同的表達“和”的模式。“分”是為了更好的“和”,它也可以被認為是“和”的有機組成。
眾所周知,儒家政治哲學傳統講究“內圣外王”。從這個意義上考量“和”“分”關系,那么“和”就是一種“內圣”,“分”即是一種“外王”。“和”將天道、人性等內在要求展現得淋漓盡致,“分”則將抽象的政治倫理具體化,變得有操作性。前者是后者的根據,后者是前者的指向。至此可以斷定,“和”與“分”的不同,不是目的的差異,而是手段的區別;不是價值取向的分歧,而是方式途徑的多樣。
三、先秦儒家“和”、“分”思想對當代社會政治文明建設的啟示意義
先秦儒家政治倫理中的“和”、“分”思想直接影響了后世封建統治階級的統治思維與治國理念的形成,它與講究宗法等級、孝親尊君、安分守己的自然經濟社會的內在要求極為適應,在中國兩千余年封建社會政治發展歷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盡管時代的變遷已經讓其倫理內涵與外延的合法性受到質疑,其高揚的治世方略、統治秩序的合理性受到批判,其設計的政治理想與道德追求日益暴露出“空想性”的缺憾,但其內具的邏輯理性、辯證精神,對當代社會政治文明建設卻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
啟示之一:社會政治文明建設要以“民本”為基礎。從本質上講,“和”與“分”之間的對立統一,根源在于先秦儒家想要達成的政治目標是形成在“民本主義”基石上的“尊君”。“貴和”是政治秩序穩定、民眾集體歸屬感生成、社會成員凝聚力形成的前提,君主的統治能夠世代延續的根本。“和”的客觀效果必然要“尊君”,因為“天之立君,以為民也”(《荀子·大略》),君是天為民興利除害而設立的,“尊君”也就是“尊天”,也是對維持“和”做出的一種貢獻。“有分”的目的在于“安分”,進而讓人“無爭”,社會政治得以和諧。若讓人“有分”、“安分”,除了制度上的“名分”、理念上的“類分”外,統治者對于社會各階層的關愛也是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所以我們看到,孔子一面講“為政以德”,另一面也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一面認為“保民而王”(《孟子·梁惠王上》),另一面又強調“勞心者”與“勞力者”的不同分工。由此,尊君主張與民本理念的并存并行亦成為先秦儒家政治倫理思想的一大特質。
現代社會雖然社會實存已與幾千年前的先秦境況大不相同,但是同樣需要“和”、“分”有序的社會政治局面。“以民為本”必須作為一種“執政理念”被強調,作為一種歷史經驗總結被“揚棄”、升華。
啟示之二:社會政治倫理建構必須堅持美德與規則的統一。以美德倫理學的視角考量,“和”代表著美德,“分”代表著規則。“和”與“分”在道德評價中得到了統一。在先秦儒家看來,“和”是一種道德行為,是人人追求的修養目標。不過,在個體社會化的過程中,這種道德行為要融入到具體的“分”的道德規則中。由于存在“分”,所以人們要遵循“禮”。 “禮”不僅定義“道德”或適當的人的行為,它也限定了作為一個人的意義。簡單來說,“和”的道德行為不是由獨立于個人的社會關系的個體所實施的活動,而是由在各種具體社會關系中的人來實踐的。也就是說,社會中那些符合“和”的道德行為是在社會關系中實施的符合“分”的道德規則實現中完成的。
這樣一種兼顧“美德”與“規則”的“和”、“分”倫理關系構造,其積極意義是明顯的。它恰到好處地將個體的“終極關懷”與“底線倫理”統一起來,將道德行為與道德規則間可能存在的沖突,化解于“無形”中。現代社會政治倫理的建構同樣需要這樣的“兼顧”。當道德與法制、民主與專政發生矛盾時,“美德”與“規則”的辯證統一可以恰如其分地解決問題。
啟示之三:社會政治道德設計不可忽視“倫理生態”問題。作為一種文化,道德合法性的生成依賴于能夠被社會確證自身的存在現實性與價值合理性。“存在現實性”來源于道德的“實踐理性”,既受理性指導并得到理性確證,又具有轉化為現實的能力;“價值合理性”則源自道德與社會中其他要素的整合。上述二者的均衡問題又可統稱為“倫理生態”問題。
先秦儒家關于“和”、“分”倫理范疇的設計嚴格遵守著倫理與文化生態、倫理與經濟生態、倫理與社會生態等方面的均衡。它既賦予“和”以“天道”精神、“分”以“人道”理念,基于此規范天倫與人倫,又使讓人安身立命的智慧與文化自覺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既將“和”、“分”的政治倫理內化于社會職業倫理、交換倫理、分配倫理之中,又讓“道德生活”與“道德生活方式”整合統一;既以“和”彰顯政治上“德”-“得”相通原理,以“分”明確社會行為中的“必須”與“應當”,又讓秩序理性與民主品質相互和諧、共生共榮。
毫無疑問,正處于轉型期的當代社會政治生活需要充滿“文化理解”、能夠迎合并促進體制改革、躍遷的道德原則與道德規范。先秦儒家提供的“倫理生態”智慧高效、易行,實為可資借鑒的重要參照。
參考文獻:
[1] 張錫勤.中國傳統道德舉要[M].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6.250.
On the “Aggregation” and “Separation” of
Confucians Political Ethics in Qin Dynasty
Kang Yu
Abstract: “Aggregation” and “Separation” are important categories of Confucian Political Ethics in Qin Dynasty. In political life, “aggregation” may be embodied as “people”, “governance” and “republic”, while “separation” as “birthright”, “duty", etc. “Aggregation” and “Separation” seem a pair of opposed categories, but inextricably are linked to each other. They have common theoretical basis, similar assumptions of human nature and consistent objective results. They are Confucians “moral idealism” and embody the thinking philosophy of “ethical centrism”.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political civilization can gain enlightenment from them.
Keywords: Political ethics; Qin Dynasty; Aggregation; Separation
責任編輯:王之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