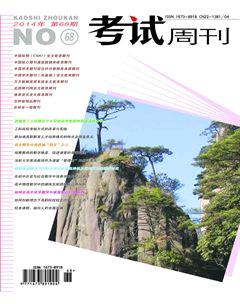約翰·契弗 《巨型收音機》 技術異化解析
梁意意 白陳英
摘 要: 文章分析了約翰·契弗短篇小說《巨型收音機》中的技術異化,揭示了人為自身創造物——收音機所限制和奴役的異化本質,探討了作者對處于豐裕社會技術異化進程中人們生存困境的深切憂慮,以期更深刻地領略作品的創作思想和藝術價值。
關鍵詞: 約翰·契弗 《巨型收音機》 技術異化
約翰·契弗(John Cheever,1912—1982年)是美國當代社會風尚小說家,尤以短篇小說創作見長, 榮獲過美國國家圖書獎和普利策獎等,在美國當代小說界大放異彩。短篇小說《巨型收音機》是其最出色、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小說中女主人公艾琳因為偶然通過新買的收音機竊聽到鄰居們日常生活隱私而沉溺其間變得一發不可收拾。她一邊探聽鄰居們的隱私,為他們表面上體面正派實際丑陋齷齪的生活感到震驚,一邊為自家的和諧幸福而擔憂,并對自己的生活是否會被鄰居窺探而變得瘋狂且不可理喻。契弗借助這臺神奇的收音機刻畫了現代科技社會中人的病態心理,展現了現代技術給人們帶來的精神空虛、恐懼與無助。
一
小說中的巨型收音機具有神奇的魔力。它對接收雜音有一種不應有的靈敏度,它播出的不是音樂,而是公寓大樓內左鄰右舍說話的聲音和一切私生活內幕:將朋友財產據為己有的丑惡行徑,為經濟困窘而產生的爭吵,女主人與勤雜工的私通,夫妻間性生活不協調,等等。作者稱其為“enormous radio”顯然不僅是指其強大的收聽功能,“enormous”除了表示“巨大的、龐大的”之外還含有“極惡的、兇暴的”之義。收音機其貌不揚,那丑陋的膠木匣子與艾琳家客廳里其他事物極不協調。當艾琳打開收音機時,調度盤馬上閃過一道惡狠狠的綠光,接著樂曲聲大得震耳欲聾,把桌子上的一個小瓷器擺設震到地上砰地碎了。這是否預示著收音機的到來可能會給主人帶來某種厄運?收音機發出的轟隆聲使艾琳感到很不舒服,而接下來它收聽鄰居們隱私的魔力更是將吉姆和艾琳·韋斯科特夫婦那看上去和諧、平靜的生活攪得一團糟。
收音機是科技的代表,小說所處的20世紀50年代正是美國科技蓬勃發展的黃金歲月,被稱為“原子時代”、“科技時代”或“后工業時代”。二戰后,傳統歐洲強國經濟崩潰,美國經濟則開始高速持續增長,美國迅速成為資本主義陣營的頭號強國。經濟實力的迅速增強帶動了科技的進步。任何人都無法否認技術對人類社會的貢獻,技術的發展大大提高了生產力,不斷創造新的產品,比如火車、飛機、汽車、電腦,等等,為人們的生活提供極大便利,推動社會發展。50年代,美國人生活水平已大幅度提高,收音機、電視機、洗衣機、冰箱、汽車等高檔商品紛紛進入普通家庭。機器取代了人力,人們有了更多休閑時間。小說中吉姆買回巨型收音機正是為了取悅妻子,讓其享受休閑娛樂時光。然而,收音機具有一種難以抗拒的強制力量,它使艾琳從此沉迷于竊聽他人隱私而卷入一場自身無法控制的瘋狂漩渦中。人類發明技術本來是要為其自身服務的,但是人類對技術的使用往往很難完全按照技術發明者的本意來進行。一方面,人類在應用技術的過程中,由于種種原因會出現技術的誤用。另一方面,人類在應用技術過程中涉及自身利益時往往會置他人利益于不顧。對此,馬克思曾精辟地指出,技術的勝利似乎是以道德的敗壞為代價換來的。人類愈有能力控制自然便愈益成為技術或別人的奴隸[1]。由于人對技術的不合理運用,人逐漸淪為技術的奴隸,而技術則成為控制人的主宰,這就是異化。
二
“異化”一詞源于拉丁文“alienatio”。在拉丁文里,它包含三種含義:一是在法學領域,意為轉讓,指權利和財產的讓渡;二是在社會學領域,意為個體同他人、國家和上帝相分離或疏遠;三是在醫藥和心理學領域,則指精神錯亂和精神病[2]。“異化”具有多義性和不明確性,一般指主體在發展過程中由于自身的活動而產生出自己的對立面——客體,成為一種外在的異己的力量反過來限制自身。19世紀德國的黑格爾(Georg Hegel,1770—1831年)首次把“異化”引入哲學范疇,并明確地提出人的異化,用以指主體與客體的分裂對立。在異化中,“人喪失能動性,人的個性不能全面發展,只能片面甚至畸形發展,人的生產及其產品反過來統治人” [3]47。馬克思(Karl Marx,1818-1883)繼而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闡述了“異化勞動”,指出其根源為私有制。艾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年)則從哲學和精神分析角度揭示了現代人的深層心理機制和性格解構的異化性質。除此之外,異化也一直是文學領域的重要課題。從古希臘神話和悲劇中人與異己力量的對立,從《圣經》中亞當夏娃的偷吃禁果、墮入凡塵,到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文學對宗教壓迫的反抗,到資本主義時期對人為物所操控的反思,異化的文學命題一以貫之且不斷呈現新的形態[4]。《巨型收音機》中收音機是科技的代表,它本是人的創造物,但它在一定條件下成為獨立于人的異己力量,反過來壓制、奴役、控制了人,使人的意識和活動從屬于它。于是技術發展成為人的異己力量,反過來給人帶來危害,這便是技術異化。技術異化的核心在于技術本來由人類主體產生,其最終目的是保障人類的主體地位,促進人類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但最后卻妨礙人類的主體地位,并阻礙人類的存在和發展。技術異化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技術對物質文明的破壞,主要表現為環境污染、生態失衡、能源危機,等等,造成人類物質生產條件和生活環境的惡化,生活質量明顯下降,嚴重阻礙物質文明的進一步發展;二是對精神文明產生危害,主要表現為某些消極道德傾向或者道德淪喪。《巨型收音機》中的技術異化則屬于第二種情況。
吉姆和艾琳本來過著殷實、舒適、優雅的中產階級生活:艾琳性情怡人,吉姆自我感覺良好。他們結婚九年,有兩個可愛的孩子,經濟收入和社會地位等均已達到大學校友統計數據中的平均水平。他們與朋友和鄰居們唯一的不同點就是他們都偏愛嚴肅音樂,參加過很多音樂會,并且經常花大量時間收聽音樂。家里的老收音機總出毛病,已經修不好了,于是吉姆預定了一臺新的收音機,希望給艾琳一個驚喜。然而,當艾琳發現新收音機的竊聽功能后,并沉迷于此,無法自拔。她無意中成了他人隱私的偷窺者,聽到了有關貧窮、疾病、失業、男女私通、家庭暴力等陰暗、骯臟的事。當她在電梯里碰到幾個衣著華麗的女人時,她盯著那一張張漂亮的臉龐看過去,努力想把她們與自己所收聽到的家庭一一對應起來,她想知道:她們中有誰曾經去過冰島?誰家正在為銀行透支而爭吵?誰的丈夫即將失業……她開始懷疑朋友和鄰居們的誠實與正直。與別人交往時,她一心琢磨著他們會有什么秘密。她明知這種行為不那么光明磊落,與趴在人家窗口偷看沒什么兩樣,卻無法抵抗誘惑。她既痛苦,又幸災樂禍,同時對自己的生活感到焦慮和缺乏信心。她反復向吉姆確認他們自己的生活與這些人是不同的,他們是幸福而體面的。這些略帶神經質的舉動引起了吉姆的反感。他毫不留情地數落艾琳的過錯。收音機沒能使兩人共同的高雅情趣得到發展,沒能增進彼此間的感情,反而暴露出他們生活中曾隱藏得很好的秘密,引起激烈爭吵,導致兩人感情破滅。
科學和技術本是中性的,并無善惡之分。當技術被當做一種改變世界的力量看的時候,它既可能為善, 又可能為惡;既可能促進人類的存在和發展, 又可能阻礙人類的存在和發展。因此,技術的異化在于人對技術的使用是否得當。不管這臺“惹是生非”的收音機有如何強大的魔力,它自始至終都只是客觀存在,而不是主觀卷入。問題的真正根源在于中產階級溫文爾雅的面紗之下藏匿的精神空虛。而揭去這層面紗的,并不是神奇的收音機,恰恰是艾琳自己。表面上看,艾琳似乎并沒有意識到自己生活中的不光彩之處。實際上,她正試圖用他人生活中的不幸、陰暗隱藏自己生活的缺憾并為自己不光彩的過去辯護,從窺視他人生活的骯臟中獲得一種道德上的優越感。某個傍晚,在出去赴宴途中,她向一個救世軍樂隊捐贈一張鈔票后臉上流露出一種為吉姆所不熟悉的洋洋自得的憂郁表情,并情不自禁地吟誦起莎士比亞《威尼斯商人》中的臺詞:“蠟燭雖小,卻照射四周;在這喧鬧的世界,好事亦如此。”她一方面被白天所聽到的陰暗生活困擾,另一方面為自己的善舉而沾沾自喜。她感到自己比別人高尚,頗有“世人皆濁我獨清”之感。這正是她內心虛弱而又企圖掩飾以獲取平衡的真實寫照。
除了給主人公帶來消極道德影響,技術異化還影響了主人公與他人的關系,造成了人際關系惡化。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哈貝馬斯提出“交往異化論”,認為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技術統治論”意識對人的壓抑已經到無以復加的程度,技術對日常生活領域的侵蝕,破壞了人與人之間的正常交往[5]。每當丈夫和孩子離開后,艾琳便迫不及待地把自己關在房間里,貪婪地收聽別人的家事,無法自拔。朋友聚會時,她粗魯地打斷別人,并緊盯著人看。如果孩子們這樣做,那么她肯定會懲罰他們的,此時的艾琳和之前快樂單純、體面優雅的艾琳完全判若兩人。她的種種失禮行為和無端的憂郁使自己的生活日漸脫離正軌。收音機也成為吉姆和艾琳夫妻關系惡化的導火索。一向溫情體貼的吉姆再也忍受不了艾琳的矯情與神經質,他歷數艾琳私吞母親遺產置親妹妹于不顧、甚至隨意墮胎等過錯,并道出他們經濟拮據的實情和對未來毫無把握的憂慮,這使艾琳精神徹底崩潰。
小說結尾,巨型收音機恢復了正常,用文雅而無動于衷的語氣播報著新聞:“東京清晨發生火車事故,死亡二十九人。布法羅附近收容盲童的天主教醫院發生火災,已為修女撲滅。現在的氣溫是華氏47度。濕度為89度。”[6]35收音機已然恢復了正常,然而吉姆和艾琳夫婦卻再也回不到原來的和諧與幸福了。而且,這兩則災難新聞是否預示著在技術異化進程中迷失了方向的現代人,已經無家可歸?愛聽收音機的艾琳和吉姆絲毫不懂收音機的構造,對他們周圍的其他設備也一竅不通,這是否在警告人們對科技的盲目追崇終將引人入歧途?
三
契弗短篇小說創作高峰開始于二戰后,《巨型收音機》出版于1953年。當時,美國社會正發生著深刻變化。表面上看戰爭已結束,經濟恢復發展,科技進步,人們可以好好享受這勝利果實了。可實際上戰爭的創傷深深地影響人們的婚姻、家庭及道德標準,造成了價值觀的極度混亂,整個國家陷入劍拔弩張、驚恐失措的氛圍中。人們緊張、沮喪、憂慮、消沉、失望、墮落,對社會生活充滿幻滅感。同時隨著戰后消費熱潮的興起、郊區的繁榮和日益膨脹的購物欲望,人們更加茫然而不知所措。這些問題在稍后的60年代終得以大爆發。契弗本人出身清教家庭。他反對科學技術,認為科學只會發明摧毀城市的武器,卻絲毫不能懂得人類的喜怒哀樂。他還反對一切現代文明,認為人們迷戀物質生活,終有一日,機器毀滅,靠其生存的人類也將隨之滅亡[7]。他通過神奇的巨型收音機無情地揭露了中產階級體面生活中的邪惡不堪、道德淪喪,表達了對處于豐裕社會技術異化進程中人們生存困境的深深隱憂,值得當代人們深思。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4.
[2]陸梅林,程代熙.異化問題(下冊) [C].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6:328.
[3]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下卷)[M].賀麟,王玖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0:47.
[4]蔣承勇.自由異化文學——論異化主題在西方文學中的歷史嬗變[J].外國文學研究,1994(2):36-42.
[5] Feenberg, Andrew. Alternative Modernity: The Technical turn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The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79-86.
[6]約翰·契弗.綠陰山強盜——約翰·契弗短篇小說集[M].張柏然編.南京:譯林出版社, 2001: 35.
[7]上海外國語學院英語系.美國短篇小說選讀(下)[C].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2:236.
基金項目:本文系2014年浙江省大學生科技創新活動計劃暨新苗人才計劃項目(2014R412024)和2013年浙江農林大學創新創業訓練計劃項目(201310002)的階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