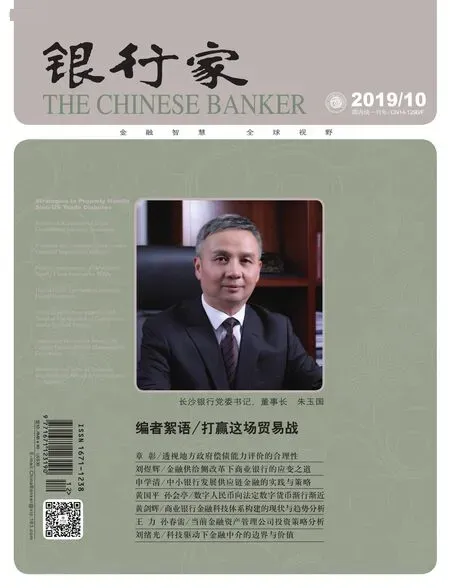依賴信用評級的監管成因及其風險分析
董裕平+范彥君
眾所周知,標準普爾、穆迪等三家美式評級機構在當今國際評級市場上占有絕對壟斷地位。這種市場格局的形成在相當程度上與監管部門對信用評級的依賴密不可分。從市場經濟發展與制度演化的歷史看,一方面,信用評級機制作為市場制度的內在部分,有其經濟合理性。因為這種制度安排符合效率趨向,可視為市場制度內生的一項結果。另一方面,由于美國監管部門對評級的利用,不僅促進了這一特殊的金融市場“守門人”角色的迅速發展,還為其輸入了強大的市場影響價值。Partnoy(2001)指出,1970年后評級行業的繁榮并不是因為評級機構發布的信息本身更有價值,而是監管對評級的認可。隨著監管對評級的依賴增加,評級行業的業務量激增,而且監管依賴也使得市場認為信用評級越來越有價值。
美國監管部門依賴信用評級的歷史簡況
我們整理總結了1936年至2000年期間美國有關使用信用評級的監管法案與規定(表1),可以窺見美國的監管對評級的使用非常廣泛,其結果不僅導致了市場對評級的依賴不斷加深,更是促進和塑造了美國評級的獨特地位。在2005年6月美國國會聽證會的報道中,至少有8項聯邦法律,47項聯邦條例以及100項州法令與評級相關。
監管依賴信用評級的原因
監管部門為什么如此依賴信用評級呢?從一些國家監管部門使用和依賴評級的基本情況看,主要的原因與目的可以歸結為:(1)審慎監管,例如,對于銀行和證券公司規定最低資本充足率要求;(2)投資者保護,如對養老金投資設置了最低評級要求等。下面對此做進一步分析。
審慎監管
審慎監管一般旨在維持市場信心以確保金融機構的穩定。美國早期審慎監管始于1931年到1936年,實施資本監管和緩減公司不能履行對于消費者和交易對手方債務能力的情況。其中最重要的是對金融機構設置最低資本要求。1975年,美國證監會(SEC)第一次使用評級規定了證券交易商的凈資本要求。SEC規定,當交易商在計算凈資本時,要從凈資本中扣除所有權證券的市場價值部分。歐洲金融監管部門對于評級的使用,主要是決定銀行用以支持收益性資產的資本要求。例如,英國金融服務局(FSA)規定,如果債務發行人被三大評級機構中至少一家評為投資級別,就可以降低對于風險權重的要求。
真正導致信用評級受到世界范圍的監管依賴則是1999年《巴塞爾協議》的修訂。1997年亞洲發生金融危機后,為確保銀行部門對于信用風險貸款定價及資本使用的合理性,巴塞爾委員會擴大了風險資產中信用風險權重。1999年公布了“新資本充足率框架”,新協議對風險資產的信用風險采取兩類估計方法:標準化法采取外部評級機構的信用評級;內部信用評級作為可替代方法,審慎監管允許銀行使用其內部信用評級和損失違約率估計風險資產。這項提議后來促成了2004年巴塞爾II 的修訂,它加強了序數評級和違約概率之間的聯系,將評級與銀行所需的權益資本和融資的信用成本更密切地聯系在一起。根據巴塞爾II,外部信用評估決定信用風險權重可以在銀行和投資公司中使用。在1999年修訂的資本協議中,巴塞爾委員會使用標準普爾體系的評級作為參考來重新劃分不同借款人,即采用評級符號來劃分貸款信用等級,使監管更加簡便具體化,但也存在漏洞,為此巴塞爾委員會一直試圖尋找可替代方法,例如,采取基于資產組合的方法測量信用風險,然而該方法也有明顯局限。
投資者保護
金融監管的基本目的之一在于保護投資者,特定的監管則是對投資者提供更直接的保護。部分集體性投資機制的監管規定可以控制和影響大量投資者的利益。例如,按照美國1940年《投資公司法案》中的第2a-7條的規定,貨幣市場基金只能投資高質量的短期金融工具,即只允許投資于由NRSROs(Nationally Recognized Statistical Rating Organizations)評級的兩類高級別短期債券,并且對沒有得到最高評級債券的持有量予以限制。1989年才允許養老金投資于資產支持證券(ABS),且只能投資于投資級別的證券。同年,《金融機構復興和改革法案》禁止儲蓄和貸款機構投資于投資級別以下的債券。類似的,加拿大海運法案(Canada Marine Act)規定,港口管理局只能投資至少有兩家評級機構評級的債券,其中一個必須是穆迪或是標準普爾,并且是投資級別的證券。1991年開始,法國貨幣市場基金投資組合受到信用評級的限制。例如,貨幣市場基金所持有的不具備投資級別的資產不得超過25%。
基于上述保護投資者利益和審慎監管的要求,監管部門還在監管實踐中廣泛地采用了評級工具作為衡量市場準入的標準,以較好地保證市場的投資品質。例如,美國對于“抵押證券”的定義,要求該類債券是至少有一家NRSROs評為最高投資級別。加拿大證券法也規定了使用評級作為市場準入,對已經擔保和已取得高評級的短期債務可以享受豁免,即不需要在監管部門注冊。在歐盟層面,對于信用評級廣泛使用的監管法案是2006年的資本要求指令。歐盟委員會也勉強接受使用評級作為監管標準,認為“在沒有其他方案進行例證分析的情況下,歐洲立法使用評級不應該被簡單的作為廣泛推廣使用的方式。在立法使用評級時,都應該比較所有可選方案。”
監管部門選擇運用評級工具來處理機構與產品的風險管理問題,包括直接用來篩選獲準進入市場的參與機構與產品,有利于市場的穩健運行,從而有效實現金融體系配置資源的基本功能。盡管監管部門允許機構運用內部信用評級進行風險管理,但是,不同機構內部評級指標體系和貸款對象不同,評級模型也不相同,這比外部評級工具要復雜得多,大大增加了監管的操作成本和難度。相反,外部評級恰恰提供了一個相對簡單的參照,不僅便于機構對其內部評級進行誤差修正和對比,同時,也為監管部門提供了更為簡易的監管指標和評價標準。于是,在監管逐步確立評級要求的制度框架下,雖然評級行業的業務量出現了激增的現象,市場也逐漸認可其價值,但潛在的問題也逐漸暴露出來。
監管過度依賴評級機構蘊藏巨大風險
監管依賴導致了評級機構成為愈加重要的市場“守門人”角色,評級機構在市場上不僅更加積極主動地擴展評級業務,而且深度參與結構性產品的開發設計,演變成了市場的“開門人”。近些年來,評級機構在短時間內幫助創造出了數萬億美元的結構性產品市場規模,雖然促進和拓展了金融衍生品市場,但最終爆發了金融危機,因此招致一片撻伐之聲。
市場對于信用評級機構的質疑和批判,多數源于評級機構在危機之前幾乎沒有給出任何預警,而在危機發生時則對一些之前給出高評級的機構或產品采取突然降級,加劇了市場恐慌。其在危機發生前后的迥異表現,一則促進了市場繁榮泡沫,另一則推波助瀾惡化了危機。客觀地看,發行人、投資者、評級機構和監管部門的不當激勵對這場金融危機都負有一定責任。就評級機構來看,不僅僅是其能否在事前給出預警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其在市場結構中處在相對特殊的地位。一般而言,評級機構負責信息的開發與生產。但對于結構性衍生產品,評級機構已經不再是作為第三方幫助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它們自身開始參與到具體的金融產品開發、設計和發行過程,成了影子銀行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此時的評級對象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即評級機構實際上是在為自己參與設計開發的產品進行評級,不僅是評級本身的準確性可能存在問題,而且其中的利益沖突比單純的付費模式問題可能要嚴重得多。
在影子銀行體系的金融創新活動中,評級作為市場定價的重要因素,對多層級復雜衍生產品的創造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說,缺少評級機構的介入,復雜的金融衍生品市場將很難成為現實。我們看到,評級機構進入信用衍生產品市場通常是利用信用衍生工具的次級形式,即債務抵押債券(CDOs)。通過建立特殊目標實體(SPE),用來購買固定收益資產組合,如果某些資產違約,初級的SPE就要承擔第一步損失,每一批付款都有一個規定的優先支付。評級機構的重要作用首先是利用模型將各個級別CDOs聯系在一起使其價值遠超過基礎資產。其次,評級機構通過重新打包評級資產池中的各類資產,將原有低級別資產通過重新組合進入高級別資產系列。而重新打包并結構化資產池中現有資產需要十分精密的模型設計,否則難以覆蓋風險傳導信息,存在評級失誤及由此導致的風險問題。
以標普為例,它使用蒙特卡洛模擬資產組合違約的分布和時間,并據此判斷模擬中的損失觸發是否具有破壞性。評級機構根據設定的違約率、回收率和資產相關系數變量,給予每一檔次一個級別。其中,回收率和回收時間的改變是依靠資產性質決定,可以人為設定,并不是一項精密的科學。而對于特定資產又幾乎沒有歷史的違約率。但是,模型需要假定評級機構輸入的回收率必須是精確的。這就為衍生產品最終評級的精確性埋下了隱患。從標普公布的一些在特定CDO評級中使用的違約率(表2)來看,其所使用的違約率估計相對固定,只是基于給定某級別的違約概率估計。這種相對固定的違約概率假設使得評級有失準確性。
評級失誤在很難被市場糾正并不斷積累的情況下,將會導致系統性災難。一者,評級信號實質上是給出了資產風險定價,評級有錯誤,即意味著市場定價錯誤,如果市場有效,這種套利機會就能夠被市場挖掘出來,從而修復或糾正這種錯誤。然而,在評級壟斷的市場格局中,客觀上很難有其他相對獨立的市場力量能挖掘這種套利機會。二者,一些投資者考慮到監管要求,持有某些經過評級并達到投資等級標準的資產,如果評級存在沒有被市場糾正的嚴重錯誤,那么這些機構的風險管理模型就很容易被擊穿。在這次金融危機中,這類問題相當普遍,加劇了系統性風險沖擊。
(作者單位:中國社科院投融資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工商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