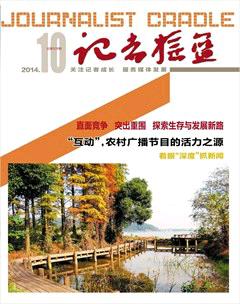尊重他人就是尊重自己
徐耀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自媒體誕生以來,媒體有沒有操守,一直是受眾評價一家媒體是否值得信賴,是否有公信力,是否值得尊重的重要標準。而有的媒體恰恰忽略了“操守”這個最重要,也是媒體賴以生存的最起碼的道德底線。一樁樁、一件件鬧得沸沸揚揚的“艷照門”事件,就是對媒體操守和媒體道德底線的一次次考問。
主流新聞媒體的國家所有制性質,以及黨的喉舌作用,決定了它的壟斷性質,也就是傳播途徑的唯一性。盡管有些媒體在這種情形下,以合資和股份制的形式,試圖擠占出一席之地而與其分庭抗禮,但是,在根本結構性的架構中,仍只能是附屬地位。恰恰是這種壟斷性和新媒體的沖擊,也使得傳統媒體在不知不覺中走向逐利的道路。市場經濟的導火索一旦點燃了新聞領地的這個火藥庫,在煙花綻放的同時,也帶來了巨大的破壞性。
于是,有償新聞出現了;廣告時段拍賣了;以負面新聞為要挾、以有價新聞換取交易的事情發生了;虛假新聞和廣告占據了主流媒體的頻道和時段;更有甚者,不惜制造假新聞,做有選擇性、有傾向性的報道……
當人們發現新聞媒體可以成為盈利的簡單方式的時候,中國大地如雨后春筍般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報刊、雜志社和類似機構,也隨之出現了大量“記者”,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如狼似虎般撲向各類企業,后來又撲向政府,特別是縣區鄉鎮一級的政府。由于這些大量涌現的、真假難辨的記者的四處出擊,以及所獲取的利益,引發了新聞出版界幾番內部清洗,但至今收效甚微。
也正因如此,我們在主流媒體上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一些畫面和很有意思的橋段:一方面,新聞節目里剛剛義正詞嚴地揭露和批判著某種產品的假冒偽劣;另一方面,卻在夜半的商業時段大肆播報這家企業的產品廣告。比如對修正藥業的宣傳,比如對所謂偽科學養生的揭露……無形中形成一種滑稽的態勢:七點鐘批判,十二點任其繼續一臉濟世救人信口雌黃!
這種極具諷刺意味的片段,不是個別現象,而是各家媒體司空見慣的事情。受眾似乎也習慣了、皮實了,你媒體說好說壞都不那么相信了,或者說,已經完全不相信了。這就是為什么一方面新聞媒體產業極度擴張,而另一方面社會認知度和公信力卻極度下降的重要原因。這是很悖常理的,也是很奇怪的一種經濟現象。理論上應當是:越誠信越有公信力的行業,越能取得豐厚而持久的利潤。而目前新聞傳媒的部分從業人員中,似乎是越無邊界、越無底線、越能獲得超常的發展。這難道不是一個怪現象嗎?可這就是我們的現實——很無奈的現實。這種現象理論上是難以持久的,這是包括媒體人在內的所有人都認可的事實。于是我們的媒體飽受詬病,然而它卻仍在洶涌的詬病中闊步前行,似乎還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
當然,由于社會的廣泛不滿意,掌舵的高層們對此也是心知肚明。于是,思變之心陡然而起,“走轉改”應勢而生。不可否認,這種形式的本身和初衷有著積極的意義,起碼讓一部分、哪怕是一小部分記者走到人民群眾中間都是可喜的,但是,卻也很可悲。腳步在走,方向卻未必明確;方向正確,視線和視角卻不免狹窄。淺薄和對深層次的缺乏探討,使這項活動在某些地方越來越像是一種概念、一場走秀。而這場秀,更像是對逐利的掩蓋和粉飾。
于是,我們又看到了一種奇怪的現象:一方面媒體瘋狂地逐利,不斷地創造利潤的奇跡;另一方面,又在努力倡導正能量,試圖把自己演變成正義的化身,打扮成救世主的模樣,而就是不能成為一個客觀事實的表述者。這種詭異的場景比單純的逐利更具破壞性。所以,我們經常會看到這樣的畫面:一邊是一些從業者打著媒體的旗號毫無底線地采訪;一邊又打造著所謂的平民神話,卻忽略對新聞陣地的堅守。
女明星王菲的離婚事件,就是個很好的例子。按說王菲離婚只能算是一件事兒,但瞬間卻占據了各大網絡媒體的頭條,鋪天蓋地、連篇累牘。但真正上升為事件,還是由于某家網絡媒體的記者,為獲取獨家報道,在高速公路上兩度駕車逼停王菲的座駕,直至拍到滿意的照片后才駕車離去。作為當事者的王菲,它不僅僅是個明星,同樣也是個剛剛離婚的女人,她需要平靜,也更需要關懷,而體現人文關懷,恰恰應該是媒體社會責任的重要表現。而媒體人為了率先掌握第一手資料爭分奪秒,雖精神可嘉,卻置職業操守于不顧。更何況社會責任論中,一個概述的要點,就是媒介必須在現存法律和制度的范圍內進行自我約束。而這位記者的行為,已經涉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盡管事后記者及記者所在媒體發聲道歉,王菲也未追究,但是記者采訪的無底線已經暴露無遺。
其實,不僅僅是我們,國際通行的職業準則,同樣容不得肆無忌憚的胡作非為。
2011年7月,默多克新聞集團旗下的《世界新聞報》因竊聽一個被綁架女孩及其家人的電話被曝光后,引發了社會公憤,不得不于2011年7月10日停刊道歉。至此,《世界新聞報》,這家有著168年歷史的老牌星期天報紙,在出版了它的最后一期后關閉。這對全世界的媒體從業人員都是一個警示。
中國有句古話,叫“君子不欺暗室”,意思是君子不因為在暗室之中(即沒人看到)就做丟人的事。但事實上,人性是復雜的,即便是君子,也總有一點見不得人的秘密。靠專門挖掘別人“暗室”中的東西,以滿足一些受眾的窺人隱私欲望,這種“誘導式”報道,令人不齒。如果在這樣的指導思想下,一代又一代的新聞人把偷拍、竊聽、導演新聞的做法放大到了極致,終有一天會引發眾怒。最終將失去媒體的操守,失去受眾的信任和尊重。《世界新聞報》這家百年老報也正是因此招來了的滅頂之災。
未來的中國將更加開放,將與國際慣例更加緊密聯系。這就要求我們更加熟悉全球通用的新聞準則,而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新聞理想和職業底線的有機結合。當新聞媒體一旦有了懲惡揚善、傳播正能量的使命,就不可以再去以追逐利益為目標,更不可用非法、非正義、非道德的手段,再去鼓吹所謂的正義。
(作者單位:沈陽廣播電視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