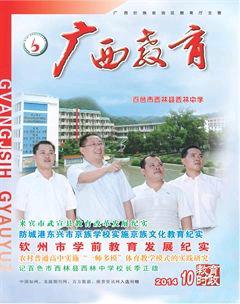詩人已騎黃鶴去
鐘云
近日,第六屆魯迅文學獎獲獎名單公布,詩人周嘯天以其古體詩集《將進茶——周嘯天詩詞選》獲得本屆文學獎詩歌獎,由此引發了一系列爭議。公眾對其詩歌的評論趨于兩極化:有的評論直指周嘯天的詩詞水平太過一般,認為其作品像“新聞詩”“打油詩”;作家王蒙、楊牧等卻力捧周詩,贊其詩“古色古香、新奇時尚”“亦屬絕唱,已屬絕倫”。連日來,圍繞周嘯天的獲獎,以及有關魯迅文學獎的種種,各大媒體展開了鋪天蓋地的爭論。
“詩”是什么樣的詩?
提到文學,當然不能不談詩歌。本屆魯迅文學獎詩歌獎的獲獎作品是一本舊體詩集。魯迅文學獎自設立以來(今年是第六屆),過去幾屆的詩歌獎獲作品幾乎都是新詩,這回評選了一本純粹的舊體詩集,似可窺見評委們推崇傳統的意圖。應該說,這番初衷是好的,從某種意義上說,回歸傳統沒有錯。
今年的詩歌獲獎作品之所以引發爭議,是因為其中的一些詩似乎很難讓讀者與文學大獎掛上鉤。試舉一二例:“寫鄧稼先:炎黃子孫奔八億,不蒸饅頭爭口氣。羅布泊中放炮仗,要陪美蘇玩博戲。”“寫印尼海嘯:由來劇變不可測,朝或多金暮洗白;饑寒起盜令齒冷,一方有難八方惜;港臺慷慨盡解囊,大陸富豪莫羞澀!”
有評論指出,這些詩歌遣詞造句都十分淺顯直白,除了時代特征比較明顯外,并沒有太多的深意,與“打油詩”沒有什么兩樣。許多網友質疑評委們的眼光,既而質疑評獎的“內幕”,還驚呼“上下五千年都排不上這個打油的周詩人啊”!
筆者不是詩歌鑒賞專家,因此不敢對其作出過多評價,單就這兩首來看,也覺得似乎不怎么樣。不過,僅憑一兩首詩就去評價一個作者的創作水準,還是有失公允的。近期媒體對周嘯天輪番“轟炸”,所引用的幾乎就是他的這一兩首淺顯的“打油詩”,似有“斷章取義”之嫌。這不是理性、公允的批評方式。
一些較為全面讀過周嘯天古體詩的作家、評論家給出的卻是另一番評價。
河南省作協副主席、河南省詩歌協會會長、第三屆魯迅文學獎詩歌獎獲得者馬新朝認為周嘯天“既有好詩,也有糟糕的詩”。馬新朝說:“王蒙說他的詩歌已經寫到了極致,這個我是不贊成的。雖然他的詩跟唐宋時候的沒法比,但是在當下舊體詩歌作者中,還是比較優秀的。”
談到周嘯天詩歌的創作形式,第六屆魯迅文學獎詩歌獎評獎委員會主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詩人高洪波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給出了這樣的答復:“在我看來,周嘯天的詩歌有對生活、對時事的感想,舊瓶裝新酒裝得不錯……我認為他的詩健康明快,對于當代很多時事生活的反映很迅捷,甚至超過了我們新詩的反映程度。”
就文學創作而言,任何創作者寫出的東西都不可能全是名文佳句,而文學評論與鑒賞也可以各有各的觀點,正如詩人高治軍指出的那樣:“一個詩人也好,一個作品也好,別人對你的評價肯定有好有壞,這很正常。”
翻閱周嘯天別的一些古體詩,要說這個詩人毫無水準,筆者不敢茍同,試看他《將進茶》中的幾句:“遙想坡仙漫思茶,渴來得句趣味佳。妙公垂手明似玉,宣得茶道人如花。”讀起來十分清新明快。其中的好與孬,讀者朋友們自己判斷吧。
對于外界的質疑,周嘯天十分鎮定,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唐人就“打油”,并用王梵志的“打油詩”形容自己,“梵志翻穿襪子,觀者雖不爽,自己的腳卻是十分舒服的”。他坦言自己獲獎后沒有受爭議的影響。
周詩人倘若真能如此,那最好不過了。
爭議的根源在于文學獎本身
與其說人們對周嘯天的詩歌提出異議,不如說人們對包括魯迅文學獎在內的各類文學獎的評選產生了質疑。看看網上的評論就知道了,似乎沒有哪個評論是單純針對文學與創作的,幾乎都要“扯”到文學獎的評選上來。
從上一屆魯迅文學獎詩歌獎獲得者車延高的“羊羔體”,到現在周嘯天的“嘯天體”,這種給文學創作戴上戲謔“名號”的做法,實際上反映了人們對過于僵化的文學獎評選體制的嘲諷。不得不說,如今國內文學獎的評選,難以達到完全公開透明化的狀態,評選本身的公平性難以保證。從某些“傳聞”中,人們似乎能從一個側面窺見評獎過程中的某些內幕。因為評獎程序、規則等方面存在諸多缺陷,讓某些逐利之夫鉆了規則漏洞也不是不可能。
那么,做出相對公平公正的評選,評委機構難道一點辦法都沒有?未必,關鍵是看他們是否有改進的誠意,例如增加讀者評選環節,把市場因素也作為其中一條參考標準等,都是較好的改進方式。遺憾的是,評委機構似乎不大愿意改進,依舊堅持原有的規則。就說魯迅文學獎,使用的基本還是“各地作協或符合條件的出版機構推薦→總體評選得出入圍名單→再次評選確立最終獲獎者”的程序,期間或許會增加評選環節,但基本的程序一直未變。據說今年有所改進,有了實名計票,但仍未能減輕公眾對評選公正性的質疑。
而有關評選標準的問題,同樣也引發了公眾的質疑與爭議。對文學作品做出評價,原本就沒有統一、“萬能”的公式,所謂“一千個讀者眼中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少數幾個評委評選出的作品,未必就是最好的作品,哪怕評委們水平再高,也終究會有局限性,也只能代表他們個人的意見。但問題恰恰就在這里——評委們都稱自己按標準公正評選了,普通讀者們卻又有不同意見。由此看來,任何一個獎項的設立都注定存在爭議。
質疑歸質疑,既然設立了獎項,就得有評選,有評選就會有投票,有投票就會有“入局”“出局”,結果總是“幾家歡樂幾家愁”。不管是世界性的諾貝爾文學獎,還是國內的包括魯迅文學獎在內的各類文學獎項,要說做到絕對公平是不可能的。即使大如“諾獎”,也一樣存在缺陷。但是,有缺陷并不等同于可以喪失原則。就文學獎而言,這個“原則”就是堅守文學的底線,堅守文學的純潔性、思想性。倘若連這一基本的底線也未能守住,那么這些形形色色的文學獎,不設立也罷。
跳出評獎看文學
設置文學獎的本意在于繁榮文學、激勵創作,可惜這樣的設獎初衷已經被異化。過分關注獎項與名譽的背后,實際上已經對文學本身造成了傷害。創作不是為了獲獎,這原本是一個樸素的真理,可惜如今已經變了味。
試問,歷史上有哪位偉大的文學家獲過什么大獎?李白、杜甫獲過什么詩歌獎?雨果、托爾斯泰得過什么小說獎?魯迅呢?矛盾、老舍?有人開玩笑說,冠以他們的名義設置的獎項,或許連他們自身的作品都未必能夠獲獎,這真是絕妙的諷刺。
許多文學大家,實際上對文學獎本身保持足夠的警惕。被譽為“文化昆侖”的錢鍾書先生就曾多次對諾貝爾文學獎提出異議。當時法國人在巴黎的《世界報》上力捧錢鍾書,說中國有資格榮膺諾貝爾文學獎殊榮的,“非錢鍾書莫屬,只有錢鍾書當之無愧”。錢鍾書對這樣的褒揚并不買賬,他在《光明日報》上發表筆談式文章,歷數“諾獎委”的誤評、錯評與漏評,條條款款,有根有據。最讓人忍俊又令人反思的是,他引用了英國著名作家蕭伯納的一句話來諷刺諾貝爾文學獎:“諾貝爾設立獎金比他發明炸藥對人類的危害更大。”而法國著名文學家、哲學家薩特更是旗幟鮮明地拒絕諾貝爾文學獎,他公開發表聲明,表示拒絕一切來自官方的榮譽,骨子里體現的是對文學純潔性的追求和思想獨立性的堅守。
遺憾的是,我們如今缺乏這樣的文學大家,更缺乏文學大家堅守思想獨立、人格獨立的骨氣。放眼當今文壇,各種傳聞、丑聞不斷,“跑獎”“賄獎”時見報端。爭論“獲獎”大于文學本身,爭論文壇是非蓋過文學創作,真是令人悲哀而又叫人憂心。任由這樣的狀況蔓延,必將導致文學界越來越浮躁,最終傷害的就是作為“人類情感與智慧結晶”的文學,也不可能產生轟動時代的鴻篇巨制,永遠只能在小打小鬧中游戲下去,迷失下去。
有人把這樣的局面歸咎于媒體的炒作。平心而論,媒體確實“有基于新聞運作而進行跟風的必要”,但如果不是文學界自身的躁動,何至于引發如此多的波瀾與口水?還有人說“這個時代就是這樣,普通圍觀者會對意外的情況發表議論,對文學本身并不感興趣”。是的,假如文壇的各種“傳聞”“丑聞”的關注價值已經大于文學本身,那么人們為何不選擇關注前者呢?
文壇需要反思,作家們更需要反思。何日能夠讓文學真正回歸本質?沒有人能夠給出明確的答案。這需要時間。不如慢慢培養一種心態吧,正如今年的“魯獎”落選作家梁衡在《關于魯獎落馬的告白》中提議的那樣:“希望讀者、評論家多關注一下作品的內容,去作一點研究,為了文學。畢竟魯迅還是思想家,這獎還頂著他的名呢。”
詩人已騎黃鶴去——或許今天注定是一個沒有詩人的時代,文壇看似熱鬧,文學早已落寞。文學不受待見、已近異化的邊沿,這是不爭的事實,也是看待魯迅文學獎及其他各種文學獎項最應該反思的地方。
(責編 歐金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