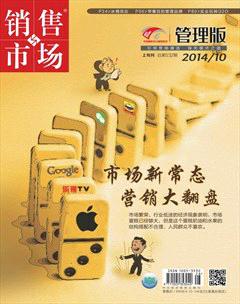新常態,新營銷
劉春雄

營銷面臨的通常不是單向問題,而是矛盾問題。營銷就是在矛盾中求解。正因為現實的答案難以同時滿足矛盾的雙方,所以正確的選擇很容易招致理直氣壯的批評,比如,過去把弱小的中國企業帶向成功的中國式營銷,就是在批評的氛圍中逐步得到承認的。
我們把中國企業目前的困局歸結為市場繁榮與行業低迷之間的矛盾,這是現象層面的觀察結論,也更深刻地提示了中國營銷面臨的根本性問題,即中國營銷的結構性問題。
相對應的,我們也可以把以前中國式營銷的生存環境歸結為消費能力不足與消費饑渴之間的矛盾。在中國市場整體消費能力不足的情況下,中國企業卻享受行業井噴,正是這種矛盾孕育了與之相適應的中國式營銷。或者說,中國式營銷是建立在強烈的消費意愿和低迷的消費能力的環境之下的產物,其基本表現就是在“雙低”(價格到底線,品質到底線)格局之下的行業井噴。
市場繁榮和行業低迷的矛盾,我們也可以解讀為強大的消費能力和低迷的消費意愿的矛盾。這是以前營銷矛盾的反轉。這是目前中國營銷所面臨的最大挑戰。
很多人認為,科特勒的最大貢獻是提出了4P理論,其實,科特勒《營銷管理》最大的貢獻是營銷環境分析,4P組合是根據環境變化而重新組合的。按照營銷環境分析的概念,不同環境下的營銷是沒有可比性的,所以,根本不存在跨國公司營銷與中國企業營銷孰好孰壞的問題,因為它們是建立在不同的營銷環境之下的。
同時,在中國壓縮式營銷進程中,中國營銷環境的變化是巨大的。我們的基本判斷是:傳統中國式營銷賴以生存的環境在快速變化。營銷的主體矛盾已經反轉,從消費能力不足與消費饑渴的矛盾,轉化為市場繁榮與行業低迷的矛盾。
這意味著,中國式營銷也該改朝換代了。
中國式營銷的背景
改革開放后,營銷所面對的中國市場的總體環境是:
第一,消費者的消費能力嚴重不足,消費水平嚴重偏低。主流消費者不可能接受發達國家的主流產品。
第二,國門突然打開,消費者突然感受到西方國家數百年積累的產品體系,有強烈的消費意愿。
第三,渠道體系嚴重碎片化,缺乏現代的商業體系,很難建立大一統的營銷體系。
此時,中國出現了以跨國公司為代表的營銷體系,表現為:1.產品接近或低于西方主流,但遠離中國多數消費者的消費能力,只能成為中國大市場的小眾。當然,可口可樂、麥當勞等是少數的例外。2.以資金優勢和品牌優勢營造消費氛圍,成為低消費能力消費者的奢望——多數人可望而不可即。3.進入現代零售業,或建立專賣店,渠道體系上占領高端。
曾經,中國的知識階層總體上是跨國公司的擁躉,或者出于對中國企業實力不對等的擔憂,或者出于對跨國公司的羨慕。
然而,跨國公司也有兩難:如果不與中國企業拉開差距,消費者憑什么選擇它們;如果與中國企業拉開差距,注定無法成為主流。正是因為無法平衡矛盾,所以多數跨國公司進入中國之初的優勢隨著時間流逝而逐步消失。
可以說,中國企業是跨國公司養大的。因為跨國公司的價格體系與中國消費者的消費能力差距太大,因為當初現代零售業離中國普通消費者太遠,中國巨大的市場,跨國公司總體上成了小眾。但近距離觀察跨國公司的中國企業卻找到了標桿,分享了跨國公司放棄的剩余市場,并以不同于跨國公司的營銷方式,迅速成長起來。
中國式營銷,是對以前中國營銷總體特征的概念式描述,總體來說大致有下列幾條線索:
第一,打造“雙低”產品。從總體需求來說,“雙低”是符合以往的主流消費格局的。因為“雙低”產品的存在,迅速擴大了市場,形成了消費者的數量滿足。盡管部分專家否定“雙低”產品,但市場是歡迎的。正因為對“雙低”產品的需求,家電行業的中國二流企業打敗了日本一流企業。營銷以滿足消費者為目標,消費者的需求無所謂高端低端之分,因此,我們無須批評“雙低”的產品格局。
第二,眾多行業的波浪式推進和行業井噴。中國有巨量的消費者,多數家庭的購買力相對平均,而且一個階段的家庭購買力集中于消費某個產品,這就造成了各行業波浪式消費的浪潮,也造成了行業井噴的現象。
第三,營銷體系(通路)建設,盡可能接近消費者。除可口可樂、綠箭等少數跨國公司外,跨國公司總體上是現代零售業的終端型企業。而中國企業則不然,按照陳春花教授的觀點,中國市場是渠道驅動優于品牌驅動。由于中國市場渠道結構的碎片化,中國企業的營銷變化聚焦于渠道建設,比如市場重心下沉(從省代到市代,再到縣代)、深度分銷、終端攔截等,基本上屬于營銷體系建設。
營銷體系建設,目標是更接近消費者,從以前距消費者好幾個環節,到直面消費者。跨國公司基本沒做這個渠道體系建設,它們直接入駐現代商業。
第四,行業整合,誕生巨型企業。對于高集中度的行業,大企業把產品做到“雙低”,小企業就在生死存亡的邊緣。大企業每一次銷量增長,伴隨而來的都是行業盈虧平衡點的提高,以及對低于盈虧平衡點企業的淘汰。
正如有人所說,中國企業是競爭導向的企業,跨國公司是消費者導向的企業。類似的描述總體上是批評的語氣,我們卻認為是中國營銷的正常現象。正確的描述應該是:在低標準滿足消費者的條件下,以競爭導向的營銷為主調。
在行業整合完成之前,營銷一定是競爭導向的。這一點,發達國家企業在早期經歷過了。這個時期的競爭,以前臺競爭為主線條,以價格為主要競爭手段。
行業整合完成后,營銷就變成以后臺競爭為主線條,以產品為主要競爭手段。
新常態
正因為有著強烈的消費渴望,并且通過“雙低”的產品格局滿足消費者的消費能力不足,所以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是驚人的。連續30多年保持10%左右的發展速度,在全世界是絕無僅有的。中國企業一直享受著發展紅利。
然而,進入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中國的宏觀經濟發生了變化,這就是新常態。
中央定調目前7%—8%的增長為新常態,《人民日報》因此發表“新常態,平常心”的系列評論。這是非常重要的宏觀判斷。
實際上,宏觀層面的新常態與微觀層面的新常態一定是對應的,表現為增速下降態勢下的結構調整。
營銷是微觀經濟層面的東西,營銷最重要的生存法則是達爾文的“適者生存”。微觀層面的營銷有賴于對宏觀層面經濟狀態的適應能力,或者說首先是對宏觀經濟的判斷能力。在新常態下,宏觀經濟的目標是“穩增長,調結構”。如果說GDP每年平均7%—8%的增長是穩增長的話,那么宏觀經濟層面調結構的微觀層面表現是什么呢?如果沒有在營銷微觀層面的表現,那么宏觀層面的調結構如何實現呢?
什么是新常態?國家發改委副秘書長王一鳴說:“從速度層面看,經濟增速換擋回落,從過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長轉為7%—8%的中高速增長是新常態的最基本特征。”
《人民日報》評論認為:環顧世界,當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歷了一段時間的高速增長后,都會出現增速換擋現象:1950—1972年,日本GDP年均增速為9.7%,1973—1990年回落至4.26%,1991—2012年更是降至0.86%。1961—1996年,韓國GDP年均增速為8.02%,1997—2012年僅為4.07%。1952—1994年,我國臺灣地區GDP年均增速為8.62%,1995—2013年下調至4.15%。
“不少國家的經濟增速都是從8%以上的‘高速擋直接切換到4%左右的‘中速擋,而中國經濟有望在7%—8%的‘中高速擋運行一段時間。”國家信息中心首席經濟師范劍平分析,這是因為中國是一個發展很不平衡的大國,各個經濟單元能接續發力、綿延不絕,導致發展能量巨大而持久,“比如,當服務業在東部地區崛起時,退出的制造業不會消失,而是轉移到西部地區,推動西部經濟快速增長。”
所幸的是,中國經濟高度發展是不均衡的。其中,既有區域發展的不均衡,如東部與西部發展的不均衡,也有城市與農村發展的不均衡。正是由于經濟發展的不均衡,使得各行業的啟蒙和普及周期較長,給了中國企業調整結構以一定的緩沖期。正因為如此,在日本、韓國和臺灣的經濟發展從8%以上的“高速擋”直接切換到4%左右的“中速擋”,才會有中國將會在較長時間內在7%—8%的“中高速擋”運行的判斷。
這是中國這樣的大國所特有的戰略緩沖空間,也是中國企業的戰略緩沖空間。日本、韓國和臺灣就缺乏這樣的戰略緩沖空間,這也使得他們營銷調整所受到的沖擊更為強烈。
中國經濟的新常態,決定了中國營銷的新常態。不排除個別行業或個別企業仍然會在某個階段有調整增長現象,中國企業的“穩增長,調結構”也將成為新常態。(作者為本刊特約高級研究員,鄭州大學管理工程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