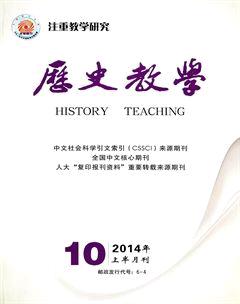中學歷史教學應有通貫的眼光
法國年鑒學派的一代宗師就“歷史有什么用?”這一問題為“歷史學辯護”。我在讀史、教學的過程中越來越感到歷史的“用”處,今天浮躁背景下,在急功近利者眼中,歷史是完全無用的,可無用之用大矣哉!以前曾把新中國說成是一張白紙,可以任意揮灑,一個有著五千年文明積累的古老民族,想要割裂傳統,無視歷史的做法,已經釀成了無可挽回的悲劇。本文提出曾久被壓抑的歷史連續性問題,試圖用通貫的眼光審視古今之變與不變,珍視文化傳統的價值。司馬遷早在兩千年前就提出成熟的史學思想——“通古今之變”,歷史學的精髓主要在于此,任何一個從事歷史教學的人都不容漠視!
歷史不是一門支離破碎、難以闡釋的學科,也就是說,歷史并不是無數彼此不相關聯的事實碎片的偶然結合,而是有連續性的。這就需要我們努力探求歷史變遷的內在聯系,對許多重要問題的因革損益有所說明,所謂“通古今之變”的中心涵義即在于此。古與今、歷史與現在之間是相通的,這種相通最重要的根據便是歷史的連續性。所以多一分對過去的了解,就多一分了解今天的根據。畢竟今天是昨天發展演變過來的。歷史盡管有變動,終有不變者在。我們如果細察歷史之變微妙處,一切發展變化都是連續中積累性的變。那種完全割斷歷史的“變”從來也沒有發生過。用通貫的眼光嵩目古今之變與不變,正是我們今天專題史教學的要求,每一個專題都是通貫古今、關聯中外。要了解人類政治領域中的制度、事件、人物在人類文明演進歷程中的影響與作用。我們不僅要分析政治事件、政治制度、政治人物本身的特點,以及與社會經濟、思想文化活動的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關系,更需要綜觀,有一番登高遠矚的景象。如果要探索蘇聯70余年的歷史,必須從帝俄歷史中去求解,并非完全因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哲學憑空特起,蘇聯農業集體化過程中慘象萬狀,其實很大程度上正是帝俄時代農奴制度的延續。還有,中國古代千年的輝煌何以轉向近代的沉淪,如果把原因單純地歸咎于“列強的侵略”,正是忽略了歷史連續性的思考。輝煌與沉淪之間究竟有怎樣的內在關聯?近代以來的苦難歷史迫使我們不能不追問19世紀以前的歷史,追問原有的社會機制到底出了什么毛病,有了這樣一種通貫古今的眼光,才會得出根本性原因就在于大一統的高度中央集權體制,這一政治模式自然具有動員、組織社會的巨大力量,但時過境遷,已成為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障礙。
“一國家當動蕩變遷之時,其以往歷史在冥冥中會發生無限力量,誘導著它的前程,規范著它的旁趨,此乃人類歷史本身無可避免之大例。否則歷史將不成為一種學問”。①所以錢穆先生教人研究歷史強調要向大處遠處看,切忌近視。那些在歷史上廣泛而持久的活動,其影響完全有可能是由古及今的。時間的遠近不會成為衡量歷史價值的標準。正如孔子的影響不低于雷鋒。所以黃仁宇提出“大歷史觀”,認為把一個歷史事件、人物放在近代15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段中才能看清事件之間的因果流轉和真實意義。近代中國社會變化劇烈,恐怕只是就它的表象而言,中國社會許多制度上的和人文環境方面的痼疾,上千年來其實并無多大改變。西諺說得好:“已有之事,后必再有。太陽底下,并無新事。”“沒有新事”當然不可能是以往之事的簡單重演,但從本質上看人性、社會特性并不會有怎樣大的改變,我們如何知道過去發生的許多情況,今后就一定不會發生了呢?新中國建立后,特別經過“三反”運動之后,一般人都認為像國民黨晚期政府官員嚴重貪污腐化的情況將不會再發生了,由此看來我們怎能低估牽制社會發展的惰性力量呢?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有一段著名的話:“人們自己制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選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當人們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圍的事物并創造前所未聞的事物時,恰好在這種革命危機時代,他們戰戰兢兢地請出亡靈來給他們以幫助,借用他們的名字、戰斗口號和衣服,以便穿著這種久受崇敬的服裝,用這種借來的語言演出世界歷史的新場面。”當社會條件、人的思想觀念并未發生根本改變的時候,那些聞所未聞的創造只不過改頭換面,本質上一仍舊貫。皇帝制度可以隨溥儀的一紙詔書而退出歷史舞臺,而變相的皇權依然繼續存在,皇權的思想、觀念如影隨形,用這樣的通貫眼光進行深層分析可以使我們了解中國的現代化何以一波三折、難局所在。
既然歷史是一個連續的過程,以往的歷史又會或隱或顯發生著很大的影響力,這就不能不讓人真切地感受到任何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文化傳統持久而堅強的精神力量,這要比階級意識,特殊的政治理想更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民族可以盡棄其文化傳統而重新開始,現代化也只能是在本國文化傳統的基礎上展開。所謂進步是包容舊的再增加了新的,決不能認為進步便是不要舊的,否則只會釀成悲劇。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德國頒行魏瑪憲法建立起魏瑪共和國,這部憲法和這個共和國充分體現了民主精神,但由于德國封建殘余意識濃厚,德國人民崇拜權威的心理,這部憲法以及由這部憲法建立起來的魏瑪共和國完全脫離德國文化背景,德國民眾竟然通過選舉導致納粹黨的崛起,釀成了滔天大禍。
我再舉另一例子,司馬遷的《史記》,開創了以人物為中心的紀傳體通史的范例,創造第一部正史,為以后兩千年所沿用,司馬遷為何有這樣開創性的成就呢?殊不知本紀是全書的大綱,從頭到尾的大事都是提綱挈領寫在里面,是仿《春秋》編年體例寫的;“八書”是《尚書》體例,專為一件事而特作一篇書;世家主要是分國的,如《魯世家》《齊世家》《晉世家》等,雖類似于《國語》《國策》這樣一種國別史,但《史記》的“世家”主要還是記事為主的;“列傳”是《史記》中最主要部分,突出了人物的重要地位,其實先秦諸子的書里記載著一個人的事與言,如《晏子春秋》,把晏子一生的言行寫成了一部書,已經突出了人的重要性,在司馬遷之前早就有在歷史中特別看重“人”的事實,所以太史公是繼承了以往史學上的各種體裁的基礎上而進行的創作。前人稱《史記》“體大思精”,這“體大”二字正是需要從通貫的眼光去領會。
有人認為司馬遷因為父親不得參與封禪,更由于個人身世的遭遇,而把《史記》寫成一部“謗書”,如果真如此,《史記》就沒有多少價值可言了。我們還是要用通貫的眼光看待司馬遷如何著史,才能明了《史記》的偉大。我們看司馬遷自己是怎么說的:
先人有言曰: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①
這是說司馬遷寫《史記》是跟著周公的《尚書》、孔子著《春秋》而來的。中國史學自周公、孔子以來就有一種久遠的傳統。那孔子為什么作《春秋》呢?太史公借著董仲舒的話說:
周道衰微……孔子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②
孔子借過去的事情而發表議論,他的議政精神曾達到了貶天子的高度,司馬遷極為推崇孔子,孔子作史的理想不會不對太史公發生一點影響,《史記》敘述漢高祖、漢武帝就跡近“貶天子”。由此可知:我們只有把《史記》置于周公、孔子以來的史學傳統中,始能看清《史記》在二十四史中的特殊價值。
有一種說法:中國傳統與19世紀中葉以后的“近代”不相連貫,中國歷史文化傳統因西方的入侵而中斷了。李鴻章認為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面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那么也就是說近代發生的前所未有的變局完全是由外來沖擊造成的。用“西潮沖擊—中國反應”說來解釋近代中國思想的演變,就是忽視了中國文化傳統從明清甚至宋元以來的內在漸變,也就是說近代中國社會轉型的動力之一是中國文化傳統的自身演變。歷史是一種漸進累積的連續性過程,每一民族、國家都有自己獨特的歷史運行軌跡和歷史連續性,不可能不經過自身的選擇去接受外來的影響和干預。傳統與近代之間怎樣詮釋“通古今之變”,我試圖在思想史領域,用通貫的眼光,為近代變局提供一個縱觀的視角。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屢為西方所敗,我們對西方折服的是“船堅炮利”,對自己文化的信心并未動搖,但是甲午喪師才成了轉變的真正關鍵,中國為日本所敗,我們不是更仇恨日本,而是對日本更加尊敬了,日本取法西方,維新自強,是值得我們效仿的。當時的知識分子抱著急迫的心態去擁抱西方,這些都是為大家所熟知了的。客觀地說,19世紀末信守儒家的知識分子包括康梁,對西學并沒有全面而深刻的認識,但他們對西方的制度、觀念之所以會一見傾心,一個合理的解釋是他們的文化價值體系中必定有許多東西與西學產生了強烈的共鳴,也就是說,儒家經典中已萌發了許多現代意識。
明清奉程朱理學為官方正統思想,現代批判儒學的人據此斷定儒學是維護君主專制的意識形態。程頤說:“天下治亂系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③程頤不僅要用儒家經典的教育來規范君權,而且主張在權力世界中相權應居于中心地位,一身任天下之重,在程頤的語氣中皇帝可有可無,簡直成了“虛君”。北宋以來皇權不斷在膨脹中,信守儒家的士大夫對皇權已流露出深深的不信任。南宋朱熹是道統論的正式提出者和道學(理學)的集大成者,這個道秉承了上古以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傳之道,來規范君權,致君行道,朱熹因此極力構建一個道統與治統合一的三代之治,不管朱熹他們是否真心相信上古史上的“三代之治”,但他們以此表達出對現實政治的強烈不滿是顯然的:“千五百年間……堯、舜、三王、周公、孔子之道未嘗一日行于天地之間也。”④由此朱熹得出一個大膽的結論:秦漢以來的所有帝王都是無道之君,所以才導致政治的長期黑暗。明亡以后,黃宗羲仍念念不忘用相權來制約皇權,黃宗羲激憤地指斥,“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罷宰相始”。⑤黃宗羲講這句話是有切膚之痛的。難怪乾隆帝對宰相制度和程頤的這句斷語深惡痛絕:“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誰乎?使為人君者,但深居高處,自修其德,惟以天下之治亂付之宰相……此不可也,且使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亂為己任,而目無其君,此尤大不可也!”①儒學政治理論的核心部分恰恰是君主專制的一個主要障礙。在乾隆痛加批判中,說明信守儒家價值的士大夫用相權來抑制君權的思想并未完全泯滅,甚至在潛意識中潛滋暗長,一到清朝統治危機全面呈露,無法用高壓手段維持穩定的時候,龔自珍喊出了“一人為剛,萬夫為柔”,②“龔自珍的今文經學終于在康有為手里取得了豐碩的收獲”。③
心學的集大成者王陽明是生活在“朝綱紊亂”的武宗朝,他主張“是非之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謂良知也”。④既然良知是一個是非之心,良知又是人皆有之,那么檢驗真理、是非的標準已不在皇帝,而是每一個人,陽明提倡“致良知”“知行合一”,從這一角度看,陽明的“良知說”涵有深刻抵制專制的意義,與西方宗教改革稍相類似,良知說也是個體心靈上的一次解放。黃宗羲是“清代王學唯一之大師”(梁啟超語),這樣的是非觀到了黃宗羲的思想體系里已開始觸及到了制度層面。“天子所是未必是,天子所非未必非,天子遂不敢自為非是,而公其是非于學校”。在黃宗羲眼里,學校不僅是培養人才的地方,更成為制約君權、決定是非的最高機構。不過所要說明的是,明清儒家思想向往的依然是三代之治,他們撤不走政治道德化的心理障礙,正如錢穆先生所批評的“只研究治道,不研究政體”。儒家思想在中國全面接觸西學前已陷入了無法有效突破的思想困境。當興民權、開議院、行君主立憲制等思想等傳入中國時,怎能不讓康梁等維新派歡欣鼓舞!他們終于在西方民主制度中發現了解決君權問題的具體辦法,吸收西學便成為當時主流思想——儒家思想的內在要求,或者說維新派通過西方的價值觀念重新發現了儒家經典的現代意識,突破了儒家傳統的限制。1898年,康有為發表《孔子改制考》,用孔教的名義提出變法要求,這一托古改制的辦法,有人稱之為“舊瓶裝新酒”。如果沒有儒家思想這一舊瓶,他們是喝不到“新酒”的。從史學觀點看,儒家思想在不斷變動之中,其中蘊含的現代意識,更使“舊瓶新酒”的喻義順理成章了。
在讀史的過程中,對許多歷史現象的分析必須從歷史連續性方面出發思考。嚴耕望注意到,“歷史的演進是不斷的,前后有聯貫性的,朝代更換了,也只是統治者的更換,人類社會的一切仍是上下聯貫,并無突然地差異。所以……注意的時限越長,愈能得到史事的來龍去脈。……研究一個朝代要對上一個朝代有極深刻的認識,對于下一個朝代也要有相當的認識”。⑤嚴耕望的觀點正可說明觀察某一時代的歷史現象要照顧到該事象在前后時代縱的線索,但不可忽視的是該現象與同一時代相關現象之間可能存在的橫的關系也同樣重要,比如中國的現在不單是由歷史因素決定的,我們沒有理由讓歷史承擔過多的責任,否則刻意用歷史來解釋現實,其目的不是為現實辯護就是對現實加以譴責。馬克·布洛赫說得好:“唯有總的歷史,才是真歷史。”⑥布洛赫顯然不會同意一元論單線思維方法,比如文化決定論、經濟決定論還是歷史決定論。任何方法、經驗都有它使用的限度,越過這個限度必然會產生謬誤。
【作者簡介】潘致遠,男,中學一級教師,浙江省新昌中學歷史教師,主要研究方向為歷史教學研究與思想史研究。
【責任編輯:王雅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