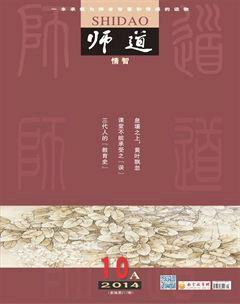留學美國途中……
彭行影
接到約稿的時候其實非常惶恐,想來我已經一年多沒有動筆了。上學的時候總是有想法沒有精力,時間一過再提筆又覺得矯情。我胡亂構思整整兩天硬是沒能寫出一個字,于是就無恥地翻起了在學校的時候隨手寫的段子。
“大二我搬到了有廚房的公寓,每次課間時間緊沒時間吃飯的時候就在早上蒸兩個速凍的奶黃包帶著。公車上打開保溫盒的時候總有一種錯覺,好像那兩個圓胖的白面團是媽媽早上放進來的。
不知道為什么人越大卻越脆弱,大概無知才無畏。
那個學期臨走的時候爸媽幫我把行李堆上車,我看著那個大概比我更少女的上躥下跳著讓我看手機鏡頭的母親,沒忍住讓她拍了個哭臉。后來擦爛了爸爸給我的紙巾,還被的士司機嘲笑說第二次走還這么激動。
我覺得生活層層疊疊地爬滿了我的心,讓我留戀一切溫暖,不忍直視分離。
還是那個學期,有一次熬夜完了又要早起繼續寫論文。半夜聽見室友在走廊經過,恍然好像回到了初中的時候,爸爸會來敲我的門問我怎么還不睡。
我怎么還不睡?其實我好困。”
最常問的問題
放假回國時總有家里的親戚朋友問“在美國上學有什么好玩的事情”,“美國生活是怎樣的”諸如此類的問題。每次被問到總有一種劈頭蓋臉之感,我不知道從何答起,也不知道別人具體想知道些什么。
1. 出國后最常被問到的問題——“有沒有美國朋友”?
這個問題爸媽問過,親戚問過,剛入學的學弟學妹也問過。長輩大多比較擔心中國人抱團不跟其他學生交流,又害怕沒有中國人沒法互相照應。
其實對于留美的中國學生來說,因為學校專業和地理位置不同,經歷也會很不一樣。
首先,很多人都知道美國大學主要分兩種。一種是綜合類大學(University),這類學校一般校園較大人數較多,課堂規模有大有小,以大課為主。另一種是文理學院(Liberal Arts College)。這類學校人數會少很多,基本上所有課堂都不會超過30人。學生之間、師生之間的聯系也會更緊密一些。
我的學校就是一所很年輕的文理學院,全校只有不到1700人。由于是上個世紀60年代建校并且校風非常的左,學生群體以白人為主。國際學生只有不到一百人,中國人更是少之又少。平時學習一旦忙起來彼此連面都很難見到,更不要說抱團了。而學校的整個圈子比較小,所以大家不分國籍還是比較相親相愛的。
對于很多在University上學的中國留學生來說,因為學校里中國人多,學生群體的基數又太大,中國朋友自然就多,甚至可以分地域集體活動。而一般大家在學校里面交到的朋友都是機緣促成,跟國籍和群體關系并不大。外向一些的人可能會參加更多的社交活動,但普遍來講留學生的社交并不刻意。
2. 很多人常常會籠統地問我:“美國人是怎樣的?”
其實,一個國家的人確實有文化上的共性,但是每個人因為家庭背景、性格以及經歷的不同,是完全不一樣的。就像并不是所有中國人都相親相愛玩在一起,我們在交朋友的時候,也有玩得來的美國人和玩不來的美國人。每個人在學習生活穩定之后都會有一些固定的朋友,而這里面并不一定有任何國籍的規律。總的來講,白人并不是一個比我們高級的種族,也大可不必為了“有白人朋友”而跟聊不來的人浪費時間。
我大二跟七個人同住一個兩層的公寓,一共八個人來自五個不同的國家。大家本身就是很好的朋友,最大的娛樂就是拿彼此的國家和文化打趣開玩笑。公寓里的美國男生無論如何都不相信我的“濕頭發睡覺會頭疼”理論,在我們無數次爭論之后,他依然會在我吹頭發的時候狠狠嘲笑我。墨西哥妹子會讓我們閉上眼睛然后給我們每個人喂蟲子,諸如此類。
3. 在美國是怎樣上大學的?
其實現在國內的很多人還持著“去美國上學就是天天party”和“在美國上學大概輕松不少”的偏見,我也是被問到類似問題才發覺這個事實,所以這一點還是值得科普一下的。
我接受過的中國的教育模式大致是:老師上課講解,學生課后寫作業鞏固,其間老師答疑,然后考試檢驗。所以上課聽講這一環節是最最重要的,身為高中老師的父親還曾經給我舉過他的學生“高中三年沒有寫作業,但是上課從來不走神最后考上深大”的例子來教育我好好聽講。而我接受到的美國的教育模式與此不同在于:老師一般會在課前布置閱讀任務,然后上課進行講解討論和答疑,然后再布置論文或者更多練習,最后再考試。想要從一門課中最大程度獲益,課前一定要非常認真地讀完老師布置的閱讀,并且帶著問題和觀點去課堂,否則沒有辦法參與課堂,與老師和其他同學同步思考。也就是說這其中自學占了非常大的一部分。
4. 我所在的大學特點?
已經說過了我們學校比較左,制度也比較另類比較自由。一般學校都會有期中期末考試,然后依據成績和等級計入GPA(平時成績)。我們學校除了語言和樂理等應用性比較強的科目外,大部分科目都沒有考試,也沒有GPA。學生成績的評估都是老師的文字評價,所以別人的成績單是一張紙,我們的都是厚厚一沓。許多人都覺得這種制度下學習過于輕松,太容易渾水摸魚,但其實所有老師對自己的課都有出席率和課堂參與等等要求,到期中和期末也會布置不同工作量的項目來代替考試。如果有些要求沒有達到就不會對這個學生給予評價,也就是說這個學生就沒有過這門課,也拿不到學分。到目前為止,我拿到的評價都是非常誠實的,包括缺席遲到了多少節課,哪些做得好哪些做得不好,事無巨細都會寫出來,批評和表揚都不吝嗇。
至于課余時間的多少,取決于選多少節課,每節課的工作量多少。課余時間參加什么活動,要不要去party,也完全取決于個人喜好。我們學校與毗鄰的Amherst College, Smith College, Mt.Holyoke College 以及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是五校聯盟,大部分情況下都可以五校之內自由選課,圖書館等資源也是共享的。我的不少同學一天要跑兩三個學校趕課,沒時間吃早飯中飯是常有的事情。
我的專業是燈光設計,屬于戲劇這個大類。我們學校要求戲劇專業的學生除了修滿戲劇不同方面的課之外,還要在五校范圍內的學生話劇作品中完成臺前幕后不同的工作。這些話劇作品大多是大四學生的畢業作品,規模不亞于專業的劇院作品。所以我們常常要用課余時間畫圖做模型,參與排練或者會議。到了tech week(合成)的時候(也就是把演員和燈光音響舞美服裝等等放在一起彩排),就是一下課就到劇場不停地排練調整,再排再調整。常常連續一周每天凌晨才能回宿舍,說不定還有作業要寫,第二天往往還有早課。當參與的話劇作品在另外一個學校時,往往排練結束公交也停運了,于是還要想各種辦法回學校。所以對于我的朋友們來說,我時不時會“消失”一周,然后重新在食堂等公共場合出現。每次都會被打趣“原來你還活著”。
我的專業和學校比較小眾,我也只能為自己代言。但是每個專業都有自己難念的經,以什么方式學習、生活也是個人的選擇。如果在任何時候自己家人或身邊人想要出國留學,希望大家保留意見,避免假設。
最艱難的事情
文理學院更加注重的是基礎教育和所謂人格教育,大部分文理學院在大一的時候都會要求學生修滿很多不同領域的科目。至少我們學校的這類要求就非常繁雜,好多人到了大二都沒有修滿。
當時對于我來說最難的是寫作課,相信很多中國留學生都面臨過同樣的問題。出國之前,除了準備托福和SAT之外,我們所學的一直都是課本英語,先不說能不能充分理解各種文學作品,大學里布置的research paper更是從來沒寫過。我上的寫作課的大課題是《了不起的蓋茨比》,并且通過這本書來研究美國上世紀20年代的社會狀況和文化。當時老師布置的閱讀和論題都非常具體,并且她本人也是一個對文字非常較真的人。我的每一篇論文交上去再拿回來都是從語法到邏輯鮮血淋漓。那是我大學的第一個學期,還在努力地適應語言、生活等各方面的事情,課堂上就算有一些想法也因為怕出丑而不敢主動發言。老師曾經有一次在我毫無頭緒的時候問我有沒有話要說。最壞的預感被實現,從那以后我一想到這節課就不能更惶恐。不過當時要是沒有這堂課,可能我到現在都不會寫論文。
我的恐懼感可以與此媲美的另一件事就是presentation。寫作課上的展示還好說,一般只要表達清楚自己的觀點,大部分時間大家其實都是在復述自己文章里面的東西。還是第一個學期,我選的燈光設計入門要求所有人做展示。這是完成一份設計中重要的一環,也就是向導演解釋清楚你的創意并讓團隊理解,同時要找到各種圖像作品來支持你的展示。聽起來好像不難,但是創意是一個非常抽象的東西,要讓一個屬于你自己的東西被人理解涉及到很多的咬文嚼字,和不同展示形式的支持。記得我第一次展示的時候幻燈片有一點點小問題,我拿著一個小本子上臺講得嗑嗑巴巴斷斷續續,也幾乎沒有看觀眾。現在回想起來都有捂臉的沖動。老師說對于一個設計師來說這是必須要過的一關,所以那個學期我們每人大概做了差不多10個presentation。到后來所有人都沒有心理障礙了。當時一起上課的大部分都是同專業的人,后來相處久了才發現,學這個專業的人大多都是心思細膩但是比較靦腆的。不管英語是不是第一語言,所有人在人前說話都會緊張,一開始都是跟我一樣有心理障礙的,而且他們也會出現表達不清楚的狀況。我還發現,一般只要是用心想過的設計,觀眾一般都可以理解我想傳達的意思。偶爾的語法錯誤從來沒有影響過他們,甚至都沒有注意,更不會像我擔心那樣的笑話我。
后來慢慢地形成了一些不好的說話習慣。到了燈光中級班,在展示的時候一猶豫就會說“I dont know”。后來老師不能忍受了,就要求我以后每說一次“I dont know”, 就要給班上每人一個quarter(25美分)。雖然班上只有4個人。從那以后我果然忍住了,沒再說“I dont know”。
最本心的抉擇
前幾天見到一個在國內上大學的高中同學,說起我下個學期要去英國交換的事情,他一臉羨慕。他說國內學校很少有這樣的機會,還提到他正在準備讀研究生時出國,很多我們的高中同學都在準備轉學交換或者出國讀研究生。
我沒有在國內上過大學,了解的皮毛也都是從朋友們口中聽到的,所以對此沒有什么發言權。我非常感恩自己出國之后受到的各種鍛煉,但一直到目前為止,我也沒有體驗過社會和職場是怎么樣的,所以當有人問到以后會回國還是留在美國,我都沒有答案。
教我中級燈光設計的老師是中國人,她暑期在北京剛好自己導了一部戲,我便自告奮勇當了廉價勞動力。從來沒有在國內劇場做過事的我本來非常的誠惶誠恐,后來才發現原來老師們都很友善沒架子,劇組氛圍也很輕松。大家每天互相調侃,也沒有人抱怨時間緊熬夜晚。在學校做事的時候其實大家也很少有不愉快,而且說實話很多事情都比國內要處理得專業有效率得多。但我卻打心底覺得在美國沒有在北京時忙里偷閑的幾句插科打諢來得有滿足感。
很多人都覺得理想的生活總是在別處。我沒有辦法把美國和中國細細比較,也不想去評論哪個更好或更差。我相信很多學生都跟我一樣,還遠不能判斷什么樣的生活更適合自己。
希望你現在或以后作出留下或離開的決定,都是為了讓自己更快樂。
責任編輯 蕭 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