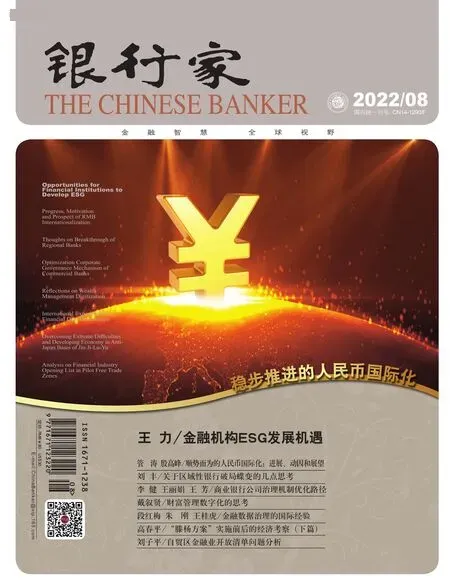宏觀調控三題
王松奇
新華社連發三篇“刺激與改革之辯”系列文章后,在國內經濟學界引起反響,特別是文章中批評“克強經濟學”這一概念化的表述以偏概全,造成了刺激和改革對立的輿論假象的論述更是深深刺痛了那些創造“克強經濟學”概念及對“克強經濟學”三大支柱假說進行鼓吹的人。這一現象似乎說明,去年6月,“克強經濟學”概念在巴克萊銀行內部刊物《全球資本客戶》上第一次出現只是某個知識分子靈光一閃的產物。這里有幾個有意思的需要深入討論的問題:
問題1:微刺激也是刺激,如此一來“克強經濟學三支柱”說已然不成立
所謂“克強經濟學三支柱”說也是“克強經濟學”概念的發明者黃益平教授提出的。但在2014年春季的博鰲論壇上,克強總理在演講中明確提出,對于中國經濟即使出現增長減速也不搞強刺激。幾乎所有人都從這次演講中聽出了弦外之音,即中國經濟還是需要刺激,只是刺激力度不要太強而已。這樣一來,黃益平教授去年6月初提出時的所謂“不刺激、去杠桿、搞改革”三個支柱就已經三去其一了。可以想見,象牙塔里的學者在創造概念時是沒有同克強總理本人溝通的。
中共十八大以來,習李體制最大的特點就是年富力強真抓實干,從政治、經濟、文化到外交,方方面面都顯現出腳踏實地、不務虛名的特點。因此,對這樣務實的領導人,如果從執政之初就被某些生造的“XX經濟學”概念套住,那倒是實在讓人難以理解。如同那句老話所說:“理論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樹常青”,中國經濟進入2014年在外需銳減,內需不振時,克強總理及時提出“微刺激”舉措,實際上就是中國6月份宏觀數據向好的關鍵政策原因。我們可以盤點一下,自從2013年中央八項規定提出和今年“反對四風”運動推行以來,全國的餐飲、服務業已出現明顯經營萎縮,大量產能過剩行業存在的現實又使得制造業從現實運營到新增投資都出現萎靡不振狀態,在全球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仍然對外需存在后續影響的情況下,如果中央不及時提出以鐵路建設、棚戶區改造及小微企業減免稅為基本內容的微刺激方案,中國下半年的宏觀經濟數據肯定會難看許多。
當然,許多固執的教授會提出一個看似滿有道理的問題——“速度低一些即使不超過7%又能怎么樣?”這種不當家不知柴米貴式的發問的確讓人哭笑不得。
中國的增長速度本身就是中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優勢之一,無論在發達工業國家還是新興市場國家,中國速度總是會讓人艷羨不已。連續35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是什么,我認為這就是中國人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實踐源頭。如果中國經濟還像文化大革命中那樣整天喊“形勢大好越來越好”,老百姓卻連飯都吃不飽,像1978年以前那樣整天講馬列、喊毛澤東思想經濟卻已到崩潰邊緣,我們還有什么本錢說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所以,用活的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實踐,不囿于任何條條框框,一切改革和發展政策選擇均以實效顯著為最終著眼點,領導人不務虛名、經濟學家不搞吹捧、文官不貪財、武將不怕死,這樣的局面才是最理想的社會景象。而這種局面形成的物質基礎就是年度經濟增速不能低于7%,只有在7%?8%之間,中國的就業、財政收入水平、產能消化、居民收入才能維持在一個不太難看的水平上,這就是中國國情。在美歐日等經濟體年GDP增速能達到3%,那就已經很高了,但在中國,只有在7.5%左右,方方面面的矛盾才不至于激化,政通人和的景象才能維持。所以,當外需萎縮內需不振時就一定要搞一點兒刺激,哪怕是“微刺激”,不搞刺激,任由經濟增速下滑再用所謂“新常態”的說法搞自我安慰,實際就是政府失職。
問題2:經濟增長與刺激和改革的關系
本屆政府一直在強調改革紅利問題,這種通過深化改革舉措來挖掘增長潛力的思路當然不錯,但中國目前已發展到這樣的階段——即當年那種將人民公社集體土地分解為家庭聯產承包的突然制度轉換式的制度變革刺激條件已不復存在了,現在,流行的說法是“改革已進入深水區”,這種語焉不詳的比喻含義是什么誰也說不清楚,但至少有兩點可以肯定,一是水深可能情況不明;二是水深何時觸底難以確定。綜合這兩點可以說改革如果被視作是經濟發展經濟增長的作用因素,它只能是一個慢變量,對以短期指標變動判斷為主要特征的宏觀經濟形勢來說,企圖靠改革來解決工業增加值、消費、投資等短期問題,恐怕不現實。能實實在在起作用的政策只能是貨幣財政政策等手段。1929?1933年經濟大蕭條、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及爾后的歐債危機,我們如果留心觀察就會發現,它們的應對處方大體相同,即寬松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貨幣一松,內需一提振,所有的蕭條和衰退都會在一段時間的政策持續期后消失,這就是世界經濟發展史告訴我們的一條重要經驗。改革以體制制度調整為著眼點,它要解決的是中長期問題,改革效果通常也是在中長期才能顯現,而刺激政策無論對何種體制的國家,它都是解決短期問題的有效處方。該刺激就刺激,即使有人說三道四又能如何?
問題3:由“大水漫灌”改為“定向滴灌”的癥結在哪里?
克強總理最近在講到微刺激政策同強刺激政策的區別時,用了一個十分形象的比喻,說“我們不搞大水漫灌而是采用定向滴灌”。這句話說得非常精彩,問題是怎樣落實“定向滴灌”。顯然,無論是漫灌還是滴灌,你要首先弄清楚誰在管水,有多少水可供分配,誰負責閘門和渠道,哪里最缺水等等,也就是說,只有把可供刺激的資源總量和分配權力結點搞清楚了,我們才能有效落實所謂“定向滴灌”問題。從已出臺的微刺激措施看,鐵路建設即使短期甚或是長期效益也不明顯,但最大好處是給中國留下一大筆優良基礎設施,中國的高鐵已令全世界羨慕不已,因此,這項投資算大賬永遠不吃虧。其次大力推進棚戶區改造,既是民生工程,又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消化過剩產能,這也是有利無害的刺激舉措。還有小微企業政策優惠,這似乎是一項短期效果不明顯的刺激政策。因此。我們從已出臺的三項微刺激措施看,如果強化刺激效果,要讓“定向滴灌”政策效果更明顯,就要從中央銀行——這個中國經濟供水總閘門入手,想一些既增加水供應量又能解決“定向滴灌”問題的辦法。我們的央行已經出臺的措施有定向降準,下一步似乎還可以采取定向取消貸款規模控制的做法。中央銀行每年年初的信貸規模分配是最具漫灌特征的貨幣政策執行方式,缺水地區支持和定向滴灌的功能基本不具備,如果對有些行業不設貸款規模限制,那就等于是解決了對缺水地區的“定向滴灌”問題,所以從大水漫灌到定向滴灌,我認為關鍵是解決執掌水分配部門傳統工作方式和模式的問題。
這里面還有一個需要厘清的問題是:由政府系機構分配的水和社會上散處于萬千江河的水到底怎么引導使其都能體現定向滴灌思路?社會上的水看來就要靠價格信號,靠利益關系調整來誘使其自動流向缺水地區。這就要運用稅收及補貼等多種手段。我早就說過,中國有三個政府: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由掌管政策資源的國家各部委構成的“二政府”。克強總理推行的簡政放權主要是削減“二政府”的權力,“改革60條”講讓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實質涵義也是解決“二政府”權力過大問題。現在為提振經濟增速,中央政府的定向滴灌思路能否有效落實,關鍵也要看“二政府”的官員們是否作有力配合的舉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