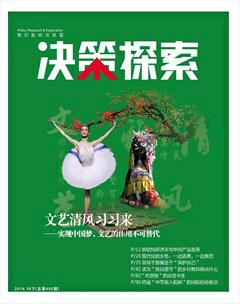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際經驗教訓
鄭之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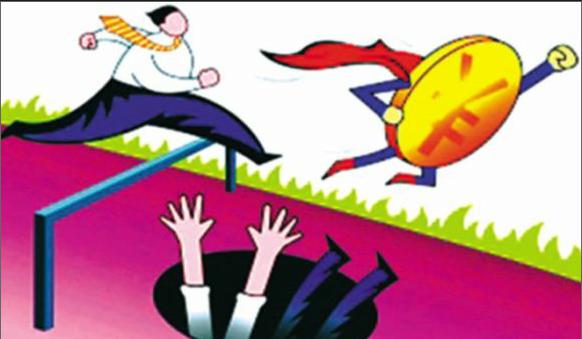
20世紀60年代初期,有100多個國家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至今進入高收入國家的只有寥寥十幾個,且大多數是小國。中國已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有人認為中國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可能性很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分析跨越陷阱國家的成功經驗和跌入陷阱國家的教訓,對中國未來發(fā)展非常重要。
一、 韓國和日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經驗
韓國和日本是通過增長動力機制轉換和經濟發(fā)展體制改革,成功實現經濟發(fā)展方式轉變,進而順利成為高收入國家的典型,對中國的借鑒意義較大。總體而言,從日本、韓國的經驗看,跨越陷阱實際上是競爭力的階段性提升和跨越問題,日韓持續(xù)增長能力的核心是培育出內生增長動力,最關鍵的是實現了從“模仿”到自主創(chuàng)新的方式轉換,其主要經驗包括以下幾方面。
(一)調整經濟發(fā)展方式
從20世紀50年代初到80年代,日本實現了輕工業(yè)—重工業(yè)—第三產業(yè)的適時轉換升級,完成了由“貿易立國”到“技術立國”再到“文化立國”的轉變。20世紀80年代以后,西方國家奉行貿易保護主義,極大地沖擊了韓國出口導向型經濟。韓國提出“產業(yè)結構高級化”的政策目標,加速從依托增加資金投入、維持廉價勞動力的粗放型發(fā)展戰(zhàn)略,轉為主要依靠增加研發(fā)投資和提高產業(yè)科技含量提升競爭力。韓國大力發(fā)展以電子工業(yè)為核心的技術知識密集型產業(yè),整頓輕紡、纖維、染色等低附加值產業(yè);將汽車、造船、機械等產業(yè)的制造工程逐步轉移出去,國內主要抓研發(fā)、設計等前端工程及營銷、售后服務等后端高附加值工程。這為韓國在全球產業(yè)調整過程中搶占先機,實現可持續(xù)發(fā)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二)依靠技術創(chuàng)新立國
高收入經濟體在中等收入階段,均采取各種戰(zhàn)略和措施來提高本國的技術創(chuàng)新能力,以此在國際競爭中占據有利地位。1982 年,韓國正式提出“科技立國”戰(zhàn)略,并明確其主要目標是利用先進技術改造原有產業(yè)。進入 20 世紀 90 年代,為減輕對發(fā)達國家的技術依賴程度,韓國進一步實施“科技立國”戰(zhàn)略,發(fā)展本國高新技術產業(yè)。與韓國類似,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日本也確立了“創(chuàng)新立國”戰(zhàn)略,并把它作為新時期經濟發(fā)展的基本國策。
(三)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20世紀70年代,韓國經濟發(fā)展模式的顯著特點是資本投入增長速度非常快,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負值,經濟增長依靠的是要素投入。但到20世紀80年代,韓國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的貢獻率達到了28.94%,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了勞動投入部分,成為僅次于資本的第二大發(fā)展動力。1998~2011年間,韓國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44.87%,成為促進經濟增長的主導因素。韓國真正實現了經濟轉型,轉變?yōu)橐揽咳厣a率發(fā)展的創(chuàng)新型經濟發(fā)展模式。日本經歷了1951~1974年的高速增長期,1975~1993年的平穩(wěn)增長期,以及1994~2005年的失去的十年期,每一個時期最重要的標志之一就是全要素生產率的同向升降。
(四)調整收入分配格局
韓國政府通過稅收政策調整初次分配格局;通過社會保障措施調整再分配格局。1980年代以后,基尼系數明顯降低,收入分配趨于均等化。1991年韓國的基尼系數由1980年的0.39降至0.26,社會高收入階層與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差距明顯縮小。
(五)實現城鄉(xiāng)均衡發(fā)展
20世紀60年代,在工業(yè)化進程中,韓國城鄉(xiāng)收入差距逐步拉大。1970年,韓國政府啟動旨在縮小城鄉(xiāng)差距、工農協(xié)調發(fā)展的“新村運動”。韓國《農林統(tǒng)計年報》顯示,1970年韓國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比例為44.7%,2005年下降到6%。農民在其他非農部門大量兼業(yè),城鄉(xiāng)收入分配發(fā)生了顯著變化。20世紀90年代初,韓國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已經達到城市居民人均收入的95%,城鄉(xiāng)收入差距已基本消失。二戰(zhàn)后,伴隨工業(yè)化、城市化的發(fā)展,日本城鄉(xiāng)差距急劇擴大,由此引發(fā)了大城市人口過密、農村人口過疏、農村經濟日漸凋敝等系列問題。日本政府于 1961 年、1969 年和 1977年先后制定了三輪綜合開發(fā)計劃,不斷調整農業(yè)、農村政策,通過加強農村地區(qū)的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完善城鄉(xiāng)統(tǒng)籌的養(yǎng)老、醫(yī)療、教育制度的方式,使城市和農村在法律地位、居民政治權利、社會保障、治理模式等方面具有一致性,有效解除了農民進城或城市居民“下鄉(xiāng)”的后顧之憂。經過幾十年的發(fā)展,日本成為了世界上城鄉(xiāng)差距較小的國家。
二、一些國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探析
許多拉美國家和東南亞國家為何相繼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以下原因不可忽視。
(一)發(fā)展失速
“中等收入陷阱”的實質是增長問題。在具有持續(xù)增長能力的經濟體內,各種社會矛盾可以通過增量調整的方式逐漸予以解決,而在增長停滯的經濟體內則只能被迫進行存量調整,陷入“增長停滯—社會動蕩—經濟失序—復蘇無力”的惡性循環(huán)。一國經濟必須保證持續(xù)發(fā)展,否則就會跌落“中等收入陷阱”。整個拉美地區(qū)20世紀80年代經濟年均增速1.2%,人均GDP增長只有-1.9%,其中1963~2008年的45年間,阿根廷還出現了16年負增長。
(二)結構失衡
巴西、墨西哥、阿根廷、馬來西亞、泰國長期存在結構失衡。第一,產業(yè)結構失衡。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國忽視具有比較優(yōu)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yè),卻轉而發(fā)展資本密集型的鋼鐵、造船等重化工業(yè),導致輕重工業(yè)比例失衡和工農業(yè)比例失調。第二,人力資本和自主創(chuàng)新失衡。高端人才匱乏和低下的研發(fā)能力嚴重制約經濟結構升級轉換。2009年,日、韓研發(fā)支出占GDP的比重超過2%,而智利研發(fā)支出占GDP的比重只有0.7%。2009年,韓國獲授權專利達到9566件,同期馬來西亞僅為181件。第三,城鄉(xiāng)發(fā)展失衡。工業(yè)化發(fā)展嚴重滯后于過快的城市化,大量無地人口涌入城市,就業(yè)、住房、收入和社會保障困難引發(fā)嚴重的社會問題。巴西城市化率從1950年的41.4%飆升到2013年的85%,達到甚至超過發(fā)達國家水平。泰國總人口6000多萬,而首都曼谷人口就達1000多萬。第四,社會保障機制失衡。就業(yè)、醫(yī)療、教育保障投入弱化,對經濟和社會穩(wěn)定形成巨大沖擊。第五,環(huán)境發(fā)展失衡。巴西大量砍伐亞馬遜熱帶雨林的樹木、工業(yè)化種植經濟作物,阿根廷過度放牧,泰國的森林資源基本被毀損,馬尼拉和雅加達大量垃圾被直接傾倒入海中。endprint
(三)資金“失血”
金融體系脆弱的國家缺乏獨立自主的金融體系,經濟嚴重受制于發(fā)達國家資金,特別是普遍存在著借短放長現象,加上過早過度放開資本管制,一旦外資撤離致使資金失血,企業(yè)就會倒閉或瀕臨破產。例如,巴西曾經成為南美的驕傲,但巴西后期嚴重依賴外資,1999年的金融危機徹底擊碎了本已脆弱的金融體系,資金大量失血,經濟下滑至谷底。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國也大致如此。
(四)應對失措
許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當重大困難或經濟危機來臨時,應對失措,使困難演變成危機,小危機演變成大危機。第一,部分拉美國家頑固堅持“舉債增長”戰(zhàn)略。20世紀70年代初石油危機后不久,不少拉美國家繼續(xù)維持“舉債增長”的發(fā)展戰(zhàn)略,同時歐美國家則相繼采取緊縮政策,極度加劇了拉美國家的債務負擔。第二,推行“原教旨市場決定論”經濟政策。20 世紀 80 年代,仍處于經濟增長停滯泥潭的拉美國家將“看不見的手”視作救命稻草,讓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見死不救。經濟監(jiān)控缺位下的救助方案不僅未能消除債務危機的根源,反而導致國際收支更趨惡化。第三,拉美不少國家脫離本國財政金融水平,照搬西方高福利制度。1987~1988年,在拉美較早建立社會保險制度的阿根廷和烏拉圭,其社會保障稅率分別高達34%~45%和54%~57%,接近歐洲國家;有不少國家為20%~30%,也高于加拿大和美國。“福利趕超”扭曲了市場價格信號,導致資源配置失當和宏觀財政上的債臺高筑。第四,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在亞洲金融危機后,未能及時對依靠低成本貿易拉動經濟的模式進行調整,沒有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
三、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應采取的舉措
“中等收入陷阱”的實質是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經濟社會可持續(xù)發(fā)展問題。中國要解決這一階段出現的各種問題,顯然需要多管齊下,例如,優(yōu)化投資、進出口和消費結構,以產業(yè)轉移實現區(qū)域協(xié)調發(fā)展,推動技術創(chuàng)新,著力提高我國全要素生產率,等等。此外,以下幾個方面的舉措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發(fā)揮政府戰(zhàn)略導向作用
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決不能忽視政府的作用。以亞洲為例,成功跨越“陷阱”的大多是政府作用明顯、經濟決策高度集權的國家,而那些放棄政府應有作用的,反而跌入“陷阱”不能自拔。菲律賓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經過30年快速發(fā)展,現代化水平僅次于日本。但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政治、經濟體制完全照搬美國,資金和政策嚴重依附IMF、世界銀行等外國勢力。菲律賓政府作用疲弱,未曾制訂明確的、長期的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導致經濟長期衰退、社會動蕩,由“亞洲典范”走向“亞洲病夫”。戰(zhàn)后日本實行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官產學一體、銀企相互滲透,在短短二三十年里,經濟實力迅速超過英國、法國和德國。韓國政府在60年代初形成以高度集權化為特點的經濟決策模式。新加坡政府在西方看來現在仍然是一個政府相對集權的國家。中國的國情和這些國家的發(fā)展經驗都證明,我們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才能保持自身特色、跨越發(fā)展陷阱。
(二)推進城鄉(xiāng)二元市場改革
中國“城鄉(xiāng)分割”的“二元結構”主要表現為土地制度、公共品供給和公共治理制度、戶籍管理和相關制度的城鄉(xiāng)分割。成功的城市化不是簡單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積擴張,更重要的是要實現產業(yè)結構、就業(yè)方式、人居環(huán)境、社會保障、配套政策等一系列由“鄉(xiāng)”到“城”的轉變。要統(tǒng)籌推進人、地、錢等重點領域和關鍵環(huán)節(jié)的體制機制改革;在城鄉(xiāng)戶籍、農村土地產權、城鄉(xiāng)社會保障和政府財政稅收制度上要有所突破,實現城鄉(xiāng)統(tǒng)籌發(fā)展,在深度城市化進程中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逐步破除城鄉(xiāng)二元結構及城市內部二元結構,近期重點抓好棚戶區(qū)改造,在資金、技術和機制上確保2017年前實現各類棚戶區(qū)1000萬戶改造目標。
(三)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要實現經濟發(fā)展方式從生產推動型向消費推動型轉變,必須依賴收入分配差距的縮小和居民收入的提高。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fā)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形成經濟增長、公平分配和社會和諧的良性互動局面。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快形成中產階級占多數的“橄欖形”分配格局。從減貧、基本公共服務、人力資本建設、就業(yè)創(chuàng)業(yè)等方面入手,提高社會機會均等程度。加快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合理確定稅前抵扣范圍和調整累進稅率,減輕中低收入群體稅收負擔,加大對高收入群體的收入調節(jié)力度。
(四)把改革驅動作為各項應對措施的主基調
金融危機促使全球經濟秩序進行深度調整。為了搶占未來戰(zhàn)略制高點,大國已進入空前的創(chuàng)新密集和產業(yè)變革時代。我們要緊緊抓住新一輪世界科技革命帶來的戰(zhàn)略機遇,牢固樹立經濟增長依靠“改革驅動”“效率驅動”的觀念,以改革對接開放、對接全球化的規(guī)則和機制,提高“中國制造”的競爭力和“中國模式”的影響力,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發(fā)展走上內生增長的軌道。
(作者系國家開發(fā)銀行行長)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