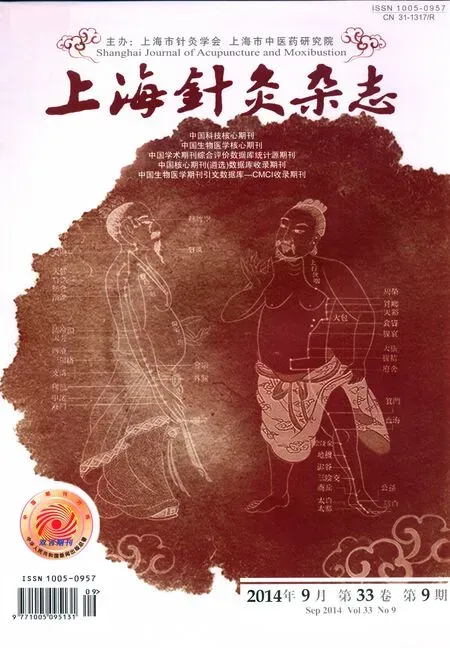電針配合中藥治療糖尿病膀胱病變療效觀察
廖華薇
(南寧市第八人民醫院,南寧 530001)
糖尿病膀胱病變(diabetic cystopathy,DCP)是由糖尿病(diabetic mellitus,DM)引發泌尿系的并發癥,屬于神經源性膀胱中的一種疾病。約有超過40%的DM患者會并發DCP,即使DM患者治療后控制血糖,仍有25%的患者并發DCP[1]。該病嚴重影響患者的生存質量,且易再次引發及加重泌尿系的其他并發癥。隨著我國DM患者的逐年增加,對DCP的認識與治療愈來愈受到關注。筆者采用電針配合中藥治療DCP患者30例,并與藥物治療30例相比較,現報告如下。
1 臨床資料
1.1 一般資料
60例2型DM并發有DCP患者均為2011年3至2013年3月我院住院患者,按就診先后順序隨機分為治療組與對照組,每組30例。治療組中男18例,女12例;平均年齡為(53±5)歲;平均病程為(8.9±6.4)年。對照組中男17例,女13例;平均年齡為(53±5)歲;平均病程為(8.6±6.7)年。兩組患者性別、年齡及病程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 納入標準
①符合1999年WHO對DM及DCP的診斷標準[2];②B超檢查膀胱殘余尿量≥100 mL;③有膀胱自主神經功能紊亂的臨床癥狀表現;④神經電生理檢查有異常表現。
1.3 排除標準
①患有泌尿系統炎癥、泌尿系統結石、泌尿系統先天畸形、前列腺增生、泌尿系統梗阻及癌變者;②高血壓患者;③昏迷及不配合治療者。
2 治療方法
兩組患者均采用DM飲食;均口服或皮下注射胰島素,血糖控制在正常范圍內。
2.1 治療組
2.1.1 電針治療
①肺胃陰虛型取氣海、膈俞、足三里、三陰交、脾俞、中極、關元;②脾腎兩虛型取內關、水溝、秩邊透水道、中極、歸來、腎俞、命門、脾俞、關元、三陰交;③腎陰虧虛型取關元、三陰交、腎俞、膀胱俞、中極、太溪、三焦俞。常規消毒后,采用0.35 mm×40 mm毫針進行針刺,行平補平瀉手法,得氣后接G6805型電針儀,用疏密波,強度以患者可以耐受為宜,留針 30 min。每日1次,10 d為1個療程,共治療2個療程。
2.1.2 中藥治療
①肺胃陰虛型選用補肺湯合養胃湯加減(茯苓、黃芪、阿膠、牛蒡子、陳皮、半夏、太子參、麥冬等);②脾腎兩虛型選用實脾飲合真武湯加減(厚樸、白術、茯苓、芍藥、附子、山藥、枸杞等);③腎陰虧虛型選用六味地黃丸加減(山藥、萸肉、黃柏、知母、龍骨、牡蠣、桑螵蛸、龜版等)。每日1劑,10 d為1個療程,共治療2個療程。
2.2 對照組
口服氨基甲酰甲基膽堿片,每次50 mg,每日4次,共服用20 d。
顯效:泌尿系統癥狀明顯改善,每日尿6~8次,無膀胱尿潴留。
有效:泌尿系統癥狀有所改善,每日尿 8~10次,有輕微膀胱尿潴留。
無效:泌尿系統癥狀無減輕,每日尿10次以上,原有膀胱尿潴留癥狀未改善或加重。
3.3 統計學方法
所有數據采用SPSS10.0統計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卡方檢驗。以P<0.05表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3.4 治療結果
3.4.1 兩組患者臨床療效比較
由表1可見,治療組總有效率為90.0%,對照組為63.3%,兩組比較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提示治療組總有效率優于對照組。

表1 兩組患者臨床療效比較 [n(%)]
3 治療效果
3.1 觀察指標
兩組患者分別在治療前后記錄膀胱殘余尿、排尿時間、平均尿流率、高峰尿流率、腓神經傳導速度等指標。
3.2 療效標準
根據《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3]及《中醫常見病診療標準》[4]并結合臨床擬定。
痊愈:泌尿系統癥狀消失,每日尿4~6次,無膀胱尿潴留。
3.4.2 兩組治療前后尿流動力學指標及腓神經傳導速度比較
由表2可見,兩組治療前尿流動力學的指標(排尿時間、平均尿流率、高峰尿流率、膀胱殘余尿量)和腓神經傳導速度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治療后排尿時間、平均尿流率、高峰尿流率、膀胱殘余尿量和腓神經傳導速度與同組治療前比較,差異均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組治療后平均尿流率、高峰尿流率及膀胱殘余尿量與對照組比較,差異均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
表2 兩組治療前后尿流動力學指標及腓神經傳導速度比較(n=30)(±s)

表2 兩組治療前后尿流動力學指標及腓神經傳導速度比較(n=30)(±s)
注:與同組治療前比較1)P<0.05;與對照組比較2)P<0.05
組別 時間 排尿時間(s)平均尿流率(mL/s)高峰尿流率(mL/s)膀胱殘余尿量(mL)腓神經傳導速度(m/s)治療組 治療前 47.92±6.58 7.47±2.40 9.28±4.55 204.60±54.70 43.81±9.70治療后 37.73±6.271) 11.26±2.391)2) 18.75±4.481)3) 80.30±27.801)2) 57.42±11.301)對照組 治療前 48.31±8.61 7.35±1.97 9.31±3.21 183.6±41.2 45.36±8.4治療后 38.25±7.611) 9.85±2.491) 13.46±2.581) 125.8±40.61) 52.97±10.31)
4 討論
糖尿病膀胱病變是糖尿病神經病變的并發癥,其與循環障礙、代謝紊亂、神經生長因子減少以及免疫功能異常有關[5]。DCP是因為患2型DM后,DM的神經病變累及其自主神經受到損害,且可以較早出現,影響泌尿系統發生膀胱殘余尿量增加及尿失禁、尿潴留等癥狀[6]。DCP患者主要特點為尿量增多、排尿反射減弱、膀胱的尿量增大,出現過多的殘余引發尿頻、排尿不盡、充溢性尿失禁、尿路感染、腎功能不全等一系列泌尿系統的并發癥。
DCP屬中醫學“癃閉”、“淋證”范疇,DCP患者尿的改變是消渴病的下消病癥。《醫學心悟·三消》:“治下消者,宜滋其腎,兼補其肺。”其病機主要是陰虛為本,燥熱為標,氣陰兩傷,陰陽俱虛,在中醫辨證分型論治中,最多使用的藥物黃芪、丹參、太子參、茯苓、澤瀉、益母草、生地、赤芍、山藥、枸杞等。現代中藥藥理學研究表明,黃芪、茯苓等可促進胰島素的分泌,增強周圍組織對胰島素的敏感性[7]。它們可以減輕DM患者早期腎小球的高濾過、高灌注,降低血糖,改善微循環、改善腎功能,消除或抑制機體中氧自由基及其衍生物對機體的損害,抑制腎系膜細胞增殖和細胞外基質積聚,抑制腎代償性肥大[8]。
DCP的中醫針灸治則為疏利膀胱氣機、溫補脾腎、益氣啟閉。針灸取穴以足少陰、厥陰經穴為主,輔以背俞穴及經外奇穴。通過膀胱俞、中極疏利膀胱氣機,而通小便;太溪為腎經原穴,取之益腎水而清其源;腎俞補益臟腑之氣,增強臟腑功能;脾俞以振奮脾腎之氣機;命門溫補脾腎,補中氣;三陰交疏通三陰的氣血,清利脾經的濕熱,運化水谷,制約水液,補益中氣,以激發經氣,從而改善腎、膀胱的供血供氧,使受損的神經功能得到恢復[9]。電針通過對穴位、經絡的持續穩定的脈沖電流的綜合刺激,可提高膀胱充盈初始感覺閾值,保持一定的低壓狀態,有蓄尿功能,增加膀胱最大容量,推遠初次尿意的出現時間,減少尿失禁的情況[10],使上尿路的功能不受損害,排尿障礙得到改善。
綜上所述,通過本研究可觀察到電針聯合中藥治療 DCP患者,可通過對患者的疾病進行針對性的辨證論治,達到對患病的機體滋腎養陰,陰陽并補。利氣機而通水道,補脾腎以助氣化,使人體的氣化得行,小便自通。實現實則清利,虛則溫陽益氣,升清降濁,補腎利尿,化氣利水。“腑以通為用”,維持膀胱順應性,保護腎功能,恢復自主排尿功能的正常生理狀態。
[1]雙衛兵,王東文.糖尿病膀胱研究進展[J].中華泌尿外科雜志,2006, 27(3):213-215.
[2]關子安,孫茂欣,關大順.現代糖尿病學[M].天津: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2000:383.
[3]鄭筱萸.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S].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02:156.
[4]龐春生,夏祖昌,郭維淮,等.中醫常見病診療標準[M].鄭州:河南醫科大學出版社,1998:49-50.
[5]鄧尚平.臨床糖尿病學[M].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2000:287.
[6]陸再英,鐘南山.內科學[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8:650.
[7]林蘭.中西醫結合糖尿病學[M].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1999:22-34.
[8]陳秋,夏永鵬.單味中藥治療糖尿病腎病研究述略[J].中醫藥學刊,2004, 22(1):103-105.
[9]袁鶴庭.針刺治療糖尿病周圍神經病變致手足麻木疼痛[J].中國針灸,2006,26(3):225-226.
[10]Zhao L, Wang SY. Treatment frequency and long-term efficacy observation on electric pudendal nerve stimulation for stress urinary incontinence[J]. J Acupunct Tuina Sci, 2013, 11(3):177-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