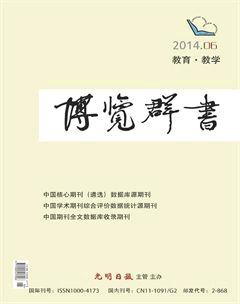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與受賄罪共犯的區別
單明敏
一、利用影響力受賄罪與受賄罪的概念
所謂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是指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或者其他與該國家工作人員關系密切的人,通過該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或者利用該國家工作人員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請托人財物或者收受請托人財物,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較重情節的行為。
所謂受賄罪,是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
二、利用影響力受賄罪與受賄罪共犯的區別
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立法旨在于彌補法律漏洞,懲處那些利用國家工作人員職權和地位收受賄賂的與國家工作人員關系密切的人。對于利用影響力受賄罪與受賄罪共犯的區分,可以以國家工作人員和關系人主觀上的故意的不同,分成以下兩種情況:
1.國家工作人員和關系人有共同受賄的故意
對于這種情形,國內學者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此時利用影響力受賄罪與受賄罪界分的基本原則是國家工作人員是否收受了財物。如果國家工作人員收受了財物,則關系人與國家工作人員構成受賄罪的共犯;如果國家工作人員沒有收受財物,那么即使國家工作人員明知關系人收受了請托人的財物,也不構成共同犯罪,只能對關系人以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定處,國家工作人員可以作紀律處分。有人認為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是行為人在國家工作人員不知情的情況下實施的行為,如果雙方通謀受賄,交易的對象不是“影響力”,而是國家工作人員的職權,應當以受賄罪定罪。
所以,上述兩種觀點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從共同犯罪的基本原理和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本質來看,都有許多不合理之處。第一種觀點與我國現行立法是一致的。從共同犯罪的基本原理來看,只要行為人主觀上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客觀上有共同的犯罪行為,那么即成立共同犯罪,而共同占有財物并非上述構成的一部分。刑法規定受賄罪并沒有要求行為人必須將賄賂據為己有,分則中“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包含為了第三者非法占有,且“行為人是為了本人非法占有還是為了第三者非法占有,對法益的侵犯程度并不產生影響”氣與控制刑法打擊面的意圖相比,不合理的添加共同占有財物的要件,可能會放縱犯罪,并且該觀點認為在國家工作人員收受了財物的情況下,一律以受賄罪共犯論處,這沒有考慮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成立的可能,過于武斷。
第二種觀點看到了利用影響力受賄罪與受賄罪的的本質聯系,但是卻不符合共同犯罪的構成和特點。其實,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的成立并不排斥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成立。“判斷某個行為是否構成某一犯罪應當看其是否符合該罪的構成要件,是否侵犯該罪保護的法益。” 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在侵害法益方面與受賄罪的區別在于后者是國家工作人員直接控制其職權行為,而前者是關系人通過其“影響力”間接控制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也就是說刑法處罰關系人的根據就在于其積極利用其“影響力”的行為為權錢交易提供了平臺,最終損害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公正性。那么判斷在關系人與國家工作人員合謀的情況下是否可能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應看關系人是否實施了積極利用了其“影響力”的行為。即使從受賄罪的角度看,財物與職務行為直接形成對價,但是從利用影響力
受賄罪的角度看,關系人實施“影響力”的行為客觀存在,其對國家工作人員決意實施職務作為或者不作為仍然具有原來本有的影響,無論在主觀上還是客觀上關系人索取或者收受請托人財物時依然完全或者很大程度上憑借這一點。筆者認為在國家工作人員與關系人有共同受賄故意的情形下,共同犯罪的性質應分情況討論。
第一種情況是關系人在共同犯罪中處于被動、次要的位置,沒有積極利用其“影響力”的,應以受賄罪共犯定處。所謂關系人積極利用其“影響力”可以比照上述第一種情形下國家工作人員不知道關系人利用影響力受賄時關系人的行為進行認定,具體來說比如關系人應積極與請托人聯系并索取或者收受賄賂、受賄故意由關系人首先提出等。總之在共同犯罪中,關系人應處于主動、主要的角色,其“影響力”的利用是國家工作人員實施職務作為或荇+作為的重要要原因(已經實施完畢的職務行為除外)。
第二種情況是關系人在共同犯罪中積極利用其“影響力”起主要作用的,其行為符合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構成要件,那么關系人與國家工作人員的共同犯罪行為同時觸犯了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和受賄罪。其中關系人成立受賄罪共犯無疑義。對于國家工作人員,雖然在普通的利用影響力受賄罪中國家工作人員也可能基于關系人的“影響力”而實施職務作為或者不作為,客觀行為與共同故意下其行為一樣,但是國家工作人員在明知關系人利用其影響力受賄情況下,依然決意實施職務作為或者不作為,為關系人犯罪提供條件,應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共犯;另一方面,即使國家工作人員不占有財物,在明知關系人受賄的情況下,亦具有權錢交易的認識和決意,應構成受賄罪。此種情形下共同犯罪性質的認定應以想象競合犯的原理和罪刑相適應原則為指導,按照從一重處罰的原則認定為受賄罪共犯,如果將關系人認定為受賄罪的從犯,導致對其處罰輕于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主犯時,則應該將關系人認定為利用影響力受賄罪。
2.國家工作人員和關系人沒有共同受賄的故意
這種情形下國家工作人員對關系人利用影響力索取或者收受請托人賄賂的行為一般情況下是不知情的,那么由于國家工作人員主觀上缺乏受賄的故意,不應以受賄罪論處,如果其違背職責構成瀆職類犯罪的,以相關罪名處罰,而關系人單獨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
實踐中還可能存在這種情況,即國家工作人員明知關系人利用其影響力索取或者收受賄賂,仍然實施了職務行為,為他人謀取了不正當利益,而關系人對此并不知情的。這種情形下,由于關系人不知情,其主觀上是利用影響力受賄的故意,即使國家工作人員明知其受賄,二者缺乏共同受賄的故意,因此,根據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對關系人只能以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定處。而國家工作人員在知道關系人利用其職務行為實施受賄犯罪時,仍然按照其要求實施職務行為,主觀上具有“錢權交易”的受賄故意,客觀上配合關系人實施了職務行為為他人謀取了不正當利益,同時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片面共犯與受賄罪,屬于想象競合犯,應擇-重以受賄罪論處。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與國家工作人員關系密切的人員收受請托人財物,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職權和地位,為請托人謀取不當利益的行為,既可能構成受賄罪的共犯,也可能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區分的關鍵在于國家工作人員與特定關系人之間是否存在共同的受賄故意和共同的受賄行為,即通謀。如果存在通謀,那么屬于受賄罪的共同犯罪;如果沒有通謀,只是特定關系人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地位和職權實施行為,那么該國家丁.作人員閃為沒有犯罪故意和犯罪行為而不構成犯罪,特定關系人不構成受賄罪的共犯,而應當以利用影響力受賄罪論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