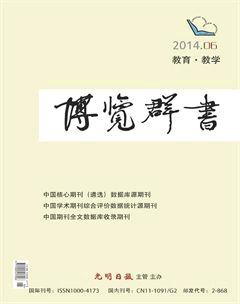對律師律師偽證罪立法局限性和程序局限性的分析
王微
“律師偽證罪”是刑法306條規定的“辯護人妨害作證罪”的俗稱。刑法306條第一款:“在刑事訴訟中,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偽造證據,幫助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威脅、引誘證人違背事實改變證言或者作偽證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律師律師偽證罪立法上的局限性
1.該法條規定的犯罪主體定位不準。該法條規定的犯罪主體是特定主體,即辯護人、訴訟代理人。該法條規定的犯罪主體定位不準。第一,在刑事訴訟中擔任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的不具有律師身份的人不應該成為該法條的犯罪主體。擔任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的不具有律師身份的人不但在刑事訴訟中的權力小于擔任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的律師,而且在法律理論知識水平和實踐經驗上的整體水平比擔任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的律師差。刑法第三百零六條將兩個處于不同專業水平的群體用同樣的標準進行規范,這實際上是不公平的。第二、如果說律師在刑事辯護中作偽證或者毀滅偽造證據具有社會危害性的話,那么檢察員、審判員、書記員提供虛假證明或毀滅、偽造證據危害性更大,是否也專門給檢察員、審判員、書記員定一個罪呢?在法庭上,抗辯雙方在地位上是平等的,既然特意單獨對辯方規定了偽證行為構成犯罪,為公平起見或是未防止司法系統內部人員偽造證據更應該單獨規定相應的罪名。第三,從比較法的角度來看,世界各國的法律并沒有對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偽造證據、幫助毀滅偽造證據、妨害作證的行為單獨定罪。因此,筆者認為,該法條規定的犯罪主體定位不準。
2.該法條規定的危害行為中的“威脅”、“引誘”含義模糊。 該法條規定的危害行為中的第三種行為是威脅、引誘證人違背事實改變證言或者作偽證,其中的“威脅”、“引誘”兩詞的具體含義并不明確。最高人民法院也未對此做出具體的司法解釋。司法實踐部門對此的理解不統一,在執法時容易出現隨意性。由于第三百零六條規定的“引誘證人作偽證”容易被隨意認定,造成律師的辯護風險太大,以致全國普遍存在律師不愿承擔刑事案件辯護工作的情況。
3.該法條未將一般的違反職業道德行為和犯罪行為劃出明確的界限。律師法第四十五條既規定了一般的違反職業道德行為,也指出了有的違反職業道德的行為可能構成犯罪。刑法第三百零六條將律師毀滅偽造證據、幫助毀滅偽造證據、妨害作證的行為一律規定為犯罪,也就是將律師毀滅偽造證據、幫助毀滅偽造證據、妨害作證的行為界定為不是一般的違反職業道德行為。筆者認為,這個做法不太妥當,負面影響比較大。
4.該罪的客觀方面的描述有漏洞。有根據《刑法》第 306 條可以分析出律師偽證罪的客觀方面表現:即在刑事訴訟中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實施以下三種情況之一:①毀滅偽造證據;②幫助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③威脅、引誘的方式,違背事實改變證言或者作偽證。由于法條本省的精簡和高度概括,所以在司法實踐中要適用律師偽證罪,解釋也就顯得尤為重要。對于刑法第 3 0 6 條的犯罪構成,主要應在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嚴格限定。第一;當事人的供述是否屬于物證。筆者認為,毀滅、偽造證據以及幫助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的行為對象應該僅限于證據。根據證據的屬性,其中對于毀滅、偽造的證據又只能是屬于有物質載體的證據,對于沒有物質載體的證據談不上毀滅和偽造 ,所以對于當事人的供述而言由于沒有具體的物質載體,當事人的供述本身就不屬于物證,也就談不上毀滅和偽造。所以對于律師引導當事人改變證言的行為應該不屬于毀滅偽造證據。
律師偽證罪罪狀的問題之一,是對罪狀的描述以及該罪客觀方面所具有的寬泛的涵蓋性。我們可以根據“ 兩高”的《罪名意見》 和《罪名規定》,將本罪分解之會發現,律師偽證罪實際上規定了三個子罪名:毀滅證據罪、偽造證據罪和妨害作證罪。律師偽證罪在客觀方面的行為又可分為三個方面。不難看出,只要將條文文字稍做擴大解釋,則該條所描述的行為幾乎囊括了刑事訴訟過程中的每個環節與任一階段的逐個細節。換句話說,在現今的法治環境下, 由于《刑法》 第 3 0 6 條的存在, 對于辨護律師可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真是易如反掌。本罪罪狀的問題之二, 是罪狀描述的模糊性律師偽證罪客觀方面的前兩種行為分別是毀滅和偽造證據,這兩種行為在司法實踐中較容易認定,關鍵是第三種行為,即威脅、引誘證人違背事實改變證言或作偽證的情況不容易認定。而且,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證據、偽造證據、 妨害作證罪罪狀描述與聯合國大會1990 年9月7日通過的《關于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 也不一致,難以和國際接軌。
二、律師偽證罪程序上的局限性
律師偽證罪立案啟動制度,是指在刑事訴訟中對律師偽證罪案件啟動刑事立案程序的各種相關因素和組織的結構方式,及各個相關因素和組織的相互作用方式和過程的訴訟制度。就其指向的對象,是指我國現行的律師偽證罪案件刑事立案運作方面的制度總和。它是法院謹慎審理該罪的一個重要的前提過程,它的本意是保護辯護人的合法權益,不讓其受到無辜冤屈的現實需要,但在實踐中它存在的一定的缺陷并會相應產生一些不良的影響。
1.啟動該類案件的主體享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是該制度存在的最大的隱患。這類案件的啟動權屬于公安機關,但是,具體每個個案的啟動權則是公安機關的負責人以及由負責人領導或授權的辦案人員。這些辦案人員都享有較大自由裁量權,具體案件中不同辦案人員可能因為個人的情操、道德、私人情緒、個人好惡、或專業水平等來裁量是否該對某一律師啟動該程序,故而影響案件立案啟動的公正性和正當性,使一些律師含冤受屈。
2.本土性色彩濃,這有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當今國際上很多國家都沒有這個罪名,而只有我國以及少數的其他國家有該罪名。它是在我國自己的法律土壤上生長出的一種罪名,有自己國家深厚的現實和社會基礎。在國外,無論是大陸法系國家,還是普通法系國家,都有關于律師刑事責任豁免制度相關規定。但我國刑法卻不但沒有這方面的規定而且還規定了此罪名。這無疑是懸在律師頭上一把利劍,使律師不敢自由的行使自己的辯護權,大膽的去與刑事公訴制度進行抗辯,維護犯罪嫌疑人的權利,這與我國的現實情況與司法環境有很大的關系。二是國際社會很多國家都沒有該罪獨立的立案程序。但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該罪的立案程序,原先是它是我國從蘇聯移植過來的,但經過多年的不斷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完善它已經成為我國獨具中國特色的一項司法制度。
3.立案渠道比較單一,是指在司法實踐過程中,公安機關接收此類案件通常都是來自于另案的訴訟參與人舉報或是公安機關自行發現,但是這種案件接收來源就會產生這兩方面的負面思考:一是另案訴訟參與人舉報一般是考慮到自己的利益(為了立功、跟律師產生一些矛盾或經濟上的溝通不善等);二是公安機關自行發現而進行立案偵查主要是為了保證正在進行的別的案件的訴訟程序能夠順利進行。公安機關考慮到律師偽證罪案件與別的案件的牽連關系和對之訴訟順利進行所產生的不利影響,一般會很快受理此類案件,而且快速啟動該類案件的訴訟程序。
4.這個罪名的立案啟動幾乎形成了這樣一個基本模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認罪→律師介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翻供→律師妨害作證(或偽造證據)→立案啟動。實踐中是否存在職業報復這樣的現象不好說,但該罪名的適用過程卻具有驚人的相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