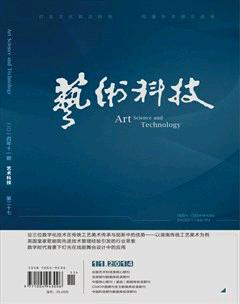《蕙風詞話》與《人間詞話》的創作論比較
李甜
摘 要:《蕙風詞話》與《人間詞話》有“雙璧”之稱,而這兩部詞話雖所處時代相近,其創作風格卻十分迥異,一部作為古代詞學評論的集大成者,一部開西方文學批評的先河,本文試比較二者在創作論方面的不同,從二者創作主體對創作的作用的不同、創作要求的標準的不同角度,看詞學觀對其創作論的影響,總結這兩本書詞學創作論共同認識及各自的疏漏之處。
關鍵詞:《蕙風詞話》;《人間詞話》;創作論
創作論的概念十分含糊,他大致可以與詞人本人的詞學觀相輔相成,但在實際的創作中,詞人卻可能違背于自己的詞學創作觀,與自己崇尚的詞學標準相悖。詞學創作論是從詞作產生之時開始發源,并且指導詞人的創作內容與表達風格,對文學創作提出了細致具體的要求。
1 從創作的主體看
創作的主體,實質也是抓住創作的起源。詞人對創作靈感的尋求是不遺余力的,所謂“情發于中而行于言”,而靈感、性靈之說又是十分玄妙的,對靈感的解釋只好依托于外物,與學力、與景物生發、與人生閱歷等相聯系,這樣也為求學之人指了一條明路,似乎通過多讀書、多感發于外物就可成就優秀的文章,實際上這樣的解讀方式是對“靈感”本身的消解。靈感既不可抹去他本身具有的神性,也不可與現世割裂的產物,是歷史與環境作用的結果。
而究竟創作起源于何處,《蕙風詞話》和《人間詞話》給出了不同的闡釋:
《蕙風詞話》:“詞中求詞,不如詞外求詞。詞外求詞之道,一曰多讀書,二曰謹避俗。俗者,詞之賊也。”又有:“填詞要天資,要學力。平日之閱歷,目前之境界,亦與有關系。無詞境,即無詞心。矯揉而強為之,非合作也。境之窮達,天也,無可如何者;雅俗,人也,可擇而處者也。”
這里提到的詞外求詞,注重作詞之外的世界,其方法為多讀書和謹避俗。多讀書終有天可達到學力與境界的融合,謹避俗即是人有力區別雅俗,擇而處之。同時況周頤又十分強調“吾心”,“吾心”即“詞心”,從心中流淌而出的真意是受到“風雨”、“江山”的感發,感到所謂“萬不得已者”,即人與景物的關系常有一種相磨礪,自然之景所呈現的必然的樣子,這種自然的天性或順己志,或逆己志,如錢鐘書在《談藝錄中》所說,“物各有性,順其性而恰有當于吾心;違其性而強以就吾心;其性有必不可逆,乃折吾心以應物。一藝之成,三者俱焉。”而況周頤也指出了“吾心”來自書卷,正如《滄浪詩話》“別才非學而必多讀書以極其至。”
而在《人間詞話》中:“詞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是后主為人君所短處,以及為詞人所長處。”“客觀之詩人,不可不多閱世。閱世愈深,則材料愈豐富,愈變化,《水滸傳》《紅樓夢》之作者是也。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
此處,王國維的觀點認為,寫詞要有“赤子之心”。而李后主“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的環境中,孕育了憂郁、細膩、純真的情感,即所謂“赤子之心”。而又將宋道君皇帝和李后主對比之后,力推李后主是有推己及人的擔當之心的人。而李后主的成就之高,不僅僅在于他的情感是承擔著天下的愁苦,更在于他自身的悲劇性,他自身經歷與詞學創作所給人的動人力量,即所謂“以血書之”。而王國維對詞人的要求也是具體的,認為如果是客觀描摹的詩人,要多閱世。主觀的詩人要保持真性情,不可多閱世。閱世包括讀書與閱歷,而詞作為主觀抒情的表達,閱世淺反而見真性情。
此二人的共同點是都發現了“詞心”的存在,也都注意到外在境界與自身的關系。王國維比況周頤深入的地方在于他能夠“發明本心”,將“吾心”降落于情真意切之上,而況周頤還是將“詞心”玄妙化了,在達到的途徑上,繼續提出要多讀書、多感于外物才能練達文章。況周頤認為“多讀書、謹避俗”是詞境界高的必要途徑,而王國維則認為性情真,文章方有內涵,我們需鍛煉的并非一概而論的“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而是注重內在性情的培養,保持真摯的情感,抒寫真意,便可成就好文章。
2 從創作的要求看
創作論觀點的核心便是如何創作才能寫出好的文章,而詞學觀的實質也是對至高藝術的追求。
《蕙風詞話》的主要詞學觀點是“拙、重、大”。首先與“拙”相對的是“巧”,文章工巧便是強調對文辭形式的雕琢,而況周頤推崇“拙”,實質便是推崇自然不雕飾的文字,認為“詞忌做,尤忌做得太過,巧不如拙,尖不如禿。”。其次是對于“重”的闡釋,認為“填詞先求凝重。凝重中有神韻,去成就不遠矣。所謂神韻,即事外遠致也。即神韻未佳而過存之,其足為疵病者亦僅,蓋氣格較勝矣。若從輕倩入手,至於有神韻,亦自成就,特降於出自凝重者一格。若并無神韻而過存之,則不為疵病者亦僅矣。或中年以後,讀書多,學力日進,所作漸近凝重,猶不免時露輕倩本色,則凡輕倩處,即是傷格處,即為疵病矣。天分聰明人最宜學凝重一路,卻最易趨輕倩一路。苦於不自知,又無師友指導之耳。”;對所謂“大”,《花間集》歐陽炯《浣溪沙》云:“蘭麝細香聞喘息。綺羅纖縷見肌膚。此時還恨薄情無。”自有艷詞以來,殆莫艷于此矣。半塘僧騖曰:“奚翅艷而已,直是大且重。”茍無《花間》詞筆,孰敢為斯語者。”這里可以看出,況周頤對“大”的闡釋為“大且重”、“大氣真力”,以《花間集》論大,一反歐陽炯對《花間集》“輕倩”的定位,其質直情真,不同于矯揉造作的呻吟之詞,感情深厚是其背后“大且重”的支撐力量。
我們可以看出《蕙風詞話》所推崇“拙、重、大”的文學氣質,是經歷一番深沉沉郁的歷練后,脫穎而出,表現為淳樸自然又不失厚重感的。
《人間詞話》對詞的高下之判雖然沒有提出具體的理論,但他在論詞的高下時常用的詞有境界、氣質、品格、神韻等詞,如有條目云“詞之雅正,在神不在貌。永叔少游雖作艷語,終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淑女與娼妓之別。”
又有“言氣質、言神韻,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氣質、神韻,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隨之矣。”這些詞看似是相近又不可區分的,似乎覺得王國維對于這些判別詞本身也是含糊不確切的,境界與氣質和神韻的區別在哪里?在我看來,王國維的境界之說在于物與我的融合,這不同于氣質與神韻的完全發乎于中,如同靈感一樣是玄虛的,好的境界便是自然之景與人真摯情感的結合,而非內在情感的宣泄,也不僅僅是文字上的清麗曉暢。總結來說,王國維對詞作創作的要求便是情真。《蕙風詞話》言:“真字是詞骨,情真,景真,所作必佳,且易脫稿。”所表達的與王國維此處對境界的看法是一致的。
放在當時所處的時代背景來看,晚清四大家推崇吳文英,將隱晦幽深的詞放在詞學的高位上,這在文學史是一個短暫而又偏激的時期,而王國維力求推翻這種評價標準,不談吳文英詞的優劣,轉而談詞的“隔與不隔”實際上是間接地糾正了詞壇的風氣,重新建立一種文學批評的視角。從這個角度看,王國維作為當時的新派,是有積極意義的,雖然他的《人間詞話》中有許多不嚴密之處,但我們能從他突破框架的灑脫中尋求王國維《人間詞話》的真意,這也是我們對于古人之理解與同情之處了。
參考文獻:
[1] 況周頤.蕙風詞話[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2] 王國維.人間詞話[M].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10.
[3] 錢鐘書.談藝錄[M].三聯書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