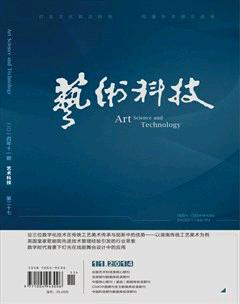亞洲內部構建藝術共識的未來
吳思雨
1 亞洲:藝術市場和國際交流
討論的大前提是從中國藝術開始的過熱的藝術市場保持距離。藝術市場邏輯對韓國、日本、印度、印尼也同樣造成了廣泛沖擊。在20世紀80年代晚期,印尼藝術是親切的批評精神與自我文化傳統再利用的亞洲新藝術誕生的預言者,但是藝術市場同樣影響了印尼藝術,導致了拍賣目錄中膚淺平凡作品的洪流。我們應該承認,藝術品銷售預設了廣泛的普及性以及作為投資的欲望,但是我們可以將腳踏實地的甚至在市場低潮期提升自己的方法和哲學的藝術家,同那些應市場要求反復使用固定風格和主題,或是在大財團基金的資助下制作更大更精巧的作品的藝術家區分出來。特別是在2008年秋,由經濟危機帶來的藝術泡沫破滅后,我們可以以更好的標準鑒定那些藝術家,而不是用那些被投資者抬高的天價。我們必須知道,亞洲藝術熱實際上只是成就了(或者損害了)極少數的亞洲藝術家。
然而,亞洲藝術的國際熱并不僅僅存在于容易被經濟情況所影響的市場上,同時也存在于中國藝術家在國際藝術世界上,獲得了任何其他亞洲國家的藝術家都無法達到的高評價。也正是那些中國藝術家們引發了亞洲藝術家市場在世界上的過熱。由于中國強大的經濟實力,數量眾多的龐大的建筑項目被啟動,各地的美術館被認為“像星巴克一樣迅速增長”。當前的中國藝術世界是這樣的:在北京有許多大型畫廊,被世界各地的策展人和藝術經理頻頻拜訪。藝術家大型的工作室有許多助手,藝術家村有成千上萬的住民,這樣的情況,對于那些了解過去的亞洲當代藝術情況——藝術家賣不出作品,無法獲得主流認同,沒有表現自由,沒有任何媒介或大型畫廊、策展人的支持,沒有登上國際舞臺的機會等等——這些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這些亞洲藝術家已經成名的例子和在國際上頻繁曝光的名譽,讓我們思考,亞洲當代藝術不再等待“國際認同”,甚至看起來好像已經是作為贏家在領導國際藝術市場。這里并不是質疑他們的藝術原創性與潛能,現在需要質疑的是他們作品和表現的目標是否只是針對策展人和收藏家等精英階級?他們的活動對其他觀眾來說是否足夠開放?他們的創作和表現的動機是否自發的來自于個體內心的精神和哲學,而不是跟隨大眾潮流或者取悅主辦方?最重要的問題是,他們的作品與活動能否在歷史無情的淘汰中存活下來。亞洲藝術家已經在過去十年間全世界范圍內廣泛參加雙年展、大型美術館和商業畫廊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我們聚焦于本地性的特質同樣可能會在當代藝術家情形的理解上被誤導。所以,繞開那些已經成名的藝術家去討論亞洲當代藝術是不合適的。
然而,我們的舉措中沒有包括那些已經頻繁的從1980年以來參加國際展,而作品在首次登場后卻沒有進步的藝術家。在國際藝術明星中選擇誰并不重要,我們應該在“誰是國內藝術家,誰是國外藝術家”區別的固定化與絕對化上更為小心,因為我們不能輕易地接受一個慣例的看法,認為國際藝術家比國內藝術家更為出色,或者僅僅欣賞那些在國際舞臺上出現的藝術,忽略本地藝術實踐的價值。這就是我們沒有將藝術家按工作區域在展覽中進行區分的原因。
2 亞洲問題的提出
在今天的藝術世界,或許是一個新話題,但討論亞洲的美學與文化價值卻可以追溯到100年前。百年前,世紀交替的日本,以岡倉天心(岡倉天心死于1913年,迄今剛過100年)為首的藝術家與美學家,極力捍衛亞洲的文化價值,認為亞洲文化推崇的“阿拉伯的騎士道,波斯的詩歌,中國的倫理,印度的思想”,文明形態正處于西方機械文明的反制。
近年來,中國周邊的東南亞各國,隨著經濟與社會政治的變化。當代藝術創作也日益活躍。亞洲格局的變化能否在亞洲內部構建一個討論亞洲藝術問題的新平臺,不再從西方的視角來觀察亞洲藝術格局的新變化。亞洲的美術館使命一直慣例邏輯性地推導出的主題所束縛。例如,“溝通”、“交流”。我們所說的亞洲內部構建共識的未來,這里強調一下內部的問題,“內部”的問題起源于對福岡亞洲美術館,這個全世界僅有的亞洲現當代藝術館的現有程序和制度的重新審視。在展示亞洲現當代藝術、從事藝術家交流項目的這幾年中,我們逐漸意識到,引起本地人對亞洲各國藝術家的興趣不是件容易事,促成外國藝術家和本地人之間生動、密切的交流和合作就更難了,這些藝術家來自另外一個世界,對本地人而言完全是陌生的。內部與外部、臨近與遙遠、直接體驗或者被大眾媒介傳達、人造的或者自然的多種的情形并存的情況,影響了選考委員會和策展團隊。
還要討論的一個問題,就是重新回顧我們已經非常熟悉的亞洲現代藝術的再現。那些在國際上(包括西方世界和近幾年的東亞展覽)已經成名的亞洲藝術家從1990年以來已經習慣于將社會事件轉換為他們的主題,在亞洲社會變遷帶來的城市化和消費文化的影響中呈現政治性與性別問題。將本地材料與地方性主題同化,他們的作品對外國人呈現出“亞洲的”感覺。同時,身份問題被如此多的亞洲藝術家使用,已經超越了亞洲的框架。在后殖民與后冷戰的全世界結構下,這是一個顯著的信號。然而,在他們被迅速的認識并頻繁曝光于西方和日本城市中時,他們可能生產出關于“什么是亞洲現代藝術”的固定模式。相反作為代替的,一部分藝術家寧愿在他們的作品中使用流行媒介和元素,這些媒介和元素似乎并不屬于亞洲本土,但是來自時尚、設計、漫畫、動畫、網絡等等文化,他們因此曾經作為亞洲藝術家武器與回家的身份問題中解放出來。
3 亞洲藝術共識新規則
在文化意義分享的過程中,話語的差異使得以歐美為代表的西方和以亞洲為代表的東方長期以來發展并不平衡,亞洲本土意識普遍缺乏,這構成了此次論壇的背景。在去年的一次藝術論壇上,“亞洲意識與亞洲經驗”作為本次論壇的議題,也是廣東美術館館長羅一平演講的主題。如果對這一話題做進一步追問,首先要回答的是何為“亞洲意識與亞洲經驗”。羅一平指出:這一追問涉及兩個基本問題,即什么是亞洲?什么是亞洲藝術?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關系到亞洲各國策展人,如何認識亞洲的藝術現狀以及發展的趨勢,以及如何通過展覽策劃呈現亞洲藝術自身的特點,從而推動亞洲藝術的發展。從近幾十年亞洲各國藝術展覽的呈現來看,清晰地說明一個事實,沒有一個感召力的概念去思考亞洲問題,思考亞洲藝術的問題,在西方作為“他者”仍然支配亞洲各國藝術發展這一點上,亞洲反而成了一個共同體。羅一平指出:如果從后殖民的語境來考察亞洲美術的話,就會發現亞洲的策展人在西方化與抵制西方化的沖突和矛盾中所付出的巨大努力,而正是這種努力從整體上影響了亞洲藝術的發展。舉辦此論壇,正是廣東美術館看到契機之外發展的共性問題。這是各國策展人在向自己發問,也是廣東美術館在向自己挑戰。對“亞洲視覺”的討論,凝聚著策展人對于亞洲思想之源的思辨與創新。美國現代藝術博物館國際部主任李文森教授用大量的圖片和文字來說明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在展示、收藏、分類上存在的特殊現象,他提示我們:日本和中國現代藝術的加入,在某種稃度上改變了西方博物館關于國際現代主義和全球當代藝術的評價體系。新加坡國立美術館策展及典藏部主任劉思偉先生更是從新加坡美術館的收藏,提出為東南亞藝術培養區域視角。
從“亞洲人看亞洲”到“歐美人看亞洲”,再到“世界看亞洲”,是此次論壇的思想路徑,也首次呈現出一個完整的亞洲看世界的視角。作為一種呼應,中國美術館的展覽策劃部主任張晴介紹了中國美術館近些年在舉辦帶有國家美術作品形象展覽時,如何將其和學術性的展覽思路融合在一起。他指出:當今美術館面對的世界是“多維度”、“多邊界”、“多規模”的藝術格局,培育本土文化突出性的同時,也承擔著當代性的使命。這實際上表明了中國研究者對亞洲藝術的學術態度,也在用自身的方弍,回應一個關鍵問題,即在超越二元對立之后,如何擁有達致自我與他者的自由、和諧溝通的路徑?
4 亞洲的立場
憑借“亞洲美術策展人論壇”開闊的國際視野和強大的策展資源,主辦方還同期舉辦“回到亞洲?亞歐美術策展案例展”。作為論壇的有機組成部分,案例展將與會嘉賓近年來心中關于亞洲問題最好的展覽“空運”到廣東美術館將相關的提案、文本、現場記錄以及與藝術家往來的書信進行案例文獻呈現。案例展立足亞洲本土策展人或美術機構的策展實踐,又涵蓋歐美策展人和機構策劃涉及“亞洲意識與亞洲經驗”的典型案例。案例展策展團隊釆用展場還原旳方式,添加工作計劃/展覽日志(Exhibition Journal)、布展手稿草圖/平面圖/3D效果圖、展覽邀請函/海報/視覺、畫冊/導覽冊/文獻集等相關出版物、公共教育項目、新聞報道及剪報、展覽錄像、展覽評估報告、布展工作現場圖片/展覽現場圖片、觀眾留言簿等等細節文件,以期復原工作現場和流程,使得展覽生動立體地再現,力圖揭示案例背后的工作方式與態度。這為“亞洲美術策展人論壇”提亮了色彩,也使觀眾對亞洲藝術與當下策展形勢獲得一個全景式的思想體認。新加坡國立美術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法國賽爾努奇博物館、韓國首爾市立美術館、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東埔寨國立博物館、大阪日本國立美術館、印度國立現代藝術館、中國美術館、何香凝美術館、香港藝術中心、關渡美術館等全球多家藝術機構積極回應。MoMA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的“東京1955—1970:新先鋒派”、法國賽爾努奇博物館的“越南印象——從紅河到湄公河”、韓國首爾美術館的“桃源夢”等令人印象深刻。
所以,在這樣一個社會中,即使我們并非被迫處于被隔離的單位,我們已經自我隔絕,然后每個世界都在分開與隔離中的自我滿足。即使我們注意到了,我們和外部世界也沒有那么多交流的需要。
一系列的藝術活動,這些都反映了藝術家對社會的興趣和愿意融入現實生活的愿望,也就是他們愿意參與生活、反映生活的態度,這種態度源于20世紀90年代出現于亞洲藝術界的現實主義。但這里所說的現實主義并非狹義的字面意義的現實主義即嚴肅的形式或對原物的臨摹,我們所說的現實主義不僅僅是,或者完全不是這種意義。因為這段時期亞洲藝術的主流不是現實主義的風格,而是一種現實主義的態度,我將其定義為“現實主義作為一種態度”。
當亞洲藝術變為投資對象和富人的炫耀物,展覽淪為娛樂工業與市民參加與教育的美麗借口,藝術如何保持“新鮮”,保持“生機”?如何“延續,繼續,展開”他者、歷史和自然?答案存在于藝術家、其他個人與群體創造的作品中,能夠提供給人類失去的事物以存在的意義,可以走向明天,需要在另一個延伸自我的希望與智慧。
亞洲藝術的明天在哪里?
參考文獻:
[1] 收藏中國當代藝術的遠大前程[J].藝術新聞,2014.
[2] 黃宓.亞洲內部的亞洲討論:思考福岡亞洲美術館與“亞
洲藝術三年展”的亞洲觀[D].中國美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