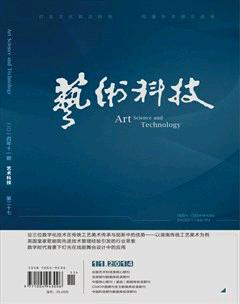魯迅與葉靈鳳的恩怨糾葛
郭伶俐
摘 要:葉靈鳳與魯迅的斗爭曾轟動一時,從此葉靈鳳的負面影響紛至沓來,甚至被戴上“漢奸文人”的帽子,以致人們會容易忽略他對文學界也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第一次全國木刻聯(lián)合展覽會的舉辦、蕭紅骨灰的遷葬,沒有他便不可能成功,而晚年的他對魯迅也是充滿崇敬,并在多部散文中表以敬意。
關鍵詞:魯迅;葉靈鳳;木刻版畫
1928年5月,《戈壁》半月刊第二期上發(fā)表了一幅名為《魯迅》的諷刺漫畫,畫中的大酒缸上伸出幾只揮舞著炸彈、小說集、狼牙棒等武器的手,里面注著小說舊聞抄、有閑階級、權威、吶喊等文字,并標注:“魯迅,陰陽臉的老人,掛著他已往的戰(zhàn)績,躲在酒缸的后面,揮著他‘藝術的武器,在抵御著紛然而來的外侮。”是誰敢這么明目張膽地諷刺魯迅?那么魯迅又是怎樣回應的呢?1928年8月10日,魯迅在《革命咖啡館》中回敬此人:“革命文學家,要年青貌美,齒白唇紅,如潘漢年葉靈鳳輩,這才是天生的文豪……”并于8月10日同一天寫了《文壇的掌故》,語氣更是冷嘲加熱諷。沒錯,該漫畫的作者就是葉靈鳳。
葉靈鳳(1905—1975)江蘇南京人,1925年加入創(chuàng)造社,與潘漢年、周全平等被稱為“創(chuàng)造社小伙計”,主編過《洪水》半月刊、《幻洲》《戈壁》《現(xiàn)代小說》,1929年創(chuàng)造社被封曾被捕,1937年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隨《救亡日報》到廣州,1938年廣州失守后到香港直到1975年病逝。
可憐葉靈鳳從此便被戴上了“齒白唇紅”的帽子,并成了他一生的招牌。新中國成立后出版的《魯迅全集》在《文壇的掌故》書信體的雜文卷末注釋里寫道:“葉靈鳳,當時曾投機加入創(chuàng)造社,不久即轉(zhuǎn)向國民黨方面去,抗日時期成為漢奸文人。”“漢奸文人”這頂更為沉重的帽子就這樣硬生生地扣在葉靈鳳頭上好幾十年。雖然在1981年人民文學版的《魯迅全集》第4卷《三閑集·文壇的掌故》中已沒有了這段話,但此時的他也已故去好幾年了。
1929年11月,葉靈鳳在自傳體小說《窮愁的自傳》中寫道主人公魏日青“照著老例,起身后我便將十二枚銅元從舊貨攤上買來的一冊《吶喊》撕下三面到露臺上去大便”。魯迅早就反感創(chuàng)造社的那些人,自然不甘示弱,1931年,他在《上海文藝之一瞥》(《二心集》)中說:“在現(xiàn)在,新的流氓畫家出現(xiàn)了葉靈鳳先生,葉先生的畫是從英國的琵亞詞侶剝來的,琵亞詞侶是‘為藝術的藝術派,他的畫極受日本的‘浮世繪的影響。”“還有最徹底的革命文學家葉靈鳳先生,他描寫革命家,徹底到每次上茅廁時候都用我的《吶喊》去揩屁股,現(xiàn)在卻竟會莫名其妙地跟在所謂民族主義文學家屁股后面了。”1934年11月14日,《答<戲>周刊編者信》:“但我記得《戲》周刊上已曾發(fā)表過曾今可、葉靈鳳兩位先生的文章;葉先生還畫了一幅阿Q像,好像我那一本《吶喊》還沒有在上茅廁時候用盡,倘不是多年便秘,那一定是又買了一本新的了。”各種冷嘲熱諷。
偏偏二人“冤家路窄”有著共同的愛好——版畫。魯迅于1928年創(chuàng)辦《朝花》期刊,把木刻版畫漸漸引向大眾,他編輯并出版《近代木刻選集》《比亞茲萊畫選》《蕗谷虹兒畫選》《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集》等畫集11冊。而美術出身的葉靈鳳也很早就很喜歡比亞茲萊的木刻版畫,他模仿比亞茲萊并把蕗谷虹兒的風格結合在一起形成“葉靈鳳式”的畫風。魯迅對此非常反感,他把葉靈鳳的模仿斥之為“生吞活剝”,說他是“新的流氓畫家”。
1928年7月,《<奔流>編校后記(二)》:“可惜有些‘藝術家,先前生吞‘琵亞詞侶,活剝蕗谷虹兒……”1931年7月,《上海文藝之一瞥》:“在現(xiàn)在,新的流氓畫家又出了葉靈鳳先生,葉先生的畫是從英國畢亞茲萊剝來的……”1934年10月,《奇怪(三)》:“原來‘中國第一流作家的玩著先前活剝‘琵亞詞侶,今年生吞麥綏萊勒的小玩藝……”他在《為了忘卻的紀念》中說編選蕗谷虹兒的畫就是為了“掃蕩上海灘上的‘藝術家,即戳穿葉靈鳳這紙老虎而印的。”
但葉靈鳳對木刻也有自己的見解,他曾寫過不少關于木刻版畫的評論文字。例如,《序珂勒惠支畫冊》《木刻論輯》《評<英國版畫集>》《<光明的追求>序》等,足見他還是有著一定的藝術功底的。雖然他沒有魯迅那么深的造詣,但不得不承認他對木刻藝術的發(fā)展也有著突出的貢獻,有些貢獻甚至連魯迅也是做不到的。1935年1月1日,全國木刻聯(lián)合展覽會在北平正式開幕,共展出七天,觀眾共達3000余人次,超過了任何美術展覽會的觀眾人數(shù),而倘若沒有葉靈鳳這次展覽會不可能成功。據(jù)展覽會籌辦者唐珂的《第一次全國木刻聯(lián)合展覽會紀事》所說,由于資金困難及政府阻撓,展覽會困難重重,魯迅的支持也不能解決所有問題,無奈之下唐珂等人便找到了葉靈鳳。葉靈鳳的姐夫是當時控制上海文化事務的教育局局長潘公展的手下,關系一疏通,展覽會就辦成了。而第一次全國木刻聯(lián)合展覽會的成功舉辦,對中國新興木刻運動的發(fā)展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這一點,葉靈鳳算是功不可沒。
1933年夏,上海良友圖書公司通過趙家璧的聯(lián)系從葉靈鳳手中借到原版書,翻印了比利時畫家麥綏萊勒的四種木刻連環(huán)圖畫集,魯迅與葉靈鳳分別為《一個人的受難》和《光明的追求》寫了序。當年得以翻印出這四種木刻連環(huán)畫集,與葉靈鳳大力貢獻出原版書是分不開的,后來魯迅收到翻印的圖畫樣書時,也對之大加稱贊。
葉靈鳳自1938年起就一直居住在香港直到病逝,晚年的他很低調(diào),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書是《晚晴雜記》(1970),此后直至1975年11月23日逝世的整整五年間,由于體弱又有眼疾,寫作幾乎一片空白。后學者發(fā)現(xiàn)他去世前一年半為1974年4月創(chuàng)刊的香港《海洋文藝》寫過專欄,并在第一卷第一期發(fā)表了《大陸新村和魯迅故居》和《景云里》,專欄冠以“記憶的花束”之名。他在這個新專欄開首兩篇都是寫魯迅,語言平實,透過字里行間能感受得到他對魯迅的尊敬。
據(jù)羅孚回憶:“當六七十年代朋友們有時和葉靈鳳談起他這些往事時,他總是微笑,不多作解釋,只是說,我已經(jīng)去過魯迅墓前,默默地表示過我的心意了”。葉靈鳳到上海拜謁魯迅墓是在1957年,并參觀了魯迅故居、魯迅紀念館和內(nèi)山書店的舊址,此前他曾在《獻給魯迅》中曾說,他在內(nèi)山書店數(shù)次見過魯迅,只是沒有交談過。晚年的他說:“我一向就喜歡比亞斯萊的畫。當我還是美術學校學生的時候,我就愛上了他的畫。不僅愛好,而且還動手模仿起來,畫過許多比亞斯萊風的裝飾畫和插畫。為了這事,我曾一再挨過魯迅的罵,至今翻開《三閑集》《二心集》等書,還不免使我臉紅。但是三十年來,我對于比亞斯萊的愛好,仍未改變,不過我自己卻早已擱筆不畫了。”他晚年的隨筆如《關于內(nèi)山完造》《果戈理的死魂靈》《愛書家謝澹如》《魯迅捐傣刊印百喻經(jīng)》《一個第三種人的下落》《敬隱漁與羅曼·羅蘭的一封信》等都有涉及魯迅。
葉靈鳳一向是熱愛祖國的,雖被戴上“漢奸文人”的帽子好幾十年,但他在香港為保存祖國的文化遺產(chǎn)貢獻過不少力量。五十年代蕭紅骨灰遷葬廣州,他親自護送,更是傳為文壇佳話。香港淪陷前夕大部分文人都撤至內(nèi)地,而戴望舒與葉靈鳳卻滯留香港,后來戴望舒遭日軍逮捕,也是經(jīng)葉靈鳳保釋出獄并為他提供住處。他早年雖與魯迅有些糾葛并一度被誤解,但晚年那些回憶文章卻感情真摯,確實難能可貴。
參考文獻:
[1] 強英良.在魯迅與葉靈鳳之間[J].魯迅研究月刊,1992(6).
[2] 陳子善.葉靈鳳的“記憶的花束”[J].博覽群書,2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