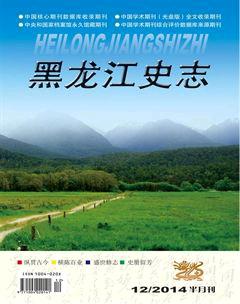人與自然的完善和發展經歷三個階段: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

[摘 要]唯物辯證法把物質世界的聯系和發展概括為三大規律:對立統一、質量互變規律、和否定之否定規律。其中揭示發展方向和道路的是否定之否定規律。否定之否定規律認為,任何事物在整體上的完善和發展都要經歷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兩次否定三個階段才能實現自我完善和自我發展。本文從否定之否定規律出發探尋人與自然之間不斷完善和發展基本路徑。
[關鍵詞]人與自然;否定之否定規律;完善和發展
任何事物內部都存在肯定因素和否定因素。肯定因素是維持現存事物存在的因素,否定因素是促使新事物的產生舊事物的滅亡的部分。當事物處于肯定階段時,事物內部矛盾的主要方面居于統治地位,矛盾主要方面的性質也得以充分展開。而事物內部矛盾的次要方面卻受到了壓制,矛盾次要方面的性質也未體現出來。這時事物是片面的不完善的。當事物處于否定階段時,矛盾的次要方面上升為主要方面,性質也得以充分的展現,而原來居于主要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卻受到了壓制,性質也未得以充分展開。可見,經過一次否定后事物一方面的性質得以展開的同時,另一方面的性質卻受到限制。這時事物仍然是片面性、不完善的。因此事物要達到完善和發展必須經過第二次否定,進入第三個階段,即否定之否定階段。第三個階段是把第一個階段和第二個階段展開的性質結合起來,并克服了前面兩個階段的片面性和不完善性。把對立的雙方結合起來,吸收前兩個階段的優點并克服了其缺點,使事物達到完善和發展。如果事物只停留在肯定階段或者否定階段,事物永遠是片面的,只有再次否定事物才能完善。
所以事物要達到“自我完善”的目標必須經歷兩次“否定”“三個階段”“一個周期”才能達到。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揭示的事物發展過程中遵循的否定之否定規律。恩格斯在寫作《反杜林論》的準備材料中,把事物自己發展中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過程,稱之為“對立之劃分,對立的斗爭之解決”,而把杜林所說的肯定和否定的無限交替稱之為“惡劣的、沒有結果的否定”,并指出:“這種沒有結果的否定是純粹主觀的、個人的否定,它不是事物本身的一個發展階段,而是由外部硬加進去的意見。由于從這種否定中不能得出任何結果,所以作這種否定的人就必然與世界不和,必然要放肆地非難現存的和以往的一切,非難整個歷史發展。”
人的內在本質須對象化于自然、人化自然,這是第一次否定。經過這一次否定人還沒有“自我完善”。雖然人的本質內化于自然亦自然人化,但是人如果不能享用這個對象化的自然反而受其奴役、控制。人與自然異化就是其典型的表現。為此,人需要對這個人化的自然再次否定,使這個人化的自然能為主體服務。也就是說第一次否定造成主觀和客觀的兩極對立,第二次否定使客觀性的東西重新回到人自身,從更高層次作為人的無機身體而存在。即人創造的東西能更好的滿足主體的需要,這樣就實現完善和發展了。人的本質在客體中得以實現和確證,同時這個客體又能為人所服務。人只有在不斷的否定自然、改造自然的過程中人才能實現“自我完善”“自我發展”。下面我們就具體來看一下人在改造自然中不斷完善自身經歷的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肯定階段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吧自然界描述成人的“無機身體”。在馬克思看來,人和動物一樣依賴無機界,人對自然界的依賴具體表現為兩個領域,即理論領域和實踐領域。“從理論領域來說,植物、動物、石頭、空氣、光等等,一方面作為自然科學的對象,一方面作為藝術的對象,都是人的意識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無機界,是人必須事先進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糧;同樣,從實踐領域來說,這些東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動的一部分。在實踐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現為這樣的普遍性,它把整個自然界——首先作為人的直接的生活資料,其次作為人的生命活動的對象(材料)和工具——變成人的無機的身體。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體而言,是人的無機的身體。”[1]
在生產力水平低下,我們的祖先只能依據最簡單的工具進行最簡單的勞動與然界之間發生最簡單的關系。從大自然中獲取生產和生活資料從而使自身得以生存,使種族得以繁衍下去。他們能否生存,生存程度如何,這完全受著周圍環境和各種現象的制約。在自然災害面前除了躲避和敬畏之外,別無選擇。人更多的時候是被動的適應這個環境,而不是積極主動的去改造這個環境。大自然更多的時候還是在人類面前展示出自己風柔日暖、萬紫千紅、芳草鮮美的一面,人對大自然是充滿了無限的暇想和期望。大自然在低層次作為人的無機身體而存在,人與自然天然的融為一體。人還沒有意識到自己與自然界的區別,也未曾想過要與自然界發生分化,人天然地尊重、敬畏和肯定自然。
第二階段——“否定階段”
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任何事物都包含肯定方面和否定的方面。肯定和否定兩者是一種辯證的關系,一方面兩者相互區別,但是另一方面兩者也是相互聯系的。肯定是包含著否定的肯定,肯定中如果不包含著否定事物就不會運動變化和發展。人與自然處于肯定階段只是暫時的,不會一直持續下去,否則人類就永遠不會進步發展,世界就永遠沒有任何生機和活力。人與動物的一個本質區別在于人具有自覺能動性,人不會被動的去適應自然,會積極主動的去改造自然。人要生存下去必須對自然界進行改造,從自然界獲取生產和生活資料的來源。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人類的發展史就是一部生產發展史。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各種聯系和關系都是在人與自然的對象性的活動中形成的。“說人是有形體的、賦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現實的、感性的、對象性的存在物,這就等于說,人有現實的、感性的對象作為自己的本質、自己的生命的表現的對象;或者等于說,人有現實的感性的對象作為自己的本質、自己的生命表現的對象”[2]自然界作為人的無機身體,是人的本質對象化所不可缺少的對象,人類在改造自然界的活動中把自己的本質力量對象化于自然并在自然中確證自己的本質力量。人在一定的目的計劃動機的支配下進行實踐活動,按照人的內在尺度對自然界進行改造,按照人的方式來調節和控制物質生產實踐活動的方向和過程。在人的實踐活動過程中,天然自然這個自在之物日益轉化為能滿足主體需要體現主體目的的為我之物。
隨著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人類步入了農業文明時期。人們試圖改造自然,造成人對自然地依附性減弱,對抗性增強,地理環境趨于惡化,出現了局部的環境問題。但總體來說,人與自然還未分離。人類對自然界的改造主要集中在對地表光、熱、水、土、資源的利用上,人對自然地破壞還不夠深,自然在一定程度上還具有自我調節和自我恢復的能力,自然仍然與人融為一體。由于科學技術的進步,人與自然關系關系中介物—生產勞動工具的巨大改革和進步,人對自然界的作用大大提高。人類文明出現了第二次轉折,從傳統農業社會進入到工業社會。工業社會與農業社會相比人類活動有了空前的發展,人類對自然的干預能力有了巨大的提高。這種巨大的活動強度,來源于工業社會的資源基礎和技術基礎確立以后,很快形成了新的技術、經濟、社會、文化相互協調、適應的系統結構,強化了人類不斷開發利用資源的進行財富積累的過程。在只有短短幾百年的工業文明時代內人類在開發、改造自然方面獲取的成就遠遠超過了過去一切時代的總和。人類在對自然的改造方面無論是在廣度上還是深度上都取得了很大的進步。然而在工業文明給人類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的同時,卻給自然造成了難以彌補的傷害,因而使人類自己也陷入了著巨大的生態危機中。人類對自然進行肆意的掠奪而不顧資源和環境的承載能力,使自然界喪失了自我修復能力。“人類好像一夜之間突然發現自己正面臨著史無前例的大量危機:人口危機、環境危機、糧食危機、能源危機、原料危機等等………這場全球性的危機程度之深、克服之難,對迄今為止指引社會進步的若干基本觀念提出了挑戰。”[3]自然界也向人類進行了瘋狂的報復——生態危機、生態失衡就是很好的證明。這時的人與自然處于技術的兩端。人類以自然界的主人自居處于改造的一方,自然界則處于被改造的一方。人與自然漸行漸遠繼而形成一種對抗性的關系。
第三階段——“否定之否定階段”
以人的自我完善過程看,人的理想、目的在未對象化之前是主觀性的,在對象化之后,即被否定了之后變成了客觀性的了,變成人化自然,但主觀性和客觀性是兩極,兩種片面性,因而須對人化自然再次否定后方能達到完善。圖示:
在第三階段-否定之否定階段,事物的基礎、內容都進到了一個更高階段上了,因而我們將它叫做仿佛回到出發點。回到出發點的意思是說經過兩次否定事物并沒有離開自己。這表明事物的發展是自我的發展,發展的主體是自我。
近代的工業革命結束了漫長的農業社會,使人類步入一個全新的機器大工業時代。在這時期人們把自然當做可以任意擺布的機器、可以任意索取的對象。長期在這種思想的支配下人們發現人們對自然界改造范圍越廣,自己能夠棲居的地方越窄。把自然界改造的越是美好,人類自己反而變得更加丑陋;對自然界的改造力度越大,自己反而變得越發無力;改造自然的技術含量越高,人類反而變得更加的愚笨。馬克思曾指出,工業”一方面聚集著社會的歷史動力,另一方面破壞著人與土地之的物質交換,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費掉的土地的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從而破壞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件。”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警告世人:“但是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遺憾的是,人們對此置若罔聞。就因為他們過分癡迷于身外之物(物質財富),而失去了“打開進入內在生命可能性的、通往價值階段的意識,”[4]他們不再能“覺知自己深處的真實”[5],已無法聽到其“內在的聲音以求得平衡”[6]。
自然界是人的無機身體,人的生存和發展離不開大自然。如果有一種技術把人與自然隔離開來,切斷了人與自然界的這種天然的聯系,這樣的技術無論多么先進,算是什么技術呢?“那些拖著病體在市場、職場拼搏,然后再花大筆金錢去購買健康(買保健品或住院治病)的人,則是最不懂得關心自己的人。”[7]在自然的規定范圍內,可制作,可創造,可施展聰明才智。但是,自然的規定不可違背。人不可背離土地,不可遮蔽天空,不可忤逆自然之道。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此之謂也。一位英國詩人吟道:“上帝創造了鄉村,人類創造了城市。”創造城市,在大地上演繹璀璨的人生篇章,證明了人的智慧。可是,假如人用自己創造的東西把自己和上帝饋贈的禮物隔離開來,那就是愚昧和無知。把上帝饋贈的禮物排擠和毀壞,那就是褻瀆。
人在對自然進行改造的時候,一定要時時記得反思,反思這個人化的自然,對這個人化的自然進行再次否定。使這個被改造過的自然能重新回到人自身,從更高的層次作為人的無機身體而存在。不光是人的物質生活資料的來源,同時也是人的精神資料的來源。自然界就如同我們身體的其他器官一樣,當我們的無機身體—自然遭受苦難時,我們人類也遭受苦難,當我們的無機身體—自然被毀滅之時,我們人類也將面臨滅頂之災。德韋爾和塞欣斯認為:“誰也不會獲救,除非我們大家都獲救。這里‘誰不近包括我自己、單個的人、還包括所有的人、鯨魚、灰熊、完整的熱帶雨林、生態系統、高山河流、土壤中的微生物等。”我們一定不要等到走到窮途末路時,才開始思考是否曾經做錯了。人類應該時刻傾聽來自自己內心深處的聲音,人若連這種功能都喪失了,人就會在改造自然地過程中迷失自己。人只有明白自己是誰?才能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也才能明白如何以自我的方式去改造自然。這種改造是否能將人帶向自由、自覺的幸福生活。人一旦在改造自然中迷失了自我,自然界當然也不會以“自我”的本質來確認“自我”的存在。所以一定要提醒自己對自然的改造一定要返回自身,不斷地調整人與自然行進的步伐。否則自然會離人類越來越遠,從而走向人的對立面。相信我們人類一定會能夠昂首挺胸,與自然達到肉體上極度契合,靈魂上的高度統一。重新擁有一片蔚藍的天空,走出人與自然地異化,實現兩者的同一。
參考文獻:
[1][2]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P56.P121
[3]梅薩羅維克等著,劉長毅等譯[M].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1987.P78
[4][5][6][日]池田大作,[法]路奈·尤伊古.黑夜尋求黎明[M].卞立強譯,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3.P138,P178,P217.
[7]盧風.“關心自己”與關愛地球—兼談“人性革命”[J].中晉陽學刊,2010年第四期.
作者簡介:盧小青(1988-),女,安徽巢湖市廬江縣人,重慶人文科技學院基礎教學部助教研究方向:應用倫理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