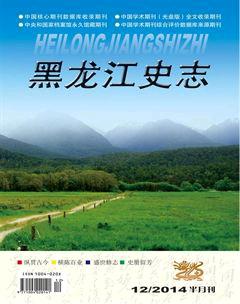論《唐律疏議》中的人情
胡秀全
[摘 要]我國古代社會(huì),天理無非人情,王法本乎人情,重視人情是我國傳統(tǒng)法文化的一大特色。受儒家文化影響,我國的傳統(tǒng)人情有人之常情(以忠孝為核心)和人情世故兩層含義。傳統(tǒng)人情以禮為核心,和諧而又沖突:人情與法律的和諧,以不孝罪、留養(yǎng)制度和親屬相犯為代表,《唐律疏議》將之法律化,人情與法律相融合;人情與法律的沖突,以為親復(fù)仇、恤刑和赦免為例,《唐律疏議》中有相異甚至是矛盾的規(guī)定。
[關(guān)鍵詞]中國;傳統(tǒng)法文化;人情;《唐律疏議》
一、我國古代社會(huì)中的人情
《論語·子路》言“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1)”,《論語·顏淵》云“片言可以折獄,其由也歟(2)”;孔子認(rèn)為法律應(yīng)當(dāng)“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公正蘊(yùn)含在人情之中,行事符合人情,才是最大的公正。
人情歸屬于文化領(lǐng)域,必然受其所處時(shí)代的影響,以儒家文化為背景的傳統(tǒng)人情必定蘊(yùn)含儒家經(jīng)義。
《禮記·大傳》強(qiáng)調(diào):“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3)”,“親親”和“尊尊”分別對應(yīng)孝和忠,儒家文化被確立為封建正統(tǒng)后,孝和忠被發(fā)揚(yáng)光大,成為一個(gè)人道德水平的評判標(biāo)準(zhǔn),傳統(tǒng)的人情觀也烙上了忠孝的印記。《禮記·禮運(yùn)》記:“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xué)而能(4)”;唐代法哲學(xué)家韓愈、明代法哲學(xué)家王陽明也有同樣的觀點(diǎn);古代思想家所論的人情是社會(huì)性的人類的普遍情感,也就是所謂的人之常情。由此而言,傳統(tǒng)的人情是帶有儒家倫理性的以忠孝為核心的人之常情。
“仁”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儒家學(xué)派的最高道德準(zhǔn)則,如:孔子的“仁者愛人”、孟子的“惻隱之心”和“義”。儒家文化影響下的兩千余年間,仁義、為政以德、安居樂業(yè)等觀念,深入國人的靈魂,影響著國人的一言一行,成為國人日常生活中約定俗成的行為規(guī)則。由此而講,傳統(tǒng)人情指我國古代社會(huì)中的人情世故。
綜上所述,傳統(tǒng)社會(huì)中的人情有兩方面的內(nèi)涵,一是指帶有儒家倫理性的以忠孝為核心的人之常情,二是指我國古代社會(huì)的人情世故。
二、人情與《唐律疏議》的鏈接
儒家文化一直是我國古代社會(huì)的正統(tǒng)文化,統(tǒng)治者制定的律法中蘊(yùn)含儒家經(jīng)義。兩千余年影響下,“天理無非人情”,“王法本乎人情”,崇尚、重視人情,成為我國傳統(tǒng)法的一大特色。儒家文化傳承于西周的禮文化,“親親”、“尊尊”是禮文化的基本原則,“親親父為首”,“尊尊君為首”,分別維護(hù)宗族和國家的秩序。從某種程度上而言,我國古代人情與法律的關(guān)系,便是禮與法的關(guān)系。
在我國古代禮法融合進(jìn)程中,《唐律疏議》總結(jié)以往各王朝的立法經(jīng)驗(yàn)及司法實(shí)踐,折中損益,以儒家道德倫理為思想理論基礎(chǔ),熔禮法于一身,以“一準(zhǔn)乎禮”著稱,標(biāo)志著我國古代禮法融合的真正完成。我國古代,緣情制禮,因禮制律,在人情法律化的進(jìn)程中,《唐律疏議》處于承前啟后的地位。
人情與法律,以禮為核心,和諧而又沖突。“合情又合法”,人情溶于法律,合法即是合情,這便是人情與法律的和諧。人類社會(huì)的復(fù)雜性,使人情與法律在具體適用過程中,不可避免會(huì)“合情不合法”或“合法不合情”。因禮法融合程度的不同,人情與法律和諧或沖突的表現(xiàn)形式亦不相同。體現(xiàn)在《唐律疏議》中,人情與法律的和諧指對同一法律現(xiàn)象無相異的規(guī)定,人情與法律的沖突則指對同一法律現(xiàn)象有相異甚至是矛盾的規(guī)定。
三、《唐律疏議》中的人情體現(xiàn)
俗語道“百行孝為先”,《孝經(jīng)》載“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5)”,將不孝視為最大的犯罪。人情與法律的和諧,首先表現(xiàn)為不孝罪。
現(xiàn)存史料中,不孝罪的明確定義見于《唐律疏議·名例》“謂告言、詛詈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別籍、異財(cái),若供養(yǎng)有缺;居父母喪,身自嫁娶,若作樂,釋服從吉;聞祖父母父母喪,匿不舉哀,詐稱祖父母父母死。(6)”可知,唐代不孝罪體現(xiàn)在:日常生活中不順父祖;冒犯(觸犯父祖名諱或狀告、咒罵甚于毆打、殺害)父祖;父祖被囚或喪葬期間違背禮的規(guī)定。
日常生活中的不孝,體現(xiàn)于《唐律疏議·戶婚》155條、157條和《唐律疏議·斗訟》348條。例如:唐律155條規(guī)定:“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孫別籍、異財(cái)者,徒三年。(7)”
冒犯父祖,體現(xiàn)于唐律的職制、詐偽、斗訟、賊盜四篇,具體為:《唐律疏議·職制》121條,《唐律疏議·詐偽》383條,《唐律疏議·斗訟》345條、329條、330條、331條和314條,《唐律疏議·賊盜》253條、255條和260條。例如:唐律121條規(guī)定:“諸府號、官稱犯父祖名,而冒榮居之;祖父母、父母老疾無侍,委親之官;即妄增年?duì)睿郧笕胧碳懊鞍笫苏撸和揭荒辍V^父母喪,禫制未除及在心喪內(nèi)者。若祖父母、父母及夫犯死罪,被囚禁,而作樂者,徒一年半。(8)”
父祖被囚或喪葬期間的不孝,體現(xiàn)于《唐律疏議·戶婚》162條、180條、156條、179條、181條、188條和《唐律疏議·職制》120條。例如:唐律156條規(guī)定:“諸居父母喪,生子及兄弟別籍、異財(cái)者,徒一年。(9)”
不孝是對孝道的違犯,為親復(fù)仇是對孝道的一種極致表現(xiàn)。儒家文化影響下,因孝悌而復(fù)仇是傳統(tǒng)社會(huì)的一種高尚倫理。
關(guān)于復(fù)仇,體現(xiàn)于《唐律疏議·斗訟》335條、256條、265條和《唐律疏議·賊盜》265條。例如:唐律265條“移鄉(xiāng)避仇”規(guī)定:“諸殺人應(yīng)死會(huì)赦免者,移鄉(xiāng)千里外。(10)”
唐律26條規(guī)定:“諸犯死罪非十惡,而祖父母、父母老疾應(yīng)侍,家無期親成丁者,上請。犯流罪者,權(quán)留養(yǎng)親。(11)”。依儒家孝道,子孫應(yīng)盡養(yǎng)老送終的義務(wù),統(tǒng)治者為體現(xiàn)對孤寡老弱的憐恤之心,在符合“孀婦獨(dú)子”的情形下,經(jīng)刑部提出留養(yǎng)申請,獲得皇帝首肯后,免予死刑,在施以一定處罰后準(zhǔn)其留養(yǎng)以奉養(yǎng)其父母長輩或承續(xù)其家族血脈,這是孝道的又一表現(xiàn)——留養(yǎng)制度。
唐律52條規(guī)定:“諸稱期親及稱祖父母者,曾、高同。稱孫者,曾、玄同。嫡孫承祖,與父母同。緣坐者,各從祖孫本法。其嫡、繼、慈母,若養(yǎng)者,與親同。稱子者,男女同。緣坐者,女不同。稱袒免以上親者,各依本服論,不以尊壓及出降。義服同正服。(12)”這是唐代五服的規(guī)定,為晚輩子女與父母祖父母之外的親屬犯罪時(shí)適用,包括親屬相告、親屬相盜、親屬相毆、親屬相奸和親屬相殺。
親屬相告,體現(xiàn)在兩方面。一是鼓勵(lì)親親相隱,唐律46條規(guī)定:“諸同居,若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若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為隱(13)”;二是限制親屬相告,體現(xiàn)于《唐律疏議·斗訟》345條、346條和347條,例如:唐律345條規(guī)定“諸告祖父母、父母者,絞。(14)”
親屬想盜,體現(xiàn)于《唐律疏議·賊盜》287條和288條。例如:唐律疏議287條規(guī)定:“諸盜緦麻、小功親財(cái)物者,減凡人一等;大功,減二等;期親,減三等。(15)”
親屬相毆,體現(xiàn)于《唐律疏議·賊盜》294條、325條、326條、327條、328條、332條、333條、334條和《唐律疏議·斗訟》324條。例如:唐律327條規(guī)定:“諸毆緦麻兄姊,杖一百。小功、大功,各遞加一等。尊屬者,又各加一等。傷重者,各遞加凡斗傷一等;死者,斬。即毆從父兄姊,準(zhǔn)凡斗應(yīng)流三千里者,絞。若尊長毆卑幼折傷者,緦麻減凡人一等,小功、大功遞減一等;死者,絞。(16)”
親屬相奸,體現(xiàn)于《唐律疏議·雜律》411條、412條和413條。例如:唐律413條規(guī)定:“諸奸父祖妾、謂曾經(jīng)有父祖子者。伯叔母、姑、姊妹、子孫之婦、兄弟之女者,絞。即奸父祖所幸婢,減二等。(17)”
親屬相殺,體現(xiàn)于《唐律疏議·賊盜》253條、287條、288條、325條、327條、328條、334條和《唐律疏議·斗訟》345條。例如:唐律253條規(guī)定:“謀殺緦麻以上尊長者,流二千里;已傷者,絞;已殺者,皆斬。即尊長謀殺卑幼者,各依故殺罪減二等;已傷者,減一等;已殺者,依故殺法。(18)”
我國古代,嚴(yán)格遵循法律,依法斷案可能招致輿論的非議,相反,曲法申情之舉則會(huì)被視為仁政或者德政。恤刑和赦免便是統(tǒng)治者為體現(xiàn)其仁慈之心而對犯罪者的法外施恩。
恤刑,體現(xiàn)于《唐律疏議·名例》30條、31條和《唐律疏議·斷獄》474條、494條、495條。例如:唐律495條規(guī)定:“諸婦人懷孕,犯罪應(yīng)拷及決杖笞,若未產(chǎn)而拷、決者,杖一百;傷重者,依前人不合捶拷法;產(chǎn)后未滿百日而拷?jīng)Q者,減一等。失者,各減二等。(19)”
除卻對老幼婦殘的矜恤,恤刑還體現(xiàn)在刑訊過程中的慎刑,體現(xiàn)于《唐律疏議·斷獄》476條、477條、478條和497條。例如:唐律476條規(guī)定:“諸應(yīng)訊囚者,必先以情,審察辭理,反覆參驗(yàn);猶未能決,事須訊問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訊。違者,杖六十。若贓狀露驗(yàn),理不可疑,雖不承引,即據(jù)狀斷之。(20)”
我國古代,皇帝的權(quán)力至高無上,其命令凌駕于法律之上,赦免是皇帝的專有權(quán)力,是人情與法律沖突的典型。關(guān)于赦免,體現(xiàn)于《唐律疏議·斷獄》488條、489條。例如:唐律489條規(guī)定:“諸聞知有恩赦而故犯,及犯惡逆,若部曲、奴婢毆及謀殺若強(qiáng)奸主者,皆不得以赦原。即殺小功尊屬、從父兄姊及謀反大逆者,身雖會(huì)赦,猶流二千里。(21)”
此外,我國古代體現(xiàn)人情的法律制度還有春秋決獄和宥過制度,唐律雖未規(guī)定,但司法實(shí)踐中,遇到唐律無規(guī)定的情形,司法官仍會(huì)適用自由裁量,依據(jù)儒家經(jīng)義斷案或者心生惻隱以減免對罪犯的刑罰。
四、余論
我國傳統(tǒng)的人情因素,源自我國自身的歷史文化背景,符合國人的生活習(xí)慣和道德信仰,更易為國人所接受、認(rèn)同,至今仍影響著國民的觀念與行為方式,并一定程度上與現(xiàn)代法治精神與實(shí)踐相契合。根植于我國的優(yōu)秀傳統(tǒng)法律文化,重新認(rèn)識人情的合理因素,可以推進(jìn)我國的法律現(xiàn)代化。
參考文獻(xiàn):
[1]孔子撰,張燕嬰譯.論語[M].北京:中華書局,2006.
[2]巢峰主編.辭海·語詞分冊[M].上海辭書出版社,1979.
[3]錢玄等譯.禮記[M].長沙:岳麓書社,2001.
[4]孔子撰,陳書凱譯.孝經(jīng)[M].北京:中國紡織出版社,2007.
[5][唐]長孫無忌等.唐律疏議[M].北京:中華書局,1983.
[6]史廣全.禮法融合與中國傳統(tǒng)法律文化的歷史演進(jìn)[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7]史廣全.中國古代立法文化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8]馬小紅.禮與法:法的歷史鏈接[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4.
[9]馬小紅.中國古代社會(huì)的法律觀[M].鄭州:大象出版社,1997.
[10]武樹臣.中國傳統(tǒng)法律文化[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4.
[11]俞榮根.儒家法律思想通論[M].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2.
[12]范忠信等.情理法與中國人:中國傳統(tǒng)法律文化探微[M].上海:上海書店,1992.
注釋:
(1)孔子撰,張燕嬰譯.論語[M].北京:中華書局,2006,95頁.
(2)孔子撰,張燕嬰譯.論語[M].北京:中華書局,2006,178頁.
(3)錢玄等譯.禮記[M].長沙:岳麓書社,2001,第457頁.
(4)錢玄等譯.禮記[M].長沙:岳麓書社,2001,第306頁.
(5)孔子撰,陳書凱譯.孝經(jīng)[M].北京:中國紡織出版社,2007,第116頁.
(6)[唐]長孫無忌等.唐律疏議[M].北京:中華書局,1983,第12頁.
(7)[唐]長孫無忌等.唐律疏議[M].北京:中華書局,1983,第236頁.
(8)[唐]長孫無忌等.唐律疏議[M].北京:中華書局,1983,第206頁.
(9)同(1).
(10)[唐]長孫無忌等.唐律疏議[M].北京:中華書局,1983,第341頁.
(11)[唐]長孫無忌等.唐律疏議[M].北京:中華書局,1983,第69頁.
(12)[唐]長孫無忌等.唐律疏議[M].北京:中華書局,1983,第136頁.
(13)[唐]長孫無忌等.唐律疏議[M].北京:中華書局,1983,第130頁.
(14)[唐]長孫無忌等.唐律疏議[M].北京:中華書局,1983,第432頁.
(15)[唐]長孫無忌等.唐律疏議[M].北京:中華書局,1983,第365頁.
(16)[唐]長孫無忌等.唐律疏議[M].北京:中華書局,1983,第411頁.
(17)[唐]長孫無忌等.唐律疏議[M].北京:中華書局,1983,第494頁.
(18)[唐]長孫無忌等.唐律疏議[M].北京:中華書局,1983,第327頁.
(19)[唐]長孫無忌等.唐律疏議[M].北京:中華書局,1983,第570頁.
(20)[唐]長孫無忌等.唐律疏議[M].北京:中華書局,1983,第552頁.
(21)[唐]長孫無忌等.唐律疏議[M].北京:中華書局,1983,第56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