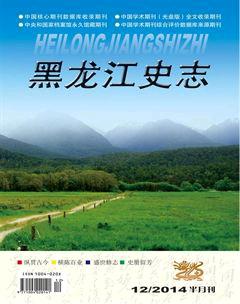論洋務(wù)運(yùn)動(dòng)時(shí)期官督商辦中的官商關(guān)系
李婷婷 丁文
[摘 要]官督商辦是晚清洋務(wù)運(yùn)動(dòng)中實(shí)施的一種特殊的企業(yè)機(jī)制,出現(xiàn)在十九世紀(jì)七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達(dá)到全盛。特殊的歷史背景造就了這一特殊的企業(yè)機(jī)制,在這一對(duì)矛盾關(guān)系中,既存在相互利用的一面,又存在相互斗爭(zhēng)的一面,對(duì)歷史發(fā)展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的影響。
[關(guān)鍵詞]洋務(wù)運(yùn)動(dòng);官督商辦;官商關(guān)系;斗爭(zhēng);利用
一、洋務(wù)運(yùn)動(dòng)時(shí)期官督商辦企業(yè)產(chǎn)生的歷史背景
(一)洋務(wù)派需要資金來(lái)振興商務(wù)
七十年代,洋務(wù)派打著“自強(qiáng)”的旗號(hào)興辦起來(lái)的官辦軍事企業(yè)已經(jīng)很難維持下去了。我們知道,要振興商務(wù),首先需要充足的資金作為保證。正如當(dāng)時(shí)一個(gè)熟悉洋務(wù)活動(dòng)的代表人物所說(shuō)的:“講求土貨則需款,仿造洋貨則需款,開(kāi)采寶礦則需款”。無(wú)論做什么,都需要資金。但是當(dāng)時(shí)清政府不斷對(duì)外賠款,對(duì)內(nèi)鎮(zhèn)壓人民起義開(kāi)支大量軍費(fèi),明顯力不從心。在國(guó)庫(kù)空虛時(shí),封建官僚自然而然地講目光投到了有錢(qián)的商人身上,尤其是當(dāng)時(shí)一些暴發(fā)戶(hù)的買(mǎi)辦商人。李鴻章在籌辦招商局時(shí)說(shuō)過(guò):“近年來(lái)華商殷實(shí)狡黠者多附洋商名下,如旗昌、金利源等,華人股份居其大半”這些華商的資金就成了洋務(wù)派的資金來(lái)源。
(二)買(mǎi)辦商人需要官的統(tǒng)治地位作為支持,對(duì)官抱有幻想
買(mǎi)辦商人在洋行企業(yè)中積累了巨額資金,非常渴望獨(dú)立發(fā)展,追求更大的利潤(rùn),但擺在面前的是重重的封建阻力,所以,他們對(duì)官抱有極大的幻想,希望將官權(quán)作為自身發(fā)展的保護(hù)傘,以便給自己的投資帶來(lái)格外優(yōu)厚的利潤(rùn)。他們認(rèn)為自己找到了壯大力量行之有效的辦法并逐步將“官督商辦”神奇化進(jìn)行大量投資。洋務(wù)派想利用“官督商辦”來(lái)收取商人資本,同時(shí),買(mǎi)辦商人想靠“官督商辦”來(lái)收萬(wàn)世之利。我們可以說(shuō),正是有了這個(gè)共同的利益點(diǎn),原本對(duì)立的官、商結(jié)成了一對(duì)特殊的矛盾,使官督商辦有了實(shí)現(xiàn)的可能。
二、洋務(wù)運(yùn)動(dòng)時(shí)期官督商辦企業(yè)中的官商關(guān)系
(一)官商相互利用
李鴻章在籌辦第一個(gè)官督商辦企業(yè)輪船招商局時(shí)對(duì)“官督商辦”做過(guò)說(shuō)明,大體意思就是說(shuō):“由官總其大綱,察其利弊”,“所有盈虧全歸商人與官無(wú)涉”。以后的官督商辦基本都是以這兩句話(huà)為基準(zhǔn)的。可以知道,官就是通過(guò)總其大綱的方式來(lái)掌握對(duì)企業(yè)的控制權(quán)。
(二)官商相互矛盾斗爭(zhēng)
1、商挾私用人,阻礙管理制度規(guī)范的規(guī)范
在官督商辦企業(yè)創(chuàng)辦的規(guī)劃中,李鴻章表示應(yīng)該選舉投資較多的人為商董,然后再“聽(tīng)該商董等自定條議悅服眾商”,還說(shuō)“商務(wù)應(yīng)由商任,不能由官任之”。如果事實(shí)能夠如此,便能使官督商辦更接近于開(kāi)辦時(shí)的理念,但這只不過(guò)是為了招攬商戶(hù)所說(shuō)的好聽(tīng)的話(huà),事實(shí)證明這一說(shuō)辭并沒(méi)有得到過(guò)認(rèn)真的兌現(xiàn)。在他親自批準(zhǔn)的官督商辦企業(yè)的“用人章程”中就明確規(guī)定了“專(zhuān)派大員一人認(rèn)真督辦,用人、理財(cái)悉聽(tīng)調(diào)度”,這樣產(chǎn)生的督辦有封建政權(quán)撐腰。督辦為了擴(kuò)充自己的勢(shì)力而挾私用人,培植黨羽,“血統(tǒng)關(guān)系”、“裙帶關(guān)系”、“心腹舊故關(guān)系”自然而然就成了他們的用人準(zhǔn)則。盛宣懷從十九世紀(jì)七十年代起任過(guò)幾個(gè)官督商辦企業(yè)的督辦,是“任人唯親”的典型。比如中國(guó)電報(bào)局在各地分支機(jī)構(gòu)的負(fù)責(zé)人中盛宣懷的叔父、堂弟、姻親、外甥、女婿、堂侄就高達(dá)31人。另外,唐廷樞兄弟長(zhǎng)期控制廣州分局,李鴻章的舊故麥佐控制天津分局,更有甚者由他們“兄授其弟,父?jìng)髌渥樱癫灰詾楣帧边_(dá)二三十年之久。在這種用人制度之下,投資者絲毫沒(méi)有發(fā)言權(quán),開(kāi)始是所說(shuō)的“商務(wù)應(yīng)由商任”明顯變成了一句空話(huà)。好的企業(yè)管理制度,是企業(yè)健康發(fā)展的保證,只有將企業(yè)置于規(guī)范嚴(yán)格的管理之中,才能使企業(yè)健康有序地發(fā)展。反之,要想依靠這種挾私用人的制度管理好企業(yè),自然是不可能的。所以,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官督商辦企業(yè)的發(fā)展,注定要走向失敗。
2、營(yíng)私舞弊、貪污腐敗造成積累不足
一名著名評(píng)論家在清王朝崩潰前夕,對(duì)官督商辦企業(yè)內(nèi)部的腐敗情況進(jìn)行了這樣的描述:“正如肥肉自天而降,蟲(chóng)蟻聚食,不盡不止。”蟲(chóng)蟻聚食的根子就在“官督”。官督有封建政權(quán)撐腰,督辦在用人、理財(cái)方面把清末衙門(mén)里的腐敗一套帶進(jìn)了企業(yè)管理當(dāng)中。1887年輪船招商局購(gòu)買(mǎi)旗昌輪船公司時(shí),發(fā)現(xiàn)旗昌有房產(chǎn)三十間、洋房十七所,價(jià)值五十萬(wàn)兩。1897年,盧漢鐵路施工時(shí),眼看沿線(xiàn)地價(jià)要漲,當(dāng)時(shí)官督商辦漢陽(yáng)鐵廠總辦鄭觀應(yīng)就密函盛宣懷,請(qǐng)其立購(gòu)二百畝,如果沒(méi)有許多好地或購(gòu)漢地百余畝,河南、直隸各數(shù)十畝也可,并請(qǐng)他不要聲張。這就是總辦和督辦在職權(quán)上勾結(jié)營(yíng)私。至于總辦以下,就更是上行下效。比如天津電報(bào)局的總辦每年可以撈近兩萬(wàn)元。商賈們對(duì)官進(jìn)行強(qiáng)烈的控訴,但卻無(wú)力回天,無(wú)法制止這種蟲(chóng)蟻聚食的狀況,因?yàn)橐哉麄€(gè)封建勢(shì)力為后臺(tái)的“官督”制度不是商賈們忿激的呼聲所能動(dòng)搖的。這樣的蠶食鯨吞造成的直接結(jié)果就是企業(yè)的積累不足,最終走向失敗。第一個(gè)官督商辦企業(yè)招商局就是一個(gè)典型例子。從1874年到1884年,招商局的總支出共3757395兩,其中各種利息、官利、官款利息三項(xiàng)的支出就高達(dá)3125902兩,占到了中支出的百分之八十三點(diǎn)二,本來(lái)應(yīng)該支出的折舊費(fèi)只有23106兩,僅僅占到總支出的百分之零點(diǎn)五六。僅1884年一年用于“商紳情面挪用未還款”的壞賬損失就達(dá)到18萬(wàn)兩。這樣的資金流動(dòng),怎能談得上積累與擴(kuò)張呢?其他的官督商辦企業(yè)也沒(méi)有逃脫這種命運(yùn),到后來(lái)都處于勺水無(wú)源,其固立待的尷尬局面了。
參考文獻(xiàn):
[1]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C].臺(tái)北:文海出版社,1962.
[2]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譯署函稿[C].臺(tái)北:文海出版社,1962.
[3]孫毓棠.中國(guó)近代工業(yè)史資料·下冊(cè)[M].北京: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1957.
[4]交通鐵道部交通史編纂委員會(huì).交通史·航政篇:第1冊(cè),[M].上海:交通鐵道部交通史編纂委員會(huì).1935.
[5]李孤帆.招商局三大案[M].上海:現(xiàn)代書(shū)局,1933.
[6]沈祖煒.政府經(jīng)濟(jì)政策和經(jīng)濟(jì)發(fā)展[A].上海:上海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1992.
[7]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