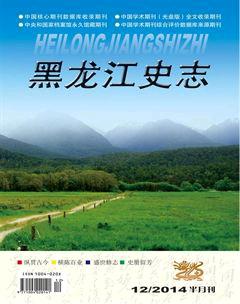現實·審美·幻象
馬愛忠
[摘 要]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是以現實世界為構思起點的。現實生活的“頗不寧靜”迫使他走向心儀已久的“審美世界”:荷塘。在荷香月色中,如醉如癡的審美體驗洗滌了塵世的疲倦,心靈得到了真正的審美愉悅。但是,猝然而終的荷塘世界沒法使他的審美享受得到延續。為了填補心靈的空虛,作者又構建了一個古典的幻象世界。因此,“三個世界”是作者的漫步荷塘的三個階段,也是思緒連貫的三個心理過程。
[關鍵詞]《荷塘月色》;現實世界;審美世界;幻像世界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朱自清先生是一位赫赫有名的散文大師,“他在對自然景物的描寫中,把深藏于內心深處的獨特感受和脈脈情愫融化在對景色的描繪之中,在情景交融中使作品充滿了一種濃郁的意境。”(1)他的散文《荷塘月色》被奉為中國現代散文的典范之作,其藝術價值是多方面的。錢理群先生就說過,該文最突出的特點是意境與情韻的“明凈淡雅”(2)。依筆者之見,作者的思緒在現實、審美和幻想三個世界中穿梭,從而獲得連續的審美體驗是該文不同凡響的原因之一。正因為如此,《荷塘月色》的深層結構呈三層立體型,即作者由紛繁的現實世界進入恬美、寧靜的審美世界,得到了從“悅耳悅目”到“悅神悅志”(3)的審美愉悅,但這種審美愉悅隨著自己走出荷塘而終止。為了延續先前的審美享受,作者就用古典詩文的意境構建了一個幻象世界。朱先生正是按照這種思路處理該文的外在結構和內部情韻的。現具體分析如下:
一、紛繁的現實世界
從《荷塘月色》開篇第一句話“這幾天心里破不寧靜”中,我們就能揣摩出作者當時的心境:身處思想活躍但戰亂頻發的時代,繁雜無序的工作事務,平淡乏味的家庭生活,這一切讓他的內心充滿了一種無法言說的疲倦與煩惱。文中寫到:“墻外馬路上孩子們的歡笑,已經聽不見了;妻在屋里拍著閏兒,迷迷糊糊的唱著眠歌”。這種平淡無奇的現實生活不能滿足自己的精神需求,腦海里便浮出“日日走過的荷塘”,于是就“悄悄地披了大衫,帶上門出去。”試想一個平庸之人,過上收入穩定、家庭幸福的生活應是滿足了。但對于朱自清,平淡的現實生活很容易使其失去情趣,因而他就以逃避平庸的方式對抗現實,追求真正的、超然的自我,自然就心儀另一個世界,向往另一種生活。這也就是作者戀戀不忘荷塘,進而就陶醉于荷香月色中的最初動因。那么,讓作者心曠神怡、脫塵忘俗的地方在哪兒?那就在以荷塘為物質載體的審美世界中。
二、恬靜的審美世界
朱自清先生的審美世界充滿了寧靜、恬淡的情趣。作為審美世界,要有審美主體(即審美者)、審美客體(即審美對象)和主體間性(即審美主客體之間的審美關系)。因而在審美世界中,審美客體已不是純粹的、無生命的客觀事物,而是在審美主體觀照下的有靈性的審美對象;審美主體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個體存在,而是被審美客體感染下的物我合一的審美體驗者(4)。在《荷塘月色》中,“曲曲折折的荷塘”、“田田的葉子”、“零星的”“白花”、“如流水一般”的月光,這一切在多愁善感的、“愛群居也愛獨處”的“我”的感情投射下,生成了一個即實在又神秘的審美境界。作者的心身完全投入其中,陶醉在“像亭亭的舞女的裙”般的荷葉、如“剛出浴的美人”般的荷花中,主客相容、物我相忘。作者的靈魂得到愉悅、升華和凈化。正如文中寫道到,“路上只我一個人,背著手踱著。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個世界里。”當然,作者也清醒地意識到:“這時候最熱鬧的,要數樹上的蟬聲與水里的蛙聲;但熱鬧是它們的,我什么也沒有”。隨著審美客體的退出,原先如醉如癡的審美體驗也會隨之消褪,“我”只能在《采蓮賦》與《西洲曲》的意境中寄托自己的一廂情愫。
三、古典的幻象世界
荷香月色的審美世界隨著“我”走出荷塘而戛然終止。為了填補由于審美世界的消失而給心靈帶來的空虛,為了撫慰由于審美情感的消褪而對心靈的微創,作者就“忽然想起采蓮的事情了”,只好把心思投入到古典的幻象世界中,在梁元帝的《采蓮賦》與南朝民歌《西洲曲》的意境中又找到了心靈的依托和審美的延展。“采蓮南塘秋”的荷塘比“日日走過的荷塘”更具魅力,因為有“妖童媛女”的活潑與妖艷;她們“纖腰束素”的裝扮、“恐沾裳而淺笑”的清純活潑,又讓作者暫時忘卻了心中的“不寧靜”。畢竟,作者更欣喜的是《西洲曲》中的那位淑女型的多情女子。文中雖然只引用了四句詩,但卻為我們留下了廣闊的藝術想象空間,我們一定會聯想到“海水夢悠悠,君愁我亦愁。南風知我意,吹夢到西洲”的纏綿。這樣,作者委婉含蓄地透露出了自己靈魂深處的秘密:夢想遙不可及,夢中的荷塘比“西洲”更遙遠;因為這是一個純幻覺的世界,一切審美客體都是幻象。這些幻象雖然更具古典神秘的特質,但終究是虛幻的,就如浮士德追求海倫終歸幻滅一樣。人盡管可以體驗審美世界的愉悅,可以陶醉于幻象世界的縹緲,但最終還是要回到“頗不寧靜”的紛繁的現實世界,即使作家亦是如此。正如錢理群所言,“(朱自清)寫作態度嚴肅不茍,始終執著地表現人生。”(5)與徐志摩相比,朱自清先生的現實與深刻之處便在于此。《荷塘月色》的結尾就透露出了作者的這種嚴肅與務實的情懷。
總之,《荷塘月色》中的“三個世界”是相互聯系的,它們之間由作者的思緒一以貫之。作者以現實世界為落腳點,其紛繁與平庸促進他走向自己的審美世界。在情景交融之中,心靈得到了真正的審美愉悅和放松,如癡如醉的審美體驗使塵世的疲倦洗滌一凈。但是,隨著作者走出荷塘,荷香月色的審美情趣必然要消褪,于是其心靈又就進入了一個蘊藏于古典詩文中的幻象世界。因此,“三個世界”是作者的漫步荷塘的三個階段,也是思緒連貫的三個心理過程,而每個世界有自己獨特的藝術價值和審美特質。
注釋:
(1)雷達主編《中國現當代文學通史》甘肅人民出版社,2006.8.第197頁。
(2)(5)錢理群主編《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7.第154頁。
(3)李澤厚《美學三書》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10.第290頁。
(4)朱立元主編《美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第95頁。
參考文獻:
[1]雷達.中國現當代文學通史[M].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6.8.
[2]錢理群.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7.
[3]李澤厚.美學三書[M].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10.
[4]朱立元.美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