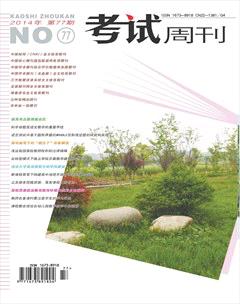從理論角度論述英語傳統語法教學的普適性
蘭莉鵬
摘 要: 近年來,隨著西方外語教學理論的不斷引入,我國的英語教學也由傳統的以語法翻譯法為主的教學模式,轉向了以強調交際能力為主導的交際型教學法或任務型教學法。但事實證明,傳統的語法翻譯法在我國的英語教學中依然占據主導地位,這是由于傳統語法教學的安排體現了語言學習的順序性和階段性,這符合學生學習語言的心理認知水平。本文旨在從多維模式理論、強化理論、輸入假說、標記性區分假設及注意的選擇性等理論出發,通過傳統語法翻譯法的實施細節即從語法規則的講述與練習的角度闡明傳統語法教學的普適性。
關鍵詞: 英語傳統語法教學 理論角度 普適性
傳統語法教學在我國長期占據主導地位,論述和評判這個領域的文章數不勝數。羅立勝、石曉佳(2004)對語法翻譯法的歷史進行了回顧,指出了語法翻譯法存在的問題和自身特點并對其進行了展望。作者認為這種方法在新的語言研究理論和方法的推動下將不斷調整并預言該方法一定會長久地根植于外語教學之中。王東波(2004)介紹了語法翻譯法的內涵,分析了其特征,總結了其優點。樂學玲(2010)肯定了語法和語法教學的重要性,指出了不能因為語法教學的低效性而懷疑語法本身,要從語法改革的新視角探討語法和語法教學問題。高建平(2010)在文章中分析了語法翻譯法在教學中的作用,指出語法翻譯法能夠促進學生有效學習。戴煒棟、陳莉萍(2005)通過對二語語法教學的重要性在理論上和認知上的梳理,指出當今二語習得的研究者又開始格外關注該方法。以上文章都是在宏觀的理論層面對語法翻譯法進行說明和闡釋,沒有說明在具體實施語法翻譯法時為什么教師每次在對規則講授后便對其進行練習,本文從多維模式理論、強化理論、輸入假說、標記性區分假設及注意的選擇性理論等角度說明此問題。
回顧我國英語課堂的教學模式,教師大都是在教學大綱和教學目標的指導和安排下進行英語教學。教師通常的做法是:教師在講授一項語法規則后便用各種手段對該項規則進行訓練,達到使學生掌握的目的。語法規則的講解則是由淺入深、由易到難、循序漸進、有條不紊的。教學實踐也表明這樣的教學模式是適合中國本土的教育模式的。追根溯源,這種方法源起于18世紀末和19世紀中期歐洲在教授拉丁語和希臘語所使用的方法即語法翻譯法。該方法以翻譯和語法學習為主,一節課由介紹語法規則、學習詞匯表和翻譯練習組成,其目的是培養學生閱讀外國文學作品和模仿范文進行寫作的能力。時至今日,盡管情景和交際教學法在英語教學中被推崇備至,傳統的語法教學模式歷經時代變遷依然經久不衰并且廣為傳用,一定有其優勢和普適性。
1.語法學習的順序性——多維模式理論(the Multidimensional Model)
Manfred Pienemann(1984)等人基于對外國人習得德語的研究,發現了外國人德語語序的習得情況,進而提出多維模式(the Multidimensional Model)。這個理論一般是指任何沿著兩個或多個而不是單一方向發展或學習的模式。Pienemann指出了第二語言習得的多維模式即有些語言特征的習得是按照心理語言加工限制所限定的自然順序進行,而其他更多的則是由學習者進行選擇:根據是定向于正確和規定性標準還是定向于流利性標準而定。該理論提供了兩個發展軸線即“發展順序軸線”(developmental axis)和“學習者語言變異軸線”(variational axis)。這里的“發展順序軸線”強調學習者在學習語法結構(grammatical structures)時表現出語法學習的排序(sequence),即SVO(主謂賓)、ADV(adverb preposing副詞前置)、SEP(verb separation動詞分離)、INV(inversion倒裝)及V-END結構(verb-end動詞結尾)(見table-1)。Pienemann的實驗結果表明來自不同國家的學習者,無論是大人還是小孩,都會遵循這五個階段的發展順序,這種發展順序不可改變。
Table 1
Sequence of acquisition German word order rules (based on Pienemann, Johoston, and Brindley 1988) Ellis: 104
Pienemann后來在實驗中發現,一個處于副詞前置即第二階段的女孩Teresa,如果跳過動詞分離的第三階段而直接給她講主謂倒裝即第四階段,則沒有任何效果。相反,一個中介語水平已經達到第四階段的叫Giovanni的男生,學了第四階段的主謂倒裝后便能運用自如。這說明學習者不能跳過一個階段而習得下一個階段的知識。據此Pienemann(1985:37)提出了可教性假設(Teachability Hypothsis),即“只有當學習者中介語發展到可以在自然環境中習得某種規則時,這種規則才能在教學中習得”。如果學習者的中介語水平沒有發展到那個階段,則不會取得教學效果。這就說明語法教學的前提就是看學生的中介語水平, Johnston和Pinemann(1986)也測試出了外語學習者英語習得順序的模式(見Table 2)。所以,教師在教授語法項目時,要了解學生中介語的發展水平,循序漸進。
Table 2
Generalized pattern of acquisition for L2 English (based on information provided in Johnston and Pinemann 1986) Ellis: 105
在以英語為第二語言的研究中也發現盡管學習者的年齡和母語不同,但他們在習得某些特定的一系列詞素方面表現出一致的習得順序(Dulay&Burt 1973)。第二語言學習者在習得某些語法形式時也表現出一致的習得順序,而且某些習得順序與所觀察到第一語言習得順序相似(Schumann 1979)。我國的外語教學在初高中階段,英語課堂的語法教學均體現出這種順序性,語法項目的編寫也都是由簡單到復雜。在每個語法項目下,又有很多的語法規則,教師都是在以語法項目為基礎的前提下,講解規則,然后通過練習達到使學生掌握的目的。可見,多維模式理論為這種教學提供了理論支撐。
2.語法規則的具體實施及其合理性
了解了語言習得要遵循一定的習得的順序,筆者從行為主義的強化論、輸入假說、標記性區分假設及注意的選擇性三個角度闡釋具體語法規則的實施及其合理性。
2.1行為主義的強化論(reinforcement theory)
上世紀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初期,Skinner(1957)等人認為解釋語言學習的最合適的模式就是刺激—反應論(stimulus—response theory),特別是工具型的條件反射論。該理論認為兒童學話無非就是對環境或是成人的話語做出合適的反應。如果反應是正確的,成人就會給予物質的或口頭的鼓勵,把它強化下來,由此形成語言習慣。在“強化”論者看來,語言能力是由一些不相聯系的言語行為單位組成的,必須分別學習。在教學當中,學習者通過不斷接受外界刺激,包括語言形式和結構,不斷的模仿,最后內化成學習者的知識。教學中的反饋是指學習者得到的來自教師或其他學習者的關于某一學習任務是否成功的評論或信息。傳統語法教學則體現出這種刺激—反應的模式。教師向學生講解一個語法規則,這就被視為是一種刺激,如果是教師一味地講解,則僅僅是刺激在起作用,刺激會產生怎樣的效果不得而知,因此要不斷對刺激形成反饋,也就是教師在教授了一個語法規則之后,立即通過練習的手段對學生進行訓練,形成反饋,促進學生習得。
2.2輸入假說(input hypothesis)
輸入即在語言學習中,學習者聽到或接收到的并能作為其學習對象的語言;二語或外語的學習者需要對對輸入或吸收做出區分。吸收的語言是指真正有助于學習者學習的語言,學習者聽到的語言(即輸入的語言)中,有些太難或太快了,學習者不能理解,因而在學習中無法運用(即不能成為吸收的語言)。Krashen(1981;1985;1989)提出的輸入假說,認為在第二語言或外語學習中,要使語言習得得以發生,有必要向學習者輸入稍高于其現有語言能力的語言項目。學習者利用情境提示理解這些語言,最后,很自然地形成產生語言的能力,而無需直接傳授。這個假說強調了環境的重要性。可是在我國,傳統的語法教學以教師講解為主,即老師以教授語法規則為核心,教師向學生傳授知識,并且實際情況是一個教師要面對幾十個學生。Krashen提出的輸入假說,在我國實施起來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其思想,要向學生輸入稍高于其目前水平的語言項目對二語教學則有積極的指導意義。
Long針對Krashen的輸入假說也提出自己的觀點。Long認為,當交際雙方在交流中出現了問題,即無法使交際很好地進行下去的時候,就需要一種解決問題的手段,也就是在意義協商中要有修飾性的互動協商(modified interaction),即當一方聽不懂時,另一方就重新構建自己的話語和用詞。Long(1985a;1991)認為正是這些互動協商在課堂上能為學生提供大量的可理解的輸入(comprehensible input),之后他又用證據表明這種可理解性的語言輸入可以促進習得。
在課堂教學模式下,老師在向學生講授語法規則時,這時就是對學生的一種刺激,并且由于學生之前沒有接受過這樣的語言項目和語法規則,教師對學生的輸入就是稍高于學生目前的知識水平,那么學生對其的接受和領悟程度就是要通過練習和學生形成一種反饋,通過反饋,教師可以很好地了解學生的掌握程度,調整自己的話語和用詞,向學生提供大量可理解性輸入,促進學生對語法規則的掌握。相反,如果教師只是一味地講解規則,而沒有和學生之間形成反饋和提供可理解性的輸入,則將會對二語教學產生不利影響。
2.3標記性區分假說(markedness difference hypothesis)
Eckman(1977)提出了標記性區分假設(markedness difference hypothesis)。這一理論是指在語言內部和跨語言之間,某些語言成分可被視為無標記的,亦即:簡單、核心或者原型的成分;而另外一些可別被視為有標記的,亦即:復雜、邊緣或者例外的成分。在二語學習和外語學習中,標記現象有時被作為習得順序或難度方向的預測計。根據這種觀點,如果目的語言包含有標記的結構,學習起來就困難。如果目的語言是無標記的,就不會有或者幾乎沒有學習難度——即使它們并不存在于學習者本族語中。根據本族語和目的語的語言特征可以對學習者可能遇到的難點進行預測和安排。在語法教學中,諸如非謂語動詞、虛擬語氣、主謂一致都是教學難點和學習者難于掌握的語法項目,這些大的語法項目都是又被分成了若干個語言小項目展開的,每條語法項目下又蘊含著若干規則,根據Pienemann對于英語學習順序的研究,學生通常會先對形式有所了解,所以教師在具體講解時也是先告訴學生某個語法項目的形式,進而對規則進行講解,然后對此形式和規則進行反復操練。
2.4選擇性注意假說(selective attention)
Lightbown(1985a)認為課堂教學的引導可以促進習得的發生,這并不意味著這種正式的引導可以使得學生立即對新的語言形式內化,而是為學生提供了一些可以連接其他語言形式的途徑。Gass(1991:137)認為這種引導可以激發學生在最初的二語習得階段就對語法結構進行重新建構。這是由于早在1979年,Seliger(1979:368)就指出讓學習者的注意力要分配在一些真實的語言概念屬性上,因為這些語言概念會應用在以后的語言輸出中。Seliger(1979)還指出,學習者在老師的引導下即使有意識地學習了某些語法規則,對于這些規則的掌握也會產生一些差強人意的地方。這就表明,教師在對語法規則進行講解后,如果沒有及時進行練習,則學生對這種語法規則的掌握將會千差萬別,這樣將非常不利于二語學習。
鑒于以上的理論,在英語教學當中,教師對語法規則的講解是非常有必要的,并且這種語法規則的講解就如Seliger所講的要讓學生對某種屬性產生注意力上的分配。教師如果在講解了某一語法規則后能夠立即對這一規則進行操練,則會達到對其強化的目的。相反,教師如果不對其操練,而直接講述其他語法規則或語言屬性,那么學生的注意力將不知道該如何進行選擇性的分配,這就不利于學生的學習和教師的繼續引導。假設教師一次輸入了多種語言形式,學生也會根據自己的選擇有所取舍,也不可能注意到所有形式和語法項目。這個理論表明如果教師在講授了一個語法規則后不斷練習,不斷重復,則會幫助學生注意該規則和該形式,有利于學生的學習和掌握,從這個角度講,在講授一個規則后對其進行練習非常有必要。
3.對教學的啟示
中國的國情決定了中國教育的模式。自上世紀70年代交際法傳入中國后,我國英語教學一直沿襲的語法翻譯法受到很大沖擊,但是中國的語言學習環境決定了交際教學法并不完全適合中國國情,語法翻譯法仍具有普適性和價值。事實上,中國的英語課堂也仍在采用這種傳統的教學方法即在一個語法項目下對規則進行講述,并且立即對其進行練習。隨著學生認知水平的提高,教師對這一語法項目的講解也在逐漸細化和系統化。許多教師一直在使用這樣一種教學風格和模式。語法是一個知識系統,學生通過老師對某一規則的講解注意到了一種基本形式,這種規則被學生掌握需要一個建構和再建構的過程。多維模式理論、強化理論、輸入假說、標記性區分假設及注意的選擇性理論幫助我們了解語言學習自身呈現出的特點和特性,這使教學得到合理安排。在教學中,對語法項目下的語法規則進行講解和練習將會提高學生對該種規則的注意程度,促進學生對這種規則的掌握及今后教學活動的開展。
參考文獻:
[1]戴煒棟,陳莉萍.二語語法教學理論綜述[J].外語教學與研究,2005(2):92-99.
[2]高建平.語法翻譯法在外語學習中的作用[J].楚雄師范學院學報,2010(1):86-87.
[3]樂學玲.英語語法及語法教學新視角[J].中國成人教育,2010(2):125-126.
[4]劉東紅.多維模式的多維分析[J].外語教學,2003(5):69-72.
[5]羅立勝,石曉佳.語法翻譯教學法的歷史回顧、現狀及展望[J].外語教學,2004(1):84-86.
[6]王東波.論語法翻譯法的適用性及其存在價值[J].山東大學學報,2004(4):52-55.
[7]Dulay,H.C.& Burt,M.K.Should we teach children syntax?[J].Language Learning,1973.23:245-258.
[8]Eckman,F.‘Markedness and the contrastive analysis hypothesis.[J].Language Learning,1977,27:315-330.
[9]Gass,S.& E.Varonis.‘Miscommunication in nonnative speaker discourse in Coupland et al.(eds.),1991.
[10]Krashen,S.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M]Oxford:Pergamon,1981.
[11]Krashen,S.The Input Hypothesis:Issues and Implications[M].London:Longman,1985.
[12]Krashen,S.‘We acquire vocabulary and spelling by reading:additional evidence for the input hypothesis[J].Modern Language Journal,1989,73:440-64.
[13]Lightbown,P.1985a.‘Can language acquisition be altered by instruction? in Hyltenstam and Pienmann(eds.),1985.
[14]Long,M.1985a.‘Input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tion theory in Gass and Madden (eds.),1985.
[15]Long,M.‘Focus on form:a design feature in language teaching methodology in de Bot et al.(eds.),1991.
[16]Pienemann,M.‘Learnability and syllabus construction in Hyltenstam and Piennemann(eds.),1985.
[17]Piennemann,M.Psychological constraints on the teachability of language[J].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1984.6:186-214.
[18]Schmann,J.The acquisition of English negation by speakers of Spanish:A review if the literature[A].In R.Andersen(ed).The Acquisition and Use of Spanish and English as First and Second Languages[C].Washing DC:TESOL,1979:1-32.
[19]Schmidt,R.W.The role of consciousnes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J].Applied Linguistics,1990.11/2:129-158.
[20]Schmidt,R.W.Attention[A].In P.Robinson (ed.).Cogni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Instruction[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21]Seliger,H.‘On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language rules in language teaching[J]TESOL QUARTERLY,1979,13:359-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