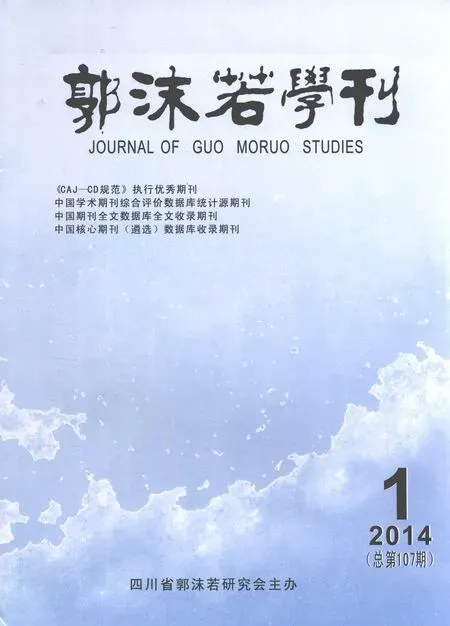魔鏡畫家埃舍爾的啟示
王 火
幾年前,在友人處見到一本國外雜志,其中有幾幅飲譽全歐的具有獨特風格的荷蘭現代畫家莫里茨·柯內里新·埃舍爾(1898-1972)的作品,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一幅畫名叫《蕩漾的水面》,作于1950年,利用的是平面反映的原理,畫面顯得極其自然:一棵冬天掉光了葉子的樹倒映在清澈的水面,背后是一輪蒼白無力的太陽的倒映。有兩顆水珠滴在光滑的水面,蕩起波紋,它誘發人們對水面的立體想象,畫面本是靜止的,但兩滴水珠喚醒了這一切。這幅畫掛起來是很美的。
更有一幅就是他的名作《魔鏡》。1946年,畫家創作了這幅單一的變形轉化循環的石版畫,展示了平面與立體空間的循環。畫面是這樣的:中央有一面直立在架上的魔鏡,左右側各有一個圓球。圍繞圓球各有一群長翅膀的小狗在行走,增加了魔幻的意味。鏡中反映著行動的狗和靜止的球。鏡面上的圖案逐漸長出鏡面,隨后步入空間。鏡子的兩邊出現同樣的情況,走到中途,狗變成雙縱隊,兩個相反方向的狗形成規律性的平面分割圖案,由白狗和黑狗構成從空間到地面的造型,畫面好像只有那兩個球是真的,因為觀者還能看到一個球在鏡子里反映出的一部分。畫是什么意思呢?我說不出,但我卻凝視著它難以舍棄,覺得它將魔幻的鏡子這一主題用畫作了表述,而且,確是一幅令人贊嘆的藝術品,平面上的空間造型利用夸張的手法使觀者暫時忘卻平面而被其魔術般的造型深深打動。埃舍爾運用獨特的技法,獨特的畫面構圖,展示了一種動態平衡。人們認為他“通過觀察結果,最終使藝術步入數學領域”。人說他的《魔鏡》這幅畫,“乍一看如一個亂線團,繼而又仿佛是在說一個故事,這個故事首尾交融在一起了,它誕生于鏡面”。是他利用反映原理在創作上邁出更新一步。這里不光是鏡子反映出來的畫面,更有誕生于鏡面而步入真實空間的聯想。是一種耐“咀嚼”的畫。
M.C.埃舍爾真是一位魔鏡似的畫家。但他也是一個在中國被忽略了的藝術大師。當人們關注著歐美古典主義、現實主義、現代主義直至后現代主義的所有大師時,卻似乎忽略了他。
隨著改革開放,我們需要不斷打開眼界,了解國外一切對我們有益,有助于我們開闊眼界和思路的文化成果。埃舍爾和他的作品理應屬于這一類。
埃舍爾是一個不肯循規蹈矩的藝術家。本來,藝術家為什么一定要在創作上循規蹈矩重復前人呢?我是十分欣賞埃舍爾這一點的。他出名以前,并沒有人收藏他的作品,藝術評論家也不知如何去評價他的作品。但他鍥爾不舍,時過境遷,現在對埃舍爾作品入迷的觀眾越來越多。在1937年以前,他的作品總的說來是表現出純粹的繪畫性的。像他的木刻《女人與花》(1925)、石版畫《父親》(1935)、版畫《手與球面鏡》(1935)、版畫《靜物與街道》(1937)……那些充滿詩情畫意的風景版畫,那些富于表現力的肖像,已足夠為一個藝術家寫評傳了。那些畫都是很好賣的。他是一個熟練地掌握并杰出地運用技巧的畫家(他指責大部分現代藝術家缺乏技巧,只是亂涂一氣;對有些抽象藝術,他認為沒有靈魂、蒼白無力)。但1937年后,這種純繪畫性的創作形式不再是埃舍爾的主要研究方向。他被均衡的、有規律的數學結構及無窮無盡的結構可能性吸引。他將三維空間搬上平面,踏進了一條前人從未發現的小徑。誰也不會認為每個畫家都應走他這條路,但誰都會感到一個藝術家有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的可貴與可羨。他堅持著為自己著迷的藝術道路貢獻智慧。作為一個藝術家,為了作出獨特的貢獻,不去理會世俗名利,也不趨風尚趕時髦,他這種獨辟蹊徑,想為真正的藝術獻身的愿望和有所發現和創造的精神是很可敬的。藝術批評家格萊維薩蒂(G.H.SGravesande)曾說:“關于埃舍爾的作品,總有這樣一個問題縈繞我的腦際:他最近的作品是否該算在美術范疇之內,盡管這些精致的東西同樣能打動我。”
確實,埃舍爾1938年創作的《晝與夜》、1948年的《露珠》、1951年的《魔梯旁》等名作,要立刻完全理解它的含意也許很難。但它們不但精致,而且是極美極能打動人的,說它們“不屬于美術范疇之內”,恐怕只能是一種偏見。以《晝與夜》來說,被譽為是“最令人驚嘆的一幅作品”。畫面的中央是平面填充,但這卻不是《晝與夜》的終點,其終點在畫面下方中部。這里是些菱形田地,我們的視線離開田地自動上升,田塊變形得很快,剛進了兩級已成了白色的飛雁,沉重的大地突然飄升到了天穹,白色的大雁越過碼頭邊的小村落向黑夜的深處飛去。從左到右,白晝逐漸變成黑夜,從上到下,大地變成了天空的生靈,這幅畫藝術家通過自己的幻覺達到了他的理想所在,構思是十分獨特的。
時間幫助人們認識和接受新的東西,這已成為顛撲不破的真理。埃舍爾大約在1954年左右已聲名大振,直到現在經久不衰。海牙市為他舉辦隆重的作品展,參觀的人數不亞于當年為倫勃朗舉辦紀念展的人數。1970年,荷蘭外交部專門將埃舍爾及其作品攝成電影。作曲家尤利安·安德里森(JurriaanAndriessen)從埃舍爾作品中獲得靈感創作的現代音樂作品,演出時場場滿座。今天,埃舍爾作為版畫家比任何一位同行更有名望。
超現實主義畫家創造了謎一般的世界,觀眾若不被其迷惑,畫家就算沒有達到目的。埃舍爾的作品中也有謎,但同時也有答案——它藏得隱蔽,制造謎并不是他的宗旨,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被人稱贊,讓人迷惑,但同時又能悟出謎之所在。埃舍爾的作品都是一絲不茍的,他自己說過:“我的創作都是在傳達我的發現。”埃舍爾的作品都有他自己的發現,因而都能給人一種陌生感。即使在常情之中,乍一看,觀者無不驚訝。他不走人家的老路,不用自己的老套,獨自迷醉于自己在探索追求的美的世界,他應算是一位真正的獨特的美術家。他形成了自己的流派,誰也會在世界美術殿堂中,發現他那些參與陳列的使人傾倒的豐碩成果。
國外,有人認為哥德爾(Godel)的數學原理,埃舍爾(Escher)的畫,巴赫(Bach)的曲,揭示了數學邏輯、繪畫、音樂等領域之間的深刻的共同規律。《科學美國人》游戲數學專欄專家道格拉斯·霍夫施塔特說:哥德爾的數學原理、埃舍爾的畫、巴赫的曲,美妙地編織了一條光燦燦的金帶——GEB。他們用這條永恒的金帶,把這些表面大相徑庭的領域貫穿一起,構成奧秘的思維,人工智能和生命遺傳機制的基礎。
埃舍爾曾說:“但愿你們知道,我在黑夜深處看到的……我常常很痛苦,因為我不能表現這種黑暗。每一幅畫與黑暗相比都微不足道,而它卻從未被表現過一絲一毫,它們會有什么樣的效果呢?”黑夜誰都用黑色在畫,他卻有這種獨到的“痛苦”。
其實,埃舍爾那些富于想象力的畫已經夠在一定程度上滿足我們想象的愿望了。不僅表現黑暗,而且表現光明,在他的名作《晝與夜》與《星體》中人們就會看到這一點。
我在從事文學創作中,常深切感到文字的蒼白、平淡與無能。文字表達思想感情,表達色、香、味,表達音樂旋律,表達動態……總是那么受到局限,那么力不從心。但文字又每每與音樂、繪畫藝術等等領域有著密切的關聯。有時一種感情用音樂表達比文字好得多,有時一種意境和氣氛用繪畫表達比文字也美得多。如何使文字的表達與傳導有所突破,從音樂、繪畫等等藝術上得到補充,是我常常思索并試探的問題。思想上的禁錮與束縛少一些,活躍與放開一些,推進藝術思維與在文字上的實踐也每每能好一些。埃舍爾涉足數學等領域對待藝術創作的思想和他那些破除陳規尋找新的表現方式的不同于一般的作品也正在這方面對我有喜出望外的啟示。
埃舍爾說過:“當我創作一幅作品時,我認為這是世界上最美的東西了,它果真獲得成功的話,我就會在傍晚坐在它面前向它傾述我對它的愛情,這種愛情遠遠超過對人的愛情……”這一位將畢生傾注在藝術追求上的大畫家的心聲,表露得何等令人心醉而且感動啊!據說埃舍爾曾計劃創作一幅了不起的畫。那是根據一個流傳的童話故事作題材的。故事中有一道“寶門”,它孤零零地立在綠樹點綴其間的草原上,附近有肥沃的丘陵綿延。這是一道莫名其妙的門,既非出口,也非進口,只需從它中間過一下,奇跡就出現,門開時,里面閃出霞光萬道,眼前一派閃爍:那金的山、寶石般的河流和種種奇花異草,令人目不暇接。這樣一個“寶門”入畫當然是非常美而且極富幻想的。如果畫出來了,勢必會與《魔鏡》一樣出名。本來,要求不高的畫家用蹩腳的圖解式的畫來表現也是不難的,但要有奇妙的構思和別出心裁的畫面就難了。可惜埃舍爾從1963年開始構思,經歷多年,卻始終未能畫成。人們認為可能只有埃舍爾才會為我們創作這樣難的一幅高超美術作品,用他精湛的技巧,如反映透視平面分割和向無止境的童話世界推進。只是,太可惜了!他卻沒有畫成。也許,過多的思索和過高的要求,造成了流產吧?真是遺憾的事。
說來也許你不相信,在我創作過程中,我常愛翻閱世界藝術大師們的繪畫作品,達·芬奇、拉斐爾、米開朗琪羅、提香、丟勒、魯本新、貝尼尼、弗美爾、倫勃朗、雷諾茲、戈雅、大衛、安格爾、米勒、列賓、馬奈、高更、莫羅等等的作品和畫冊,我都愛仔細一遍遍地翻閱欣賞,有時甚至到圖書館去專門借閱。我寫的是小說,但看的是繪畫,是不是有點風馬牛不相及?不,從我的體驗,受益很大。藝術大師們的繪畫作品本身,未必會對我的寫作有多大的關系(雖然我在有些作品如《戰爭和人》、《隱私權》、《心上的海潮》、《濃霧中的火光》等內也常談到繪畫),但從那些珍品體現出的創造性、想象力,那些珍品迸射出的奇特的美韻與詩意,放蕩與開拓,浪漫與怪誕,既有助于我開闊思路,啟動開創,也有助于我拓展眼界。那些在文學藝術上共通的屬于九九歸一的創作要素,或者是各不相同的別出心裁的創作風格與技巧,打破固有程式的勇氣,超凡脫俗的觀察體昧與思索,寓情寄意的造型,每每會使我的筆由笨拙變為神奇,由滯澀變為流暢,由暗淡變為多彩,由呆板變為多姿,我思想會開竅的!例如,我并不喜歡活躍于國際藝壇的十分怪異的英國現代藝術家培根·法蘭西斯(Bacon.Francis 1910—),他畫的人物太丑陋了!但他的“獨特”卻吸引了我,我也并不欣賞多少帶有玩世消閑意味的年輕一代英國藝術家大衛·霍克尼(David Hockney1937—),他是今天舉世公認、卓有成就的蝕刻和制圖藝術家。但他的拼貼技術和錯位排列的藝術特征,使我產生的幻覺感受非同凡響,也使我發現在同一個領域內,開拓的天地廣闊無垠。比利時的兩位在國際畫壇聲譽日隆的超現實主義畫家 K.馬格里特(1898-1967)與 P.德爾沃(1897-1994),都有其獨特個性。馬格里特善于畫出夢一般的景象,看他的畫就像讀詩(埃舍爾很欣賞他的作品),德爾沃是人體藝術史上立下豐碑的大師之一,他的繪畫世界的主角是通常處于情愛氣氛中的女性。人說他畫的女人是“美的符號,詩的幻覺,光的化身”。也有人說,看馬格里特的畫有些像讀卡夫卡的作品,讀德爾沃的畫則有些像讀普魯斯特的作品。總之,藝術不論在西方或在東方,達到最高境界時,總是相通的,我看到大師之為大師,全賴他們創造的個性,他們實際都注重于提出新問題而非重復老問題,不倦、不斷創新,讓自己區別于別人,努力去尋求美的表達,他們首先也都有其民族風格和個人特色。即使我不太喜歡其中有的人的過于怪誕與荒謬,但他們在藝術追求上的造詣和成就,對我都有震動。
從這使我想到:藝術的創作是無止境的。我們需要新,需要深,需要脫俗,深入在生活中的用“藝術之眼”可以得到的應當表現成為貢獻給人民的藝術品的一切,應當用不斷革新、不斷進步的主題和技巧來豐富、表現,這關鍵在于藝術家的努力與探索,因而這也需要我們面向世界,放開視野,開闊思路,不排斥任何一位對人類文化寶庫作出積儲的大師,探討吸收他們有益于我們的成分。時下,習慣于“老子天下第一”,習慣于人云亦云,習慣于墨守成規,習慣于走人們走過的老路,不太講究表現技巧的畫家與作家,從埃舍爾等的創作中可以得益之處應當是不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