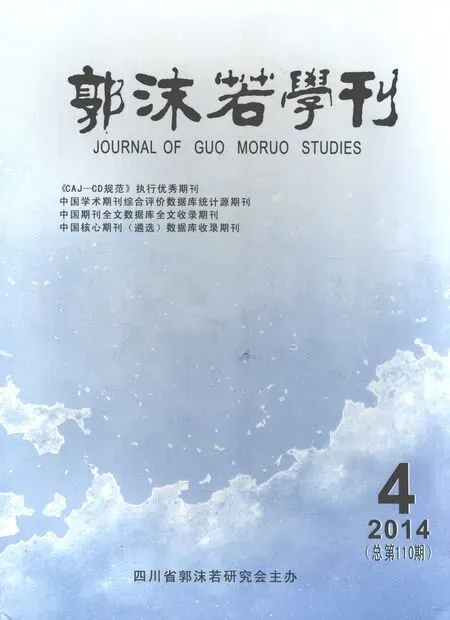郭沫若對老子和《道德經》評價的幾個問題
楊勝寬
(樂山師范學院,四川樂山614000)
郭沫若對老子和《道德經》評價的幾個問題
楊勝寬
(樂山師范學院,四川樂山614000)
在20世紀20年代初至40年代中葉的二十多年研究歷程中,郭沫若對老子和《道德經》的認識與評價發生了與時俱進的變化。大體上講,其受泛神論思想支配的20年代,對老子的思想評價最高,視之為古代思想史發展的革命先驅者;30年代注重社會形態與宇宙觀念的發展演變研究,肯定老子“道”的概念具有形上學的本體意義,老子的地位未變,但已經注意到其思想的局限性及負面成分;40年代用“人民本位”的尺度衡量諸子學說,對老子思想的估價大為降低,總體顯示負面評價為主。《道德經》則是因老子的出生年代及其遺說的保留程度等學術問題爭論引出的相關話題,郭沫若認為此書系黃老學派傳人之一的環淵筆錄潤色老子遺說而成,其中包含了大量發揮老子思想旨意的成分。
郭沫若;老子;《道德經》;“道”本體;黃老學派
老子作為道家文化的創始人,對中國數千年逐步形成的儒道互補思想文化發展格局,具有極其廣泛和深遠的影響。郭沫若從讀書發蒙之初,最早閱讀的古代文化經典中,除了《三字經》《唐詩三百首》及《四書》《五經》之類的啟蒙基礎讀物,憑個人愛好興趣選擇的,就是十三四歲開始閱讀的《莊子》《道德經》等道家經典。由此可以看出,早年郭沫若就對道家文化發生了解的興趣,并較早形成了對道家文化創始人老子的基本認識。迄今可見郭沫若最早的學術性論文,是1921年發表于《學藝》第3卷第1號的《我國思想史上之澎湃城》,在這篇沒有寫完的長文中,其提綱的下篇首論“再生時代之先驅者老聃”,雖然不能確知作者如何論述老聃為“再生時代”的到來作出了怎樣的劃時代貢獻,但至少可以看出此時的郭沫若心目中,認為老子在中國古代思想史發展上,起了革命性的重要作用,具有不可忽視的地位。
從20世紀20年代初至40年代中葉的二十多年時間里,中國的社會發生著歷史性巨變,郭沫若的人生也在這種驚天動地的社會變局中跌宕起伏、驚險叢生,雖然在這段漫長的人生歷程中,郭沫若從未放棄過對中國古代文化的關注、研究與思考,但世易時移及由此引起的郭沫若自身思想觀念與學術觀念的變化,不能不導致其對老子和《道德經》在認識與評價上產生相應變化。遵循這種變化軌跡,我們可以看出郭沫若各個時期對老子和《道德經》評價觀點的不同。
一、1923:思想家老聃評價與文學形象老聃塑造所體現的強烈反差
郭沫若對老子的學理性認識與評價,大致應該從其1922年末至1923年初撰寫的《中國文化之傳統精神》一文開始。據將此文譯成中文的成仿吾在民國十二年五月十四日所寫的“譯后附識”稱,郭沫若的文章是專門為日本大阪《朝日新聞》的1923年新年特號而寫的,目的之一是向日本讀者介紹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要義與精華,所以在這篇不長的專文中,郭沫若著重介紹了以老子、孔子思想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傳統基本精神,他把這種精神主要歸納為兩點:即“把一切的存在看做動的實在之表現”;“把一切的事業由自我的完成出發”。他認為這是在老子、孔子思想中體現得最突出、最鮮明和最有代表性的古代中國文化固有的傳統精神。
文章在論述老子思想內涵及其革命性進步意義時指出:
到了周之中葉……革命思想家老子便如太陽一般升出。他把三代的迷信思想全盤破壞,極端詛咒他律的倫理說,把人格神的觀念連根都拔出來,而代之以‘道’之觀念。他說:‘道’先天地而混然存在,目不能見,耳不能聞,超越一切的感覺而絕無名言,如‘無’,而實非無。這‘道’便是宇宙之實在。宇宙萬有的生滅,皆是‘道’的作用之表現,道是無目的地在作用著。……
此時的郭沫若相信泛神論。他認為,夏、商、周(西周)三代迷信天意和鬼神,統治者有意將其加以神化,為其君權神授的統治尋找合理性根據,達到讓天下百姓順從這種統治秩序的目的。郭沫若把這個人格神迷信觀念盛行的時代,稱為中國思想史上的第一個“黑暗時代”。而老子用“道”的觀念取代“神”的觀念,提出“道”是先于天地、無所不在的宇宙之實在,萬物的生滅,宇宙的變化,都是“道”作用的結果。老子“道”的觀念,其革命性意義在于破除了三代千余年一直奉行的迷信天意鬼神的思想觀念,統治者用以愚弄天下、粉飾君權無比合理神圣的謊言被無情戳穿了。從這個意義上看,郭沫若認為老子的思想觀念,在古代中國思想史的觀念發展變化上,具有非常明顯和深刻的劃時代革命性進步意義。
顯然,郭沫若該文對老子的認識與評價,延續了其《我國思想史上之澎湃城》中將老子定位為“再生時代之先驅者”的認識評價思路。在郭沫若看來,春秋戰國諸子百家著書立說,紛紛發表各家各派的思想主張這樣一種百家爭鳴的局面,體現了人的自我意識之覺醒,思想觀點自由表達的高度開放,是中國古代思想史發展的一個黃金時代,他所謂的“再生時代”,即指此而言。而這個“人”的覺醒與思想自由時代的到來,多虧了老子這位勇敢的先知先覺者,是他的思想觀念,激發了廣大士人開始對宇宙規律和社會倫理等重大理論問題作自由而嚴肅的思考,稍后興起的儒、墨、道、名、法、陰陽諸家,盡管各自關注的重點不同,提出的理論主張也存在諸多差異,有的甚至彼此攻難非毀,但恰恰是通過這樣的自由辯難爭鳴,使一切神秘主義的思想偽裝無所遁形,迷信的神權觀念失去了信眾的市場,取得了明辨是非、揭示真理的理論效果。郭沫若認為,這些進步的實現及成果的取得,是作為思想先驅者的老子,其以“道”為宇宙本體的世界觀,從根本上解答了萬物的起源演化,宇宙的發展變化,以及社會的應然秩序等基本原則與規律。因此,在春秋戰國這個思想觀念大變革時代,老子居功至偉。
然而,就在1923年下半年,郭沫若發表了與歷史人物老子身世經歷有關的歷史題材小說《柱下史入關》,其中的老子形象,則完全被塑造成了另外一副面孔。在正史里,最早記錄老子生平活動情況的權威史書《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謂老子為周守藏史,“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遁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于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終。”關于老子遠遁所過之關隘,史家或認為指函谷關,或認為指散關。但不管什么關口,司馬遷都只記載了老子將隱“出關”的事,且言去后莫知所終。但郭沫若的小說,名曰《柱下史入關》,內容主要寫老聃出關到了人跡罕至的大沙漠,沒有水喝,沒有食物,即將渴死餓死,最后為求活命,親手把自己所騎的青牛殺了,飲其血以解渴,得以不死,歷盡艱辛回到函谷關,準備回歸中原,重新選擇入世生活。小說通過老聃與關尹喜的大段對話,表現老聃對當初作出遁世遠隱草率決定的后悔,并且反復申明所著的《道德經》五千言全是騙人的鬼話,反映了自己的無比自私和虛偽。談到關尹奉為寶典的《道德經》,他說:“我在這部書里雖然恍恍惚惚地說了許多道德的話,但是我終竟是一個利己的小人。我向你說過,曉得善的好處便是不善了,但我偏只曉得較權善的好處。我曉得曲所以求全,枉所以示直,所以我故作蒙瞽,以示彰明。我曉得重是輕根,靜為躁君,所以我故意矜持,終日行而不離輜重。我要想奪人家的大利,我故意把點小利去誘惑他。我要想吃點鮮魚,我故意把它養活在魚池里。啊啊,我完全是一個利己的小人,我這部書完全是一部偽善的經典啦!我因為要表示是普天之下的唯一真人,所以我故意枉道西來,想到沙漠里去自標特異……”作為文學形象的老聃,面對其思想主張的狂熱崇拜者關尹,逐一批判了自己所著《道德經》中的思想觀點,全盤否定了其“自隱無名”的思想學說,并且一再申言《道德經》是一部偽善的經典,自己則是一個利己的小人!他為自己殺牛飲血懊悔不已,并且說青牛之死讓他幡然醒悟:
青牛它是我的先生呢。它教訓我,人間終是離不得的,離去了人間便會沒有生命。與其高談道德跑到沙漠里來,倒不如走向民間去種一莖一穗。偽善者喲,你可以頹然思返了!我的牛,啊,我的先生,它給了我這么一個寶貴的教訓。它的這條尾巴比我五千言的《道德經》還要高貴五千倍呢。
老聃決定重返人間,認識到人間是離不得的,離去了人間便會沒有生命,并且希望到民間去種一莖一穗,過自食其力的普通人生活。這樣徹底否定自己的思想和人生態度的自我醒悟,不是他自己經歷沙漠的艱辛與生命的苦難換來的,而是死去的青牛給他的寶貴教訓與啟示,所以他不止一次說青牛是他重獲新生的“先生”!小說在即將結尾時寫道:“(老聃)自言自語地說:‘我這部誤認的《道德經》,只好讓我自己拿去燒毀了。’他便把那編竹簡挾在腋下,右手拿起他的牛尾巴,悠悠然向東南走去。”老聃要用這種極端的方式,處置充滿欺騙與虛偽的《道德經》,以此向世人宣告與過去的思想和認識態度徹底決裂。
就在大約半年以前,郭沫若站在學理的角度,還認為老聃是春秋戰國時代最了不起的先知先覺者,是他對宇宙萬物和人間萬象的睿智思考,使中國古人對宇宙本體、萬物生長變滅與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發生了革命性改變,促使“黑暗時代”進步到思想自由的“再生時代”。而在此時,郭沫若卻借歷史題材和人物原型,在小說中把老聃刻畫成一個自私、偽善的勢利小人,他的全部學說與主張,都是為自己的名利在盤算。為了一個虛無縹緲的“博大真人”名號,他不遠千里棄世出關,隱遁荒漠,甚至為了留名,還特意為關吏著書五千言,宣揚其道德學說;見了沙漠“草沒有一株,水沒有一滴”的惡劣環境,他經受不住寂寞與艱苦的考驗,殺牛飲血,狼狽而返,追悔自己的隱遁決定十分愚蠢和荒誕,青牛之死提供的深刻教訓,就是不能離開人間,不能離開生活實際去高談迂闊虛偽的道德。一個引領時代思想風氣之先的智者,這時候心悅誠服地拜青牛為“先生”,認為自己的《道德經》五千言,還抵不上一只牛尾巴!如此前后迥異的不同認識,如此智愚相懸的巨大評價反差,著實讓人難解和困惑。
我們都知道學術研究與文學創作不同,在文學創作中,作者可以根據創作動機或者人物典型塑造的需要,對人物原型及相關素材進行取舍和虛構;我們也知道郭沫若的思想認識與對待歷史的態度,在不同的人生階段與政治背景之下不斷發生著改變,這種改變的進程貫穿郭沫若的一生,即便學術研究也突出地表現出這一特點;我們還知道小說集《豕蹄》所收的各篇歷史題材小說,寄寓了作者當時“以史實來諷喻今事”的某種特別用意。但是,通覽《豕蹄》中的所有歷史題材小說,像《柱下史入關》這樣研究評價與文學形象塑造截然相反的歷史人物,畢竟還是非常罕見的。何況,根據作為《豕蹄》這部小說集的序言《從典型說起》交代的歷史題材小說創作原則,以及歷史人物塑造方法,把老聃塑造成與其一貫肯定老子思想的反面文學人物形象,也是顯得多少有些怪異的。郭沫若在文章中說:“以諷喻為職志的作品總要有充分的嚴肅性才能收到諷喻的效果。所謂嚴肅性也就是要有現實的立場,客觀的根據,科學的性質,不可任意賣弄作者的聰明。尤其是取材于史實,是應該有歷史的限制的。”還說:“任意污蔑古人比任意污蔑今人還要不負責任。古人是不能說話的了。對于封著口的人之信口雌黃,我認為是不道德的行為。”只有一種情況屬于例外,即歷史人物的真實形象因為特殊原因被歪曲或者粉飾,“作者為‘求真’的信念所迫,他的筆是要采取著反叛的途徑的。”依照郭沫若創作歷史題材小說的原則,老聃的形象似乎完全沒有理由在短短的半年時間里,作如此顛覆性的改變。唯一的合理解釋,大概是郭沫若出于諷喻現實的客觀需要,小說中“偽善者喲,你可以頹然思返了”的老聃道白,似乎透露了作者當時的創作動機。郭沫若想通過作品中老聃對遠遁自隱行為的幡然悔悟,及重回人世間的人生道路選擇,告誡世人要積極入世,進取有為,為改變丑惡的社會現實而盡到每一個人的責任。這符合五四運動以來知識分子苦尋救國方略的普遍理想追求和人生價值選擇。
二、關于《道德經》的成書問題考察與老子思想評價的總體定位
旅日十年的郭沫若,由于遠離故土及中國的社會斗爭現實,所受五四運動精神激蕩而高漲的文學創作熱情,因為主客觀條件的改變而迅速降溫,他帶著幾分無奈和不情愿,進入了以周秦諸子為重點的歷史研究領域。后來收入《青銅時代》的歷史論文,一部分就是30年代在日本旅居時期的研究成果,其中與老子和《道德經》相關的,主要是《老聃、關尹、環淵》和《先秦天道觀之進展》兩文,涉及《道德經》的作者與成書年代,老聃思想的評價諸問題。
寫于1934年12月的《老聃、關尹、環淵》一文,屬于考證性論文,與本文論題相關的主要是老聃的生活年代、《道德經》的著述性質、成書過程及完成該書的作者等問題。郭沫若在文章的開頭部分,首先介紹梁啟超關于《道德經》成書甚晚的觀點,表明大致同意梁氏及多數學者的意見,認為該書“成書的年代約略在戰國中葉”。既然《道德經》成書于戰國中葉,那么其與生活于春秋末期的老聃之間的關系,就面臨了許多與歷史記載相矛盾的問題,其中包括司馬遷《史記》所載老聃為關尹著書上下篇五千言,是否就是后世認定的《道德經》問題。
要理清老子與《道德經》的關系,就須先確認老子的生活年代。郭沫若從司馬遷《史記》中關于老聃記載的自相矛盾,看出其在漢初已經難于理清老聃的真實身世經歷,所以涉及老子其人,就有老聃、老萊子、太史儋三種不同說法,三個人生活的年代不一樣,老子究竟生活在什么時代?各種紛繁的見解,在現代學者錢穆的《先秦諸子系年·老子雜辨》中,有著相當詳盡的梳理,在文章的末尾,錢氏認同了宋人陳師道的一種說法:“‘世謂孔、老同時,非也。孟子辟楊、墨而不及老,荀子非墨、老而不及楊,莊子先六經,而墨、宋、慎次之,關、老又次之,莊、惠終焉。其關、楊之后,孟、荀之間乎?’此疑老子身世最先,而定老子身世亦最的。”錢穆同意老子生活于關尹、楊朱之后,而與孟子、荀子相先后的說法。郭沫若卻不贊同這種觀點,其理由是,(一)秦漢以前的人都認為老子即是老聃,年輩先于孔子,曾經教導過孔子。這從《莊子·天下篇》《呂氏春秋》的《貴公》《當染》《去尤》《不二》《重言》諸篇,以及《韓非子》的《解老》《喻老》等史料中,均能找到有力佐證。(二)老子曾為孔子之師,在早期儒家經典里,孔子自己是明確承認的,比如《禮記·曾子問》四處引用老子的話,孔子親口說“吾聞之老聃”。儒家道統的維護者如韓愈之流,礙于維護道統的所謂純潔性,拒不承認孔子師事老聃的事實,是罔顧歷史,很滑稽的。郭沫若指出:“其實老子做孔子的先生是毫無遜色的,而老子有過孔子那樣的一個弟子在秦漢以前也并不見得是怎樣的光榮。”依照這樣的論證邏輯和提供的證據,郭沫若認為,要了解老子的真實身世經歷,應該取信于秦漢以前的史料記載,他因此提出明確觀點,老子即是老聃,其年輩先于孔子。
關于《道德經》的作者及成書年代。學界歷來認為,在春秋時代未曾出現私家著書的情況,《論語》《墨子》都不是由孔子、墨子本人撰寫完成,而是他們的弟子或再傳弟子們,根據師生之間的問答談話,記錄整理而成。因此,《史記》關于老子出關時為關尹著《上下篇》五千言的記載,是靠不住的。雖然老子為關尹著書不可能,但《老子》上下篇五千言又是很早就流傳于世的,不僅地上的古典文獻資料足以證明,而且上世紀70年代馬王堆等地發掘的地下楚簡,也可有力證明至少在漢初,就傳布著以道、德為主要內容的《老子》上下篇。《漢書·藝文志》道家類有《老子鄰氏經傳》四篇,《老子傅氏經說》三十七篇,《老子徐氏經說》六篇等著錄。稱“經傳”“經說”者,均是傳承、闡釋老子學說的。可見在西漢,《老子》已經被尊為經典,大概漢人因《老子》全書皆言道德問題,所以便稱為《道德經》了。
郭沫若考證《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有“環淵,楚人,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其旨意,著《上下篇》”的記載,認為環淵所著之《上下篇》就是后世所傳的《道德經》上下篇。并對此分析推論說:“太史公所錄的這些史實應當是有藍本的,藍本應當是齊國的史乘。太史公把它照錄了,在他自己顯然不曾明白這《上下篇》就是《道德經》。”他還分析了《史記》關于老子出關為關令尹著書的記載,認為這是漢初在世間的一種傳說,司馬遷用或然的口吻采錄了這種傳說,“這兒所說的‘關令尹’就是《莊子·天下篇》和《呂氏·不二》的關尹。關尹即環淵,關環尹淵均一聲之轉。……故環淵著《上下篇》是史實,而老子為關尹著《上下篇》之說是訛傳,但訛傳亦多少有其根據,所根據者即是環淵著《上下篇》這個史實。現在老子《道德經》是環淵所著錄,由史實與訛傳兩方面算得到了它的證明。”據此,郭沫若提出兩點基本結論,一是“《老子上下篇》乃環淵所錄老聃遺訓,唯文經潤色,多失真之處,考古者須得加以甄別。”二是“環淵生于楚而游于齊,大率與孟子同時,蓋老聃的再傳或三傳弟子。”用“大率”“蓋”之類的或然之辭,表明郭沫若也是依據相關史料所作的推論,并不能確定如此。因此,郭沫若在梁啟超等人提出《道德經》成書于戰國時代的觀點基礎上,進一步推斷認為是由與孟子同時的楚人環淵筆錄老聃與弟子的談話潤色而成。既否定了老子生于戰國時代的說法,又提出了《道德經》非老聃本人出關為關尹喜所著,而是由其弟子采用與《論語》《墨經》類似的做法,根據老師的談話筆錄整理形成。但是,《道德經》與《論語》《墨經》在語言風格上又有明顯不同,通篇頗具文采,很多地方甚至押韻。郭沫若對此給出了自己的解釋:“環淵是文學的趣味太濃厚的楚人,他纂集老子遺說的態度卻沒有孔門弟子那樣的質實,他充分地把老子的遺說文學化了,加了些潤色和修飾,遂使《道德經》一書飽和了他自己的時代色彩。”
《先秦天道觀之進展》作于1935年12月。在利用了殷墟龜甲獸骨作為地下發掘的資料考察商代的天、神觀念以后,郭沫若闡述了西周關于“天”的觀念所出現的新變化,指出:“以天的存在為可疑,然而在客觀方面要利用它來做統治的工具,而在主觀方面卻強調著人力,以天道為愚民政策,以德政為操持這政策的機柄,這的確是周人所發明出來的新的思想。”當歷史進展到春秋時代,郭沫若認為這是一個在政治上爭亂、在思想上矛盾的時代,政治上爭亂是為了求定,思想上的矛盾則是在醞釀著新的統一。在致力于思想統一的過程中,“中國思想上展開了燦爛的篇頁”。郭沫若交代中國古代思想的發展背景,顯然其目的在于為肯定老子、孔子在此過程中發揮的突出作用與貢獻進行準確“定位”:即老子徹底破除了夏商西周以來關于“天”在中國古代意識形態上的絕對權威,而以“道”取而代之,作為超越時空的本體觀念。他指出:“老子的最大發明便是取消了殷周以來的人格神的天之至上權威,而建立了一個超越時空的形而上學的本體。這個本體他勉強給了它一個名字叫作‘道’,又叫作‘大一’。”
《老子》第二十一章:“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一。”王弼解本章首句云:“混然不可得而知而萬物由之以成,故曰混成也。不知其誰之子,故曰先天地生。”說明“道”是先于天地萬物就存在的東西,雖然無形無名,但天地萬物都是由之生成的。陳鼓應解釋老子一再強調“道”存在于無形的原因說:“因為如果‘道’是有形的,那必定就是存在于特殊時空中的具體之物了;存在于特殊時空中的具體事物是會生滅變化的。然而在老子看來,‘道’卻是永久存在的東西,所以他要肯定‘道’是無形的。”
郭沫若認為,老子在中國古代思想史發展上的重要貢獻,首先在于賦予“道”形而上學的本體意義。在老子之前,政治家和思想家們借用道路之“道”,指稱適用于世間的法則或者方法,如《尚書·康王之誥》“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按照孔穎達《尚書正義》的解釋,這里的“道”指周文王、周武王所奉行的治國方法;《左傳》記載鄭子產所說的“天道遠、人道邇”,指的也是自然法則、社會法則。“到了老子才有了表示本體的‘道’,老子發明了本體的觀念,是中國思想史上所從來沒有的觀念,他找不出既成的文字來命名它,只在方便上勉強名之曰‘大一’,終嫌其籠統,不得已又勉強給它一個名字,叫作‘道’。”郭沫若分析,老子雖然借用了“天道”的成語,但賦予其與商周時代“尊天”完全不同的宇宙本體意義,這正是老子苦心孤詣的發明。
其次,郭沫若分析了老子對“道”作為宇宙本體的觀念內涵所進行的闡釋。《老子》第四章云:“道充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郭沫若據此分析指出,按照老子的觀點,“‘道’是宇宙萬物的本體,是為感官所不能接觸的實在,一切由人的感官所生出的范疇不僅不能范圍它,且都是由它所引申而出,一切物質的與觀念的存在,連人所有的至高的觀念‘上帝’都是由它所幻演出來的。”顯然,道既先于宇宙萬物而存在,而且先于人的觀念而存在,連至高至尊的“上帝”也是道的衍生物。錢穆、馮友蘭均對老子提出的“道”所具的思想史進步意義給予高度肯定。錢氏寫于1923年夏的《關于〈老子〉成書年代之一種考察》指出:“《老子》書中‘道’字有一主要之涵義,即道乃萬有之始,雖天與上帝,從來認為萬物之所從出者,《老子》書中亦謂其由道所生。此乃老子學說至堪注意之一特點也。”馮氏于1930年寫成的《中國哲學史·上冊》(初稿)也持相似看法:“古代所謂天,乃主宰之天……老子則直謂‘天地不仁’,不但取消天之道德的意義,且取消其唯心的意義。古時所謂道,均謂人道,至老子乃予道以形上學的意義。以為天地萬物之生,必有其所以生之總道理,此總道理名之曰道。”馮氏所謂老子之道的形上學“總道理”,即是郭沫若所指的宇宙本體。
當然,被郭沫若稱為革命思想家的老子,所提出的“道”的觀念,不僅用于解釋宇宙的本體即萬物的起源問題,否定天與上帝主宰世界的崇高地位。而且有時老子也用它起到政治上的“愚民”作用,這是構成老子政治思想的內容之一。《道德經》被歷代統治者作為君人南面之術廣泛應用,正是這種內容與特征的充分體現。比如老子也相信“天道無親,常與善人”(《道德經》第七十九章),這被郭沫若作為老子同時肯定“天”和“道”的證據之一。似乎它們都是獎善罰惡的最高主宰,共同發揮著有利于統治者教化社會、統一人心的“愚民”功能。郭沫若對此的解釋是,處于新舊思想觀念交替沖撞的春秋時代,老子的思想體系是一個矛盾體,在提出革命性觀念的同時,又難免保留著傳統舊觀念的“孑遺”:“他的思想的特色是建立了一個新的宇宙的根元,而依然保守著向來的因襲。”認為是老子新發明還沒有十分圓熟的真實呈現。
相比而言,郭沫若30年代關于老子及其《道德經》的研究,較20年代更加具體和深入,特別是關于《道德經》的成書過程及筆錄潤色者的考定,為長期以來學界爭論不休的老子其人存在與否問題、《道德經》的基本思想與環淵加工處理的關系問題等,給出了一個頗具學理性的解釋,比他十多年前模糊籠統地討論老子思想及其地位的評價方式,已經有了巨大進步。在對于老子思想進步性及其劃時代貢獻評價上,總體沿襲了20年代的基本觀點,但也顯示了明顯差別:20年代受泛神論思想支配的郭沫若,十分強調老子關于“道”的觀念之無目的性的無為思想一面,他對老子的“無為說”作了如下闡釋發揮:“道是無目的地在作用著。試看天空,那里日月巡環,云升雨降,絲毫沒有目的。試看大地,他在司掌一切生物之發育成長,沒有什么目的。我們做人也應當是這樣,我們要不懷什么目的去做一切的事。人類的精神為種種的目的所攪亂了。人世苦由這種種的為而發生。我們要無所為而為一切!”而30年代幾乎只字未提老子的“無為說”,反而著重強調了老子發明“道”的本體觀念的強烈目的性,他把老子提出“道”作為宇宙本體的觀念,視作一個“苦心孤詣的發明”,老子把“道”作為宇宙的最高主宰,目的就在于從根本上否定天與上帝的絕對權威,神的至上地位。同時,“道”在政治上所發揮的“愚民”的作用,其目的指向性更加清楚。顯然,在諸侯紛爭、天下擾攘的春秋時代,老子提出“道”的觀念作為宇宙存在的本體,絕不純粹只是一個理論思辨的哲學命題,它有著非常現實的思想動機和社會目的性。那就是要為已然發生形勢巨變的社會現實,尋找合理的觀念指引與理論支撐。
三、從對黃老學派的批判看郭沫若關于老子評價的巨大變化
20世紀40年代,郭沫若開展對先秦諸子學說及其發展演變的系列研究,后來匯集成重要研究成果《十批判書》。該書有寫成于1944年9月的《稷下黃老學派批判》一文,涉及老子及其《道德經》的評價。此外,同年7月所寫的《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1945年5月的《十批判書·后記——我怎樣寫〈青銅時代〉和〈十批判書〉》兩文,或多或少提到老子和《道德經》的評價問題。與過去相比,郭沫若此時的研究重點轉向了以繼承與發揚老子思想的稷下學者為主體的學派群體,不再是只針對老子其人其書的專門研究。正是由于研究的對象發生了明顯變化,其視角與評價方式也會隨之發生一些值得注意的變化。
首先,郭沫若認為老子及道家學派的宇宙萬物本體觀,是避世主義人生哲學和希求長生不死生活態度的理論根據。為此,他專門考察分析了道家學派由最初的默默無聞到后來形成巨大聲勢并產生重要社會影響的歷史背景。在郭沫若看來,由于老聃、楊朱本來是退攖的避世主義者,力求與社會現實相脫離,所以最初他們的學說不甚為世所重,根本不能與孔丘、墨翟當世即顯名于時的情形相比。儒、墨兩家弟子徒屬滿天下,四處宣傳,拜謁王公大人以求行道。而道家的本體學說在一般人看來不免玄虛飄渺,其徒屬又多崇奉避世主義人生哲學,難以在解決社會現實問題方面有所作為,故其學說不甚為時所重的直接原因,在于不切實用。但后來的老聃學派不僅逐漸興旺,而且其勢頭曾一度壓過儒家學派,自有其深刻的社會變化原因。郭沫若指出:“在春秋末年,一部分的有產者或士,已經有了飽食暖衣的機會,但不愿案牘勞形,或者苦于壽命有限,不夠滿足,而想長生久視,故爾采取一種避世的辦法以‘全生葆真’,而他們的宇宙萬物一體觀和所謂‘衛生之經’等便是替這種生活態度找理論根據的。這種理論,在它的本質上并沒有多大的發展前途,因為它沒有大眾的基礎;而小有產者的小眾能夠滿足于這種生活態度的,依然還占少數的時候,也無從發展。故爾它在初期不能有孔、墨那樣大的影響。然而這一學派,一經齊國稷下制度的培植,它便立地蕃昌了起來,轉瞬之間便弄到‘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了。”
在上述這段關于道家學派由衰轉盛的發展原因分析文字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把老子倡導的宇宙萬物一體觀,視為此派為其“全生葆真”避世哲學、“衛生之經”生活態度所尋找的理論依據,與之前認定的這種觀念在中國古代思想史發展中具有的劃時代革命性進步意義全然不同了。這從他對齊國扶植道家的動機與目的的解釋中也可以得到清楚印證。他說:“齊國為什么要那樣扶植道家呢?這很明顯,完全是一種高級的文化政策。所謂‘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自從齊威王襲田氏的遺烈,篡取了齊國之后,由向來養士的習慣,要有一批文化人來做裝飾品,固然是一種動機,而更主要的還是不愿意在自己的肘翼之下又孵化出新的‘竊國者’來,所以要預為之防,非化除人民的這種異志不可。在這個目標上,楊、老學說是最為適用的武器。”類似的分析論述同樣見于郭沫若的《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認為道家學派的興旺,全靠齊國“高等的文化政策保護”。顯然,這是此時的郭沫若堅持“人民本位”評價標準,按照階級分析方法,通過各家各派比較評判所必然得出的結論。
其次,通過對韓非《解老篇》關于《道德經》第三十六章解讀的分析,郭沫若嚴厲地批判了老子及其思想傳人秉持的個人主義立場,認為這種觀點被統治者利用,就自然變成了愚民政策。關于老子的政治思想中包含愚民政策的成分,雖然在郭沫若30年代的《先秦天道觀之進展》一文中就已提及,但并未深入分析論述,也沒有論證其發展演變的過程。《道德經》第三十六章云:“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王弼解后四句云:“利器,利國之器也。唯因物之性,不假刑以理物。器不可睹,而物各得其所。則國之利器也示人者,任刑也。刑以利國則失矣。魚脫于淵,則必見失矣。利國器而立刑以示人,亦必失矣。”韓非《喻老篇》引申老子觀點云:“勢重者,人君之淵也。君人者勢重于人臣之間,失則不可復得也。……故曰:‘魚不可脫于深淵。’賞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則制臣,在臣則勝君。……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體現了明顯的君主專制集權思想。有時候為了達到攫取權力的目的,完全可以采取權謀詐術。所以郭沫若認為,老子講得頭頭是道的人君治國理論,說白了就是一種為了權力可以不擇手段的“詐術”:“這在道家本身原是應有的理論。因為它根本是站在個人主義的立場的。盡管是怎樣的個人主義者,一個人不能完全脫離國家社會而生存,故論到國家社會的理則時,便很容易流露出其個人主義的本色。為要保全自己或使自己所得之利更大些,當然要把自己立于不敗之地,而以權術待人了。故老聃的理論一轉而為申、韓,那真是邏輯的必然,是絲毫也不足怪的。”在分析關尹一派繼承老子權術思想進而演變為愚民政策主張時,郭沫若列舉了《道德經》第六十五章:“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錢穆對老子的這種愚民理論評論說:“此乃圣人之權謀,亦即是圣人之不仁與可怕也。”郭沫若雖然不能完全肯定就是老子本人的遺說,但他相信,是關尹對老子愚民政治思想的進一步發展。郭沫若對此的結論性評價是:“這種為政的態度,簡直在把人民當成玩具。這如是老聃的遺說,可以說是舊時代的遺孽未除;如是關尹的發展,那又是對于新時代的統治者效忠了。不以人民為本位的個人主義,必然要發展成為這樣的,更進一步,便否認一切文化的效用而大開倒車。”盡管郭沫若強調要注意把老子遺說與道家后學區別看待,但其對該學派根本思想和政治主張基本趨于否定評價,已是非常清楚的事實。
再次,對《道德經》一書的看法,也有了值得注意的改變。在《老聃、關尹、環淵》和《先秦天道觀之進展》兩文中,郭沫若雖然已經十分肯定《道德經》就是楚人環淵筆錄老子遺說加以文字潤色而成,
但并未深入分析環淵的思想與其他黃老學派有什么不同,也沒有闡述環淵的思想在潤色老子遺說過程中得到怎樣的體現。而在《稷下黃老學派批判》中,郭沫若試圖給予回答。他首先分析了環淵一派與宋钘、慎到兩派思想觀念的差別:“照《天下篇》所引的關尹(環淵)遺說看來,他是主張虛己接物的……他的單獨成派,或者是因為他把他們兩家(宋钘、尹文,慎到、田駢)的現實傾向都拋棄了的原故罷。宋钘、尹文志在‘救世’,慎到、田駢學貴‘尚法’,他們都還沒有脫離現實,而在關尹或環淵便差不多完全脫離現實而獨善其身了。‘淡然獨與神明居’,便很扼要地說穿了這種態度。”這種主張脫離現實、獨善其身的態度,與《史記》所述“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的思想特征最為接近。郭沫若顯然是由此得到啟示,并將其作為論證環淵所著《上下篇》就是筆錄潤色老子《道德經》上下篇的重要依據之一。同時,郭沫若根據《天下篇》所引“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二十字的老子言,在《道德經》第二十八章中被潤色者將其擴充為八十六字等史料證據,得出如下結論:“可知《道德經》毫無疑問成于后人之手,其中雖然有老聃遺說,但多是‘發明旨意’式的發揮,并非如《論語》那樣的比較實事求是的紀述。因此要認《道德經》為老聃所做的書,字字句句都出于老子,那是錯誤;但要說老子根本沒有這個人,或者有而甚晚,那也跑到了另一極端。這兩種極端的見解卻是從同一個出發點出發,是很有趣的形象。因為它們都認為《道德經》是老聃自己所做的書。現在我把這層云霧揭開,斷定它是環淵即關尹發明老氏旨意而作,那么根據這項資料,我們既可以論老聃,也可以論關尹了。”只有證明了環淵學說與老子思想的相似性,他們之間的學派承續關系才能成立;環淵所筆錄的老子遺說《道德經》,其中包含了潤色者對老子遺說旨意的大量發揮,其中自然免不了摻雜環淵自己的思想成分,說明老子思想隨著學派分立而發生了演變;加之“發揮”的方式采用了論贊體形式,遂形成《道德經》文學色彩特別濃郁的表現特征,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從春秋末期到戰國中期的文風變化。應該說,這樣的證據與結論比30年代的觀點更加具有說服力。
(責任編輯:陳俐)
[1]郭沫若.十批判書·后記——我怎樣寫《青銅時代》和《十批判書》[M].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郭沫若.我國思想史上之澎湃城[A].王錦厚,武加倫,肖斌茹編.郭沫若佚文集(上冊)[M].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88.
[3]郭沫若.史學論集·中國文化之傳統精神[M].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4]司馬遷.史記卷六十三[A].北京:中華書局,1982.
[5]郭沫若.柱下史入關[A].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0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
[6]郭沫若.從典型說起——《豕蹄》的序文[A].郭沫若論創作[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
[7]郭沫若.青銅時代·老聃、關尹、環淵[A].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8]錢穆.先秦諸子系年·老子雜辨[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9]班固.漢書卷三十[M].北京:中華書局,1983.
[10]郭沫若.青銅時代·先秦天道觀之進展[A].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11]老子道德經.二十二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2]陳鼓應.老莊新論·老子哲學系統的形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13]孔穎達.尚書正義卷十九[M].北京:中華書局,1980.
[14]錢穆.關于《老子》成書年代之一種考察[A].莊老通辨(上卷)[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
[15]馮友蘭.《老子》及道家中之《老》學[A].中國哲學史(上冊)[M].北京:中華書局,1992.
[16]郭沫若.十批判書·稷下黃老學派批判[A].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7]梁啟雄.韓子淺釋·喻老[M].北京:中華書局,1982.
[18]郭沫若.十批判書·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A].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9]錢穆.道家政治思想[A].莊老通辯[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
I206
A
1003-7225(2014)04-0025-08
2014-08-17
楊勝寬,男,樂山師范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