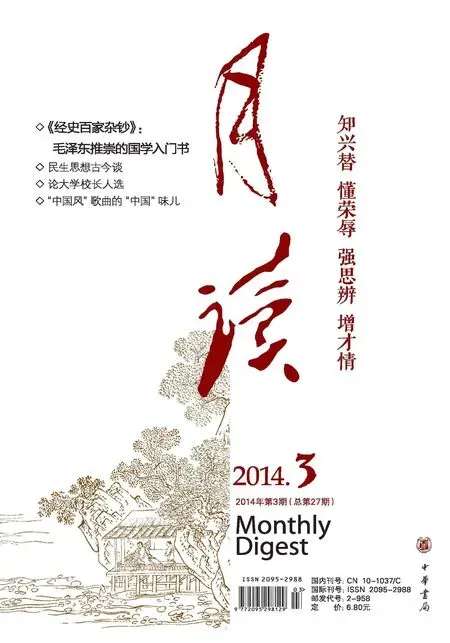非非堂記
〔宋〕歐陽修
非非堂記
〔宋〕歐陽修
權衡(稱重的器具)之平物,動則輕重差,其于靜也,錙銖(極小的重量單位)不失。水之鑒物,動則不能有睹,其于靜也,毫發可辨。在乎人,耳司聽,目司視,動則亂于聰明(視覺與聽覺),其于靜也,聞見必審。處身者不為外物眩晃而動,則其心靜,心靜則智識明,是是非非,無所施而不中。夫是是近于諂,非非近于訕,不幸而過,寧訕無諂。是者,君子之常,是之何加?一以觀之,未若非非之為正也。
予居洛之明年,既新廳事,有文記于壁末。營其西偏作堂,戶北向,植叢竹,辟戶于其南,納日月之光。設一幾一榻,架書數百卷,朝夕居其中。以其靜也,閉目澄心,覽今照古,思慮無所不至焉。故其堂以“非非”為名云。
【大意】
用秤來稱量物體,晃動時會產生輕重的差異,當它穩定下來,相差極輕微的重量也能稱出來。用水來映照物體,晃動時就不能看到影像,當它平靜下來,一絲一毫都可以辨認。在人來說,耳朵是主管聽的,眼睛是主管看的,動蕩不安,就難以耳聰目明,如果在安靜的時候,人對于所見所聞必定準確。處世立身的人若不被身外眩目耀眼的事物所迷亂,那他的內心就必定安靜;內心安靜,智慧見識就清晰明白,肯定正確的,否定錯誤的,無論用在哪里都能成功。肯定正確的,常常近于諂媚;否定錯誤的,常常近于誹謗,不幸受到指責,寧可被指為誹謗也不要被指為諂媚。言行正確,是君子的常態,肯定又有什么增益?總體上看,肯定正確不如否定錯誤更為可取。
我居住洛陽的第二年,重修官署之事已經完畢,我寫了一篇文字刻于壁下。在大堂的西邊建造了偏房,門向北開著,院內種植了幾叢竹子,在房屋的南面開辟了窗戶,接收日月的光輝。屋里擺設上一條幾案、一張臥椅,書架上擺了幾百卷書,我早晚就居住在里面。因為這里清靜,我可以閉目養神,讓思緒清澈明晰,看今日之事,想古人所為,思想就沒有不可以到達的地方。所以,我把這個廳堂命名為“非非”。
【題解】
歐陽修的名文,如《與高司諫書》《朋黨論》等,皆鮮明體現其敢于“非非”的作風。而他數次被貶,均與“非非”有密切關系。其可貴之處,在于一生都如王安石《祭歐陽文忠公文》所說:“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北宋名臣韓琦在《歐陽文忠公墓志銘》中也有評述:“公天資剛勁,見義敢為,襟懷洞然,無有城府……惟視奸邪,嫉若仇敵,直前奮擊,不問權貴……”這種直道而行、不和稀泥的人格力量,無疑對宋初文恬武嬉的風氣是一種凈化,建立了一種以正義、責任、使命為內涵的人格范式,對宋初士風轉變產生了深刻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