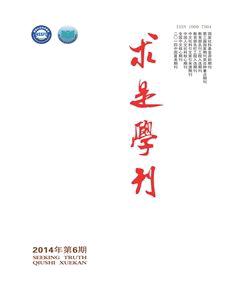視覺形式自律與視覺現代性問題
摘 要:在視覺審美中,現代性的標記無疑在于形式自律。但自律并不是簡單地專注于形式,而是如何建構出形式的意義。唯有形式感知中沒有前經驗滲入只有當下的看在起作用時,自律才得以出現,此時的形式感知由單純的看建構意義。其對應的形式特點是殊異于現實,唯有殊異于現實的形式造型才能引發自主的看。殊異成了現代性的標記,它將視覺閱讀引向了單純感性領域。
關鍵詞:形式自律;視覺感知;視覺現代性
作者簡介:王才勇,男,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從事當代德法哲學研究。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視覺現代性研究”,項目編號:09BZX066
中圖分類號:B1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504(2014)06-0020-07
對于西方19世紀中下葉前后文學藝術領域崛起的現代派運動,幾乎誰都會用形式自律去言說。所謂自律也就是不再依循現實給定,開始獨立建構。言外之意是,前現代時期的藝術創造主要來自現實,而現代派運動則開始走離現實,走向與之不同的那一面,甚至反面。縱觀延續至今的整個現代派運動,此說固然沒有問題。但是,對于現代派研究來說,單單指明這一點應該還是不夠的。此間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指明現代藝術開始與現實形式不一樣,而是要深入澄清,如何不一樣以及這種不一樣的形式創造何以在現代社會得以產生。當然,這個問題有其復雜性,而且在不同藝術領域有其不同的情形。本文以視覺為具體指向,試圖闡明視覺領域中作為現代性標志的形式自律究竟如何。
一、視覺形式的他律與自律
一般而言,按視看本然因素而來的視覺感知是自律的,而輔之以其他非視看因素而來的感知則是他律的。日常視看中本來就具有著這兩種情形:其一,面對一個視看對象,視覺感知由單純的看而發生,其間沒有其他非視覺性信息的介入,如面對一個從未見過的情景或對象而要單憑視看去獨立判斷;其二,一個視看對象是在其他非視覺性信息的介入下才被感知,如面對一個熟悉的對象或即便首次面對也有其他背景性信息輔助。所謂視覺形式的自律也就是說,對它的視覺感知無法憑依其他非視覺因素而發生,他律則是經由其他非視覺因素而來。這一點應該容易理解,但問題就此遠沒有解決。進一步的問題是,究竟哪些是感知中的視覺性因素,哪些又不是?這又具體涉及人類視覺感知的一般特點問題。
視覺感知是憑借視覺對世界的把握,就像人可以通過觸覺、聽覺乃至嗅覺來把握世界一樣,其媒介是圖像。由此首先可以確定的是,圖像并不是世界本身固有的,而是人經由視覺把握對象時從對象中概括出來的,如作為圖像基本要素的點、線、面、形狀等這些形式要素都是人為了方便視覺把握而從對象中概括出來的,對象本身只有空間、體積等因素而并不存在這樣的東西。這樣說并不是為了貶低圖像的客觀性,而是可以從基點上凸現圖像的意義特征。任何對象本身的存在不經由與人發生關聯是不具有意義的,而人在看對象的過程中從對象中概括出了圖像這個東西,表面看是為了可以從視覺上把握對象,實際上,是使對象在視覺上與人發生了關聯。所以,圖像作為視覺感知對象的媒介從一開始就是一個意義體。正是基于此,德國當代著名圖像學研究者博姆(Gottfried Boehm)指出:“單靠物質性因素,圖像是不會誕生的。圖像總是與視看、視像、意義相關。”[1](S30)圖像總是人視看的產物,對象就其自身而言是沒有諸如構成圖像的點、線、形和色彩等這些東西的,這一點也得到了現代神經心理學的證實。德國當代著名神經心理學家辛格爾(Wolf Singer)曾就視覺感知指出:“心理物理學(Psychophysik)和實驗結果表明:我們的感知并不是對現實的單純摹寫,而是由復雜的感知建構組成。”[2](S65)
其實,視覺感知的這個主觀性特點早在現代語言學、哲學等領域間接地被披露,因為圖像作為一種視覺工具與樂音、語言等其他認知工具一樣,都是人為了認知的方便從對象中概括出來的,都是人為自己構建出的意義符號。當然,對于視覺問題研究來說,指出這一點只具有一般意義,還未觸及唯視覺所特有的東西。為此,就必須將視覺與人的其他意義感知活動放在一起來看。辛格爾在研究視覺感知時曾說:“觸覺是人最信賴的感知,人的所有其他身體經驗都是建立在此基礎上的。”[2](S58)西方對視覺感知的言說自古以來就有將其建基于觸覺的說法,就充分說明了觸覺比視覺要來得基本,來得直接。但是,較之于聽覺,甚至語言,視覺感知則更具有說服力,更讓人信賴,因為視覺憑依的是一些同比而言更為直接,更為原始的感知手段,而聽覺則相對要抽象些,至于語言則更是依賴于符號這樣的抽象媒介。一般而言,感知媒介即感知手段與對象靠得越近,也就越直接,越具有說服力,但同時也越簡單,越無法通達復雜事物。視覺感知居于觸覺與知覺(抽象媒介)之間,圖像應該是唯其特有的東西。觸覺與知覺憑依的都不是圖像,唯有視覺建基于圖像。據此可以說,圖像是視覺感知特有的東西。凡是經由圖像去把握的形式就是自律的視覺形式,反之,則是他律的。
可是,問題顯然并沒有如此簡單。圖像雖然為視覺所特有,但它同時也可成為非視覺感知的對象,如知覺,在特定情況下也可成為觸覺的對象,也就是說,憑借想象,如知覺想象或觸覺想象,人同樣能去感知圖像。這時,圖像就不為視覺所特有了,這是因為圖像本身并不是對象的本然存在,而是一個由人專為視覺感知建構起來的意義體,“而這個建構很大程度來自預先儲存著的認知”[2](S65)。這個預先認知可以是視覺方面的,也可以是非視覺方面的,它們都程度不等地介入到了視覺感知中,而且這種非視覺因素的介入往往是不知不覺的。正如辛格爾所說:“視覺感知中的這種建構因素人自己是察覺不到的,在感知中,誰都信奉自己在如實感知。”[2](S76)這樣,視覺形式的自律問題中又出現了另一個更為重要的層面,沒有主觀建構,沒有非視覺因素的介入,也就是說,沒有預先認知的介入,不管是視覺的還是非視覺的。
由是觀之,視覺形式的自律問題中就有兩個層面的規定:首先,它必須與圖像相關;其次,又不能與預先給定的東西相連。這個預先給定的東西可以是視覺方面的,也可以是非視覺方面的。就前者而言,可以是曾感知過的圖形與色彩等;就后者而言,可以是來自于知覺,甚至觸覺的形象感知,比如面對一個圖像一時無法感知到什么,憑借其他信息后方才有所感知。因此,視覺形式的自律問題中關鍵性因素并不在于是否經由圖像,而在于如何經由圖像。
美國當代著名圖像學研究者米切爾(W.J.T.Mitchell)在其研究圖像問題的早期著作《圖像學:形象、文本、意識形態》(1986)中曾參照維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概念指出了圖像家族中的各個分支,其中“語言形象”和“心理形象”都占據著顯赫的位置。這就是說,在我們的圖像感知中有許多非視覺性因素介入其中,一個視覺形式可以經由圖像,也可以不經由圖像被感知,所謂“語言形象”和“心理形象”就是未經由圖像而被感知到的視覺形式。即便面對一個圖像,我們的視覺感知也不會是純粹經由視覺的,而總是夾雜著非視看性的思維活動等,所謂視覺思維指的就是這一現象。鑒于這兩種情形,視覺就不可能自律,它必然是他律的。面對一個視覺形式,人總會向其中注入某種意義,所謂讀解其實就是這種注入。對人而言,形式總是具有內容的,都是有所傳達的。因此,形式不可能自律,都是他律的。這里,問題的關鍵是:“內容”或“傳達”是人“注入”的結果。世界本身無所謂內容與形式,是人為了自己的方便,為了把握對象,才向對象中注入了內容。視覺感知同樣如此。所以,視覺形式自律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是否專注于形式,任何感知都是離不開形式的,而在于如何注入或見出意義。
正像辛格爾業已指出的那樣,任何感知,包括視覺感知,都是建立在“預先儲存著的認知”的基礎上的,也就是說,感知通常都是他律的。自律只有在脫離這種關聯時才發生,因為沒有了既往經驗提供的依循,感知就只能靠自己去重新建構意義。就視覺感知而言,當失落了既往經驗的介入——不論是視覺的還是非視覺的,感知就只能專注于眼下的看,這時見出的形式就是自律的,它不僅與既往的看,而且也與心理、直覺等其他活動沒有了關聯。這種情形往往在面對一個陌生圖形時發生,而且陌生的程度越高,視覺自律的程度就會越高。只有陌生了,視覺在建構意義時找不到任何可以憑依的東西(預先的儲存),才只能靠自己去獨立建構。這時,視看就自主了。
因而,自律就是要與日常不一樣。日常感知中沒有任何東西是純粹的,它不僅與前經驗糾纏在一起,而且也與其他知覺手段融而為一。就視覺形式而言,只有當一個圖像與日常所見出現了殊異,才開始轉向自律。這時,視覺感知就開始專注于當下的看。否則,便是他律的,他律的視看不僅接入到過去的經驗,而且也會受眾多其他非視看訊息的影響。所以,形式化并不是自律的關鍵,雖然自律往往以形式化的面貌出現。只有當形式化發展到了與現實形式有殊異的時候,自律才開始出現,因為有了殊異后,既成的內容就與之脫離,而意義建構就必須重新開始,而這時除了看本身之外沒有任何其他東西可以作為確鑿的憑依,于是,看就開始自律了。所以,視覺形式的自律并不在于是否經由或面對圖像,而在于圖像感知是否有其他非視看因素介入,有,則他律;無,則自律。從另一個角度看,自律之所以大多以形式化面貌出現,是因為當感知只能專注于看的時候,指向的就是形式。所謂視覺形式的自律就是讓形式只在視看下產生意義,那是藝術中的情形,而日常視看都是他律的,日常視覺感知中都會有其他非視覺因素的介入。
二、視覺形式自律的圖形特點
視覺形式的自律建基于殊異,而怎樣的疏離才使自律有了可能呢?在人類視覺創造的原初時期,視覺產品與日常視看之間也存在著明顯的疏離,是否最早的視覺產品都是自律的?回答應該是否定的。形式自律在其呈現方式上雖然大多見諸疏離現實,與日常形式相異。但“異”本身并不是目的所在,“異”是為了有別于日常而讓看不受其他非視覺因素的滲入,使視看只是憑借自己而沒有其他信息的支撐去建構意義。原始民族的視覺產品盡管與現實給定顯出不一致,但那是再現技巧的缺位所致,也就是說,主觀意識上并沒有想有這樣的疏離。因此,觀照時還是居于日常視域,還是會有其他非視覺因素,如想象,滲入其中。這時,殊異的形式沒有任何主觀刻意的痕跡,視看一般就不會疏離現實,還是會依循著日常軌跡前行。當然,面對原古稚拙的造型,現代人卻會進入單純看的視域,進而認為那是自主的造型,這是因為現代人沒有那時的日常視域,不會進入那時的日常視看,而當下的日常視域又與其不符,于是就只能憑借看去建構意義。當然,如果憑借一些其他文字、實物材料的訊息再去看這樣的造型,如考古學家,這時又不是自主的了。所以,一個形式的自律與否,表面看在于其是否有殊異性,實際上在于其是否能喚起自主的視看,即是否能引發自主的意義建構。殊異有時是無奈的結果,有時則是刻意的。只有當形式創造刻意走向殊異時,不同于日常視覺感知的自主視看才會被激發出來,形式才會是自律的。
在人類的視覺創造中,最早刻意走向殊異的應該是19世紀中下葉西方視覺藝術領域中出現的嬗變,而且這場轉向形式自主的運動一直延續至今,方興未艾。就這場迄今一百多年的發展看,其內在主線無疑是不斷疏離日常視看,不斷創造出激發自主視看的視覺產品。就其圖形特點來看,不外乎以下五種情形。(1)淡化日常視看的物理維度。最初以印象派為代表的努力,在視覺產品的創造中開始疏離傳統的三維透視畫法。三維透視是建基于日常視看之成像原則的,因而是他律的,因為視覺感知中就像日常視看一樣有其他非視覺因素滲入。早期印象派、納比派(Nabis)等美術家的努力,開始在形象創造中淡化或略去視覺成像中的光影效果并開始關注不同瞬間的映像,于是,創造出的圖像就與日常呈現殊異。日常視看都是建基于光影成像,而且不可能兼顧不同瞬間,總是定于某個時間點的。這樣一來,視看就不可能完全回到日常方式,感知就開始專注于眼下的看,開始更多地從眼下的看本身來建構意義。形式開始走向自律。(2)約減日常形式要素。從后印象派開始,形象創造與現實的殊異又向前邁進了一步,開始將對象的某些形式要素約減掉,以致畫面留下不少模糊,乃至空白處。正是這樣的模糊和空白是日常圖像中沒有的,所以觀照中就不會像日常視看那樣有其他非視覺因素介入。(3)變形和重組。19世紀末20世紀初,殊異化又向前邁進了一步,那就是變形和重組。變形就是變日常圖像中的形,重組就是將日常視覺成像中沒有關聯的形式組合在一起,青春派、象征主義、表現主義、野獸派、立體派、達達主義、未來主義等都程度不等地呈現出這樣的圖形特點。如此跨度的異和變自然更有效地將日常視看中的意義建構剔除了出去。由此,觀照除了眼下的看就愈加沒有了其他依循,形式自主的程度有了更大提高。(4)強化日常視看的形式維度。與現實的殊異可以是弱化或改變現實維度,也可以是強化。20世紀初西方視覺創造中出現的超現實主義就將日常視看無法看清的現實呈現了出來,以至展現的圖像比日常視看的建構還要逼真。這也引發了視看轉向自主,因為它還是與日常視看相異,只要有了這樣的異,日常視看中積淀于特定形式中的理喻就無從復現,這時,視覺感知必須依附于眼下的看并單純由這樣的看去建構意義。(5)抽象。現代視覺創造由殊異起步,到了最后必然走向抽象,因為抽象是最大程度的異。雖然抽象早在20世紀初就已開始出現,但一直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才成為西方視覺創造的主導。面對抽象的圖像形式,感知就更無法憑依日常視看的維度,更無法由預先的積淀去建構意義,而只能由當下的看去建構。從某種意義上說,抽象是最自律的視覺形式。
西方美術迄今發展呈現的這五種圖像語匯中,還隱秘地存在著一個普遍原則:由圖像中不同視覺要素間的交互作用來純視覺地生產意義。日常視看中,由于時空上定于一點的緣故,視覺在閱見特定視覺要素后,如色彩、形狀乃至質感,都會立刻轉向其背后的特定對象,繼而在有關該對象的其他信息介入下建構起視看中的意義。自律的視覺形式中,由于殊異視覺要素背后的對象變得模糊甚至消失,于是,視覺中的意義建構只能專注于所見,只能在所見之視覺要素上去見出意義。在這樣的視看下,視覺要素間就出現了日常圖像不具有的交互作用,有了這交互作用,所見之視覺要素間就會出現某種關聯。由于意義總是與關聯相關,這時意味就會出現。早期的筆觸畫法、留白乃至拼貼等,都是為了在對象的形式要素間建起某種不同于日常的關聯,視看正是依循這樣的關聯建構出了意義。現代造型中,將同色調不同色差的顏色或同質不同狀的形并置之所以會產生動感,就是由于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視覺組合,會使人在不同中見出關聯。關聯置于不同中,這就是單憑視覺見出的意義。
西方現代繪畫迄今的發展清楚表明:與現實相異是其內在主線。可以說,西方現代繪畫幾乎窮盡了形式異于現實的所有可能,正是在此意義上博姆才說:“現代派繪畫幾乎嘗試了圖像世界的所有邊界與可能。”[1](S39)如其所述,“異”只是圖像的建構方式,它的落點卻不在“異”本身,而在轉向自律,轉向視覺感知的自主建構。由此,問題的關鍵也不在“異”本身,而在刻意性。如上展現的那些自律圖像清楚表明:那不是技術局限所致,而是刻意行為的結果。我們的視覺在圖像上能準確無誤地看到這一點,正是因為刻意,那些殊異的形式就傳達出了特有的意義,而由于形式上的異,這意義又無法由日常視覺感知去建構,于是,視看就會拋開既存的一切而專注于看本身。當然,這時的形式已不是日常視看中的形式了,這不是因為與日常有異,而是因為它在獨立地建構自己,在獨立地建構意義。日常視看中的形式建構是不自主的,其間除了視看之外還有其他眾多預先存在的非視看性因素滲入,如心理的、語言的等等。而刻意創造出的殊異圖像則停止了這種滲入,使觀看只能憑借觀看本身來建構意義。正如博姆所說,圖像的固有邏輯“就是以圖像為手段對意義的獨立生產”[1](S28)。
三、形式自律與視覺現代性
迄今有關形式自律問題的研討,大多將其歸為審美和藝術轉向現代的標志。正如所述,日常視看的形式感知中都會有各種非視覺的意識活動滲入,所以形式本身不會生產意義,意義往往由這些非視覺的意識活動注入。最早的藝術活動就是在這樣的框架下展開的,形式都在努力地展現特定的內容。形式指向視覺,內容指向其他意識活動。面對一個形式,當意識活動的內容注入獲得成功,該形式則獲得意義,成為藝術作品。黑格爾就古代藝術所說的形式大于內容,就應該理解成意識活動在形式中還沒有注入多少內容,而那時形式本身還不能獨立生產意義。近代藝術則在形式感知中注入了厚實的意義,所以達到了形式與內容的高度統一。所謂統一也就是形式的物理展現與意識活動注入的意義吻合或一致,其尺度就來自于日常視看,一個作品形式只有在與日常視看中的意義建構吻合時,才會被說成與內容一致。當黑格爾就近現代藝術說內容大于形式時,應該理解成作品形式與日常意義建構出現了錯位或不一致,這時形式開始疏離其日常意義,也就是說開始脫離日常意識活動的意義注入。由此也就開始脫離原來的內容規定,自主地建構意義。所謂自主也就是脫離日常視看對形式的內容注入。現代藝術就是在這樣的美學框架下誕生的。可以說,形式自主是現代藝術的標志所在。但是,問題到此應該還沒有結束。為什么自主的形式恰恰成了現代性的標志?形式原來是不自主的,何以又變得自主了?
對于藝術現代性或審美現代性,波德萊爾在其《現代生活的畫家》一文中曾有過被廣為引用的表述:“過渡、短暫、偶然。”[3](P485)此自然可以去說明形式自主何以是現代的,因為形式自主了以后便沒有了預先確定的內容介入,它的意義建構必須即時地重新開始,即時就注定了其偶發性與瞬間性。但是,由形式自主來看,審美現代性或藝術現代性的關鍵并不在其不確定性和偶發性上,而在更深層的感知方式上。原來,視覺藝術的形式審美基本在日常感知框架下發生,其意義很大程度上是在其他意識活動,如知覺、想象等介入下建構成的。而在自主的形式中,沒有了這些其他因素的介入,感知就變得單一或純粹,正是因為感知在獨立地建構意義,所以才呈現出偶發性和不確定性,因為感性的東西往往是即時的、瞬間的、無法預先確定的,而知性的或理性的東西則大多是確定的、預先存在的。如此看來,形式自主之作為視覺現代性的標志主要并不在其外顯的不確定性上,而在其內隱的感性建構意義上。原來,感性領域的意義也是在知性或理性的參與下被建構成的,而形式自主后,感性開始獨立地建構意義。這時,不僅形式與先前不同,而且視覺觀照也不同。形式開始游離出日常內容的界定,視覺觀照也開始脫離其他非視覺因素的介入而獨立,即單一視覺地去建構意義。也正是基于此,德國當代視覺文化研究者莎德(Sigrid Schade)和溫克(Silke Wenk)指出:“轉向圖像不單純指現代文化的視覺轉向,而且也指現代文化中出現了新的視覺方式。”[4](S41)
視看開始獨立建構意義,這不僅是視覺形式自主的內核,同時也彰顯了視覺現代性的內核。自主的形式引發了獨立建構意義的視看,而這樣的視看何以又是現代的呢?對此當然可以用不同于傳統來解答。但是,不同可以有好幾種情形,為什么單單獨立建構意義的視看成了現代的呢?這又要從現代人感知方式層面發生的變化來看。對于現代人感知方式發生的變化,西方已有不少研究成果,較著名的有德國哲學家齊美爾(Georg Simmel),他曾以大都市人為例指出:“大都市的人際關系鮮明地表現在眼看的活動絕對地超過耳聽,導致這一點的主要原因是公共交通工具。在公共汽車、火車、有軌電車還沒有出現的19世紀,生活中還沒有遇見過這樣的場景:人之間不進行交談而又必須幾分鐘,甚至幾小時彼此相望。”[5](P33)大都市是現代人棲息的場所,可以說,現代人是伴隨著大都市而出現的,而“公共汽車、火車、有軌電車”則是現代社會固有的。在前現代的農業社會,人與人相遇是通過攀談了解對方的。攀談中的了解就有許多非視覺性的知覺、理喻等意識活動介入。而現代社會,看的意義得到凸現,人與人之間的相遇無須了解對方,單憑看就能與對方相處。這時的看由于沒有其他信息介入,視看活動不會轉化為其他意識活動,因而是單純的看。正是由于現代生活中視看的意義凸現才使得圖像生產中形式轉向自律。從另一個角度看,生活節奏變快的現代社會恰恰呼喚著感性對意義的直接建構,因為唯有這樣的意義活動才是快速的、直接的。
可見,視覺形式的自律之所以成為視覺現代性的標志是由于它呼應了現代感知方式,這時的形式以及與之對應的單純視看已經與以往不同,成為一種新的唯現代性特有的感知方式。它最初由現代人的視覺創造刻意生產出來,后來就一步一步鑄成了現代人特有的視覺審美方式,以至自律的形式,單純視覺上的意義建構成了現代人視覺生活中的一個審美追求。
四、形式自律的文化維度
從感知層面看,形式自律的內核是感性對意義的直接建構。正因為如此,才沒有中介,才沒有其他非視覺性因素的介入,也正因為如此,才是快速的、短暫的,進而是現代的;而他律的形式則是在其他非視覺性因素的介入下被感知的,因而并不是感性對意義的直接建構,而是間接的、有中介的,也正因為如此才不是瞬間的,因為所滲入的其他因素大多是知性或理性等非感性因素,較之于感性,這些都是相對確定而穩固的。由此,形式自律中就蘊含著一個特有的背反:一方面,由于專注于感性,沒有了其他意識活動的介入,有了獨立自足;另一方面,由于單純感性人的感知活動又開始轉向一體化,進而又失落了獨立自足性,因為感性是人之間最相近的意識活動,趨同使其失落了獨特性。深究之,圍繞著獨特性而來的這個背反其實并不矛盾,它昭示出了形式自律乃至視覺現代性問題上的深層文化蘊藉。
視覺形式的自律使視看變得純粹和獨立,變得不再或少有其他非視覺因素的滲入。由此而來的獨特性是建立在單純感性基礎上的,是相對于其他非視覺性意識活動而言的。沒有了知覺和理性活動的介入,單純筑基于感性的視看雖然顯得獨特,但同時又帶有著另一種非獨特性,一種基于人之共有感性活動而來的共性。在非自主的視覺形式中,感知是在知覺或理性活動的介入下發生的,這時,感知雖然不獨立,但卻擁有著人之間不盡相同的知覺內涵。由是觀之,視覺形式的自律與他律使得視覺感知擁有了不同的獨特性與可公約性。自律形式是建立在感性獨立建構意義基礎上的,它的獨特是因為沒有了知覺和理性活動的介入,它的不獨特是因為人盡相同的感性活動;他律形式是建立在知性、理性建構意義基礎上的,它的不獨特是因為感性形式中有了其他非感性內涵的滲入,它的獨特是因為知覺或理性這些非感性活動是人之間不盡相同的。換言之,就感性層面看,人之間顯得非常相同;就知覺或理智層面看,人之間就顯得不太相同。因此,視覺形式的自律與他律其實顯示出了不同層面的獨特性與可公約性。兩者都是就感知活動而言,自律形式的獨特指向的是感知構成的單一性和純粹性,感知活動中沒有或少有其他因素的介入;他律形式的獨特指向的是由感知內容的差異性,不同時空點的知覺或理性活動呈現出明顯的差異性。自律形式的可公約性指向的是感知層面自發的共性特征,而他律形式的可公約性指向的則是感知活動中可復得的知性或理性內容,這些內容往往可脫離感性形式而寓居于其他非感性形式中,如范疇、概念等。這種不同層面的獨特性和可公約性指向使得自律與他律形式具有著完全不同的文化蘊藉。
自律的視覺形式首先在創造著一種全新的感性活動,一種不受知性和理性活動影響的獨立感知活動,謂其“新”是因為不同于日常視看,日常視看總是程度不等地擁有著那些影響的,尤其現代生活中,這種影響更是侵入到感性生活中。所以,自律的視覺形式在改變著人對現實形式的感知。其次,由于自律形式更依賴于自發的感性活動,知性和理性的介入開始減弱,所以有其野蠻性。“野蠻”是指一味傾向于自發性,拒斥意識活動的調整與制衡,大眾性就是其具體體現。西方20世紀以來文化領域中的現代性批判之所以直指現代文化中的大眾性特點,就是因為其中蘊含著不顧理性調控只顧自發感性效果的特點。自律的形式由此將人引向了一種新的依賴,一種從理性轉向感性的依賴,所以“野蠻”。
可是,單用“野蠻”或許還不足以說明問題,因為這樣的謂詞是筑基于理性判斷的,而自律的形式恰恰要拒斥理性活動的滲入,它本來就是要拒斥理性的。所以,問題的關鍵是,在形式審美這樣的文化領域中,理性何以介入,是再回到從前讓形式感知本身就建立在理性知覺基礎上,還是深入到形式感知的現代邏輯中,即感性邏輯中,從中建構出不但有益于個體,而且也使社會受益的維度?答案顯然是后者,因為前者是逆潮流、逆歷史的。但后者是一條前無先例的道路,還有待開拓和建構。
參 考 文 獻
[1] Gottfried Boehm.“Jenseits der Sprache? Anmerkungen zur Logik der Bilder”, in Iconic Turn — Die neue Macht der Bilder, DuMont Literatur und Kunst Verlag, 2004.
[2] Wolf Singer. “Das Bild in uns — vom Bild zur Wahrnehmung”,in Iconic Turn — Die neue Macht der Bilder, DuMont Literatur und Kunst Verlag,2004.
[3] 波德萊爾:《波德萊爾美學論文選》,郭宏安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
[4] Sigrid Schade, Silke Wenk.Studien zur visuellen Kultur — Einfuehrung in ein transdisziplinaeres Forschungsfeld,transcript Verlag Bielefeld,2011.
[5] 本雅明:《波德萊爾: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王涌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
[責任編輯 付洪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