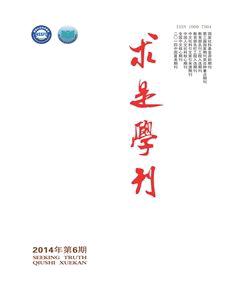族群分裂與宗教沖突:歐洲多元文化主義面臨嚴峻挑戰
摘 要:多元文化主義是西方國家20世紀60年代以來面對多樣性的族群、語言、文化和宗教的矛盾而實施的一項成功的社會政策。進入21世紀以來,由于穆斯林移民在歐洲,特別是西歐國家的迅速增長而導致的歐洲伊斯蘭化的擔憂加劇,國際上反恐政策誘發的歐洲國家,特別是西歐國家內的穆斯林族群與主流族群的分裂以及穆斯林移民的伊斯蘭教文化與基督教文化的沖突,對當代歐洲多元文化主義政策構成了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盡管西歐各國政要紛紛抨擊并宣布放棄多元文化主義政策,但實際上,完全放棄多元文化主義、重新恢復到同化的單一社會政策已幾無可能,新型的多元文化主義是實現歐洲國家族群和諧、宗教文化共榮的唯一路徑。
關鍵詞:多元文化主義;穆斯林族群;伊斯蘭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社會政策
作者簡介:宋全成,男,法學博士,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副院長、社會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從事人口社會學、人口流遷、族群、宗教與社會融合、人口老齡化與社會保障研究。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宗教信仰與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研究”,項目編號: 13JJD730002
中圖分類號:K712.5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504(2014)06-0185-07
20世紀60年代以來興起的多元文化主義,作為西方國家面對族群與文化多樣性、主張尊重差異、追求多元文化并存的重要社會思潮和社會政策,不僅在傳統的移民國家,如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取得了輝煌的成功,而且在傳統的民族國家和非典型意義上的現代移民國家的西歐,同樣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到20世紀末,數以千萬計的來自于不同國度、不同族群、不同文化背景的外國移民,共同和諧生活于歐洲社會,特別是西歐社會的大家庭中。但進入21世紀以來,伴隨著數以百萬計的穆斯林移民大舉進入歐洲,曾引為自豪的歐洲多元文化主義,不斷遭受著穆斯林移民中的極端恐怖主義、族群分裂和文化沖突的強有力的沖擊。由歐洲穆斯林移民實施或引發的英國倫敦地鐵爆炸案、西班牙的馬德里爆炸案、法國的巴黎騷亂和挪威的布雷維克槍擊案,清楚地表明:歐洲多元文化主義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
與以往我國學界對多元文化主義的研究多局限在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傳統移民國家不同的是,伴隨著近年來歐洲國家多元文化主義的危機,我國學界對歐洲國家的多元文化主義的研究逐漸增多。1上述論文主要從移民問題、文化隔離和文明沖突的傳統視角,運用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的觀點,多學科地研究歐洲多元文化主義,本文擬從族群分裂與宗教沖突這兩個視角,運用民族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重新梳理歐洲多元文化主義的產生、發展及其陷入困境的根源。
一、多元文化主義的產生及其發展
多元文化主義的產生有著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一方面,就人口與民族而言,20世紀60年代,西方國家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經濟與社會從恢復到繁榮的快速發展期。這一時期,由于經濟與社會恢復和發展,需要大量勞動力,而本國現有勞動力無法滿足這種需求。于是,西歐國家紛紛實施了吸收外來移民的勞動力市場政策。德國主要吸納了大量的來自土耳其的穆斯林移民,法國接納了來自北非國家的穆斯林移民,英國接納了來自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移民,來自于不同國家、不同文化、不同族群的外國移民紛紛進入西方國家,并逐步成為其常住人口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到60年代達到高潮的戰后殖民主義體系的土崩瓦解,促進了大量殖民地人民向殖民地原宗主國的人口流動。來自于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突尼斯、馬里、尼日爾、馬達加斯加、中非等國家的移民紛紛進入法國;來自于剛果的移民進入比利時;來自于安哥拉、幾內亞比紹和莫桑比克的移民進入了葡萄牙;來自于印度尼西亞的移民進入了荷蘭[1](P301-302)。由此,徹底改變了上述歐洲國家單一的人口結構和民族結構,形成了民族的多樣性。
另一方面,就族群與宗教而言,進入歐洲國家的外國移民族群盡管眾多,但主要是來自阿拉伯國家信奉伊斯蘭教的穆斯林移民。與來自其他族群的移民很快被主流社會同化和融合不同的是,堅守伊斯蘭教信仰的穆斯林移民很難被同化。這是因為“伊斯蘭文化作為一種宗教文化,其核心是伊斯蘭教的宗教意識或思想信仰體系,同時伊斯蘭文化又是一種‘兼具宗教性與民族性雙重特征,但以宗教性特征為主的文化。正是對伊斯蘭教的共同信仰,使得來自不同地區的穆斯林移民產生了強烈的認同意識,并集中居住在特定的區域,形成了穆斯林移民社區”[2],并堅守著獨特的穆斯林文化。到20世紀末,在歐洲的穆斯林族群已成為歐盟國家第一大外來族群,伊斯蘭教也成為歐洲國家除基督教以外的第二大宗教。信仰伊斯蘭教的穆斯林移民的大量存在表明,歐洲國家,特別是西歐國家已具有明顯的宗教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
多元文化主義作為社會政策,最早并沒有產生在多種族、多文化、多宗教的歐洲國家,而是產生于同樣面臨移民問題、民族問題、多語言、多文化問題的傳統移民國家——加拿大。“Multiculturalism第一次使用是在1965年頒布的加拿大《皇家委員會關于雙語主義與雙文化主義的報告》中。報告稱,在加拿大處理英語民族和法語民族關系的方法是Multiculturalism。1971年加拿大政府宣布多元文化主義為國家政策,指出在雙語言的框架內,對于政府而言,一種多元文化主義政策是確保加拿大文化自由的最合適的方法。”[3]這是西方世界第一個宣布實施多元文化主義的國家。在20世紀60年代,英國也放棄了美國社會推行的“熔爐說”,不再致力于同化移民。[4]1966年,英國內政大臣正式確認了移民文化的多樣性,逐漸開始推行多元文化模式。[5](P223)英國理解的“多元文化模式”是指多民族國家中,各個族裔“在社會生活中被賦予廣泛的權利,并受到鼓勵保存它們的文化遺產”[6](P124)。但英國的多元文化主義并沒有上升到社會政策的層面。1973年,澳大利亞也放棄了“我們應該有一種單一的文化,每一個人都以同樣的方式生活,相互理解,有著共同的愿望”[7](P106-107),“我們新來的移民必須在觀點和生活方式方面迅速成為澳大利亞人”[8](P202)的移民同化政策,實施多元文化主義政策。1975年,瑞典繼加拿大和澳大利亞之后,正式宣布在國內實施多元文化主義政策。這是第一個明確實施多元文化主義政策的歐洲國家。20世紀80年代以后,伴隨著西歐國家外來移民的增加所導致的民族、族群、文化與宗教的多樣性,作為解決移民問題、民族問題、文化問題與宗教問題的社會政策,英國、法國、荷蘭、比利時和丹麥等國家,先后實施了不同程度的允許外來移民保持其文化與宗教的多元文化主義政策。到20世紀末21世紀初,歐洲國家,特別是西歐和北歐國家較好地解決了移民問題、族群問題、文化問題和宗教問題,來自世界各地信仰不同宗教的不同種族、不同文化的外國移民,共同生活于歐洲社會的大家庭中,歐洲國家迎來了多元文化主義的輝煌時代。
二、當代歐洲多元文化主義面臨嚴峻挑戰
進入21世紀以來,由于穆斯林移民在歐洲,特別是西歐國家的迅速增長而導致的歐洲伊斯蘭化的擔憂加劇,國際上反恐政策誘發的歐洲國家,特別是西歐國家內的穆斯林族群與主流族群的分裂以及穆斯林移民的伊斯蘭教文化與歐洲基督教文化的沖突,對當代的歐洲多元文化主義政策構成了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
其一,穆斯林移民人口增長迅猛,歐洲人口的伊斯蘭化的擔憂加劇。在歐洲國家的外國移民族群中,篤信伊斯蘭教的穆斯林移民及其族群,較好地保留了自己獨特的生活、文化與宗教。穆斯林族群已成為歐洲國家的第一大外來族群,伊斯蘭教已是歐洲國家的第二大宗教。目前,在歐盟的穆斯林移民已達2000萬~2300萬,約占總人口的5%~6%。預計到2050年,這一比例將達到20%。與歐洲本土人口老齡化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歐洲穆斯林人口相當年輕,在法國生活的500萬穆斯林中,年齡在20歲以下的占1/3,而法國本土人口的這一比例僅占21%;在德國生活的400萬穆斯林中,年齡在18歲以下的占1/3,而德國本土人口的這一比例僅為18%[9](P28);在英國生活的260萬穆斯林中,30歲以下的穆斯林超過穆斯林總人口的60%。[10]這也意味著,隨著時間的推移,歐洲白人的人口出生的減少和穆斯林人口的急劇增加,將最終改變歐洲國家的人口結構。“9·11”以后,歐洲人對穆斯林人口的擴張的恐怖日益劇增。2006年,英國女記者梅勒尼·菲利普在其所著的《倫敦斯坦》中明確指出,英國政府“固執得近乎愚蠢地奉守文化多元主義和道德虛無主義……結果導致倫敦淪為恐怖主義的國際神經中樞”[11](P15),倫敦也將成為“倫敦斯坦”。2010年8月,前德國聯邦銀行董事會成員蒂洛·薩拉辛在《德國自我毀滅》一書中也同樣指出,土耳其、庫爾德以及阿拉伯移民正在破壞德國繁榮的基石,隨著德國人口出生率的下降,這些外來移民正在不斷取代德國人口。[12](P22)美國歷史學家伯納德·劉易斯甚至認為,到21世紀末,歐洲大陸將全面穆斯林化,歐洲將再一次被伊斯蘭征服。[13]法國歷史學家朱斯坦·韋斯在美國《外交政策》雜志上的文章《歐拉伯的荒唐事》中認為:“到2050年,歐洲將會認不出來了。在巴黎的圣日耳曼大道,林立的清真食品店將取代目前的浪漫酒吧;柏林的路標將用土耳其語書寫;奧斯陸和那不勒斯的小學生,將在課堂上朗誦《古蘭經》。”[14]正因為如此,挪威的布雷維克不能容忍歐洲的伊斯蘭化,而在挪威首都奧斯陸和附近的于特島制造了駭人聽聞的、造成77人死亡的爆炸和槍擊事件。布雷維克在其《2083年歐洲獨立宣言》中明確指出:“如果他們在重重困難下放棄多元文化論,如果他們制止穆斯林移民,開始驅逐所有穆斯林,我都會寬恕他們曾犯下的罪行。如果他們直到2020年仍拒絕投降,那就沒有回頭路可走了,我們最終會逐個逐個地消滅他們……到2020年,一旦我們掌權,所有那時未被同化的穆斯林都要被驅逐出境……支持多元化并不意味著就要滅絕自己的文化和人民。”[15]歐洲國家上至政治精英,下至普通民眾對歐洲國家的穆斯林化的擔憂,實際上始終存在,而且日益加劇。
其二,穆斯林族群與歐洲國家主流族群的分裂,誘發了歐洲當代的恐怖主義。盡管歐洲國家的多元文化主義政策的實施,使得歐洲國家的穆斯林及其族群較好地保留了其伊斯蘭教文化和生活方式,但客觀而言,穆斯林族群構成的“社會”并不是歐洲國家主流社會的組成部分,而是一個與歐洲國家的主流社會分裂的、并行的“平行社會”。因此,在伊拉克戰爭打響的時候,本土的歐洲人多支持政府出兵攻打伊拉克,而歐洲國家的穆斯林則多同情伊拉克甚至反對政府出兵。顯然,“這種模式在看似平靜的社會湖面下,隱藏著廣大穆斯林長期被忽視乃至受歧視,無法融進主流社會的怨恨”[16]和憤怒。在這種背景下,歐洲的穆斯林倍感孤獨。“對于那些孤獨的穆斯林后代,歐洲扮演了主人的角色。在名義上,這些穆斯林的后代是歐洲公民,但在文化和社會方面,他們仍然被隔離在外。”[17]于是,歐洲國家的穆斯林,特別是青年穆斯林,在遭遇歐洲國家主流文化的疏離和強烈的生活挫敗感時,極容易對原教旨主義產生同情[18],更熱衷投身于伊斯蘭的“圣戰”事業,來尋求文化認同與民族歸屬感,從而成為國際恐怖主義組織的招募對象。“英國軍情五處和警方均認為,英國境內的許多穆斯林人士都會或直接或間接地支持恐怖主義,特別是那些擁有英國國籍的巴基斯坦穆斯林后裔,或者那些父輩與基地組織有染的英國籍穆斯林,支持恐怖活動的可能性更大。”[19](P139)由此可見,穆斯林族群與歐洲國家主流族群的分裂與穆斯林極端分子發動的、針對歐洲國家政府和主流社會的恐怖主義,正在撕裂著多元文化主義政策。
其三,穆斯林族群信奉的伊斯蘭教文化與歐洲國家主流社會的基督教文化產生了激烈的沖突。從宗教文化的視角來看,歐洲基督教文化、伊斯蘭教文化產生于同一偉大的圣城——耶路撒冷,都是人類創造的宗教文化的兩顆璀璨的明珠。但從歷史上來看,這兩種不同的宗教文化所影響的世界——穆斯林世界和西方世界,卻處于長期的敵對狀態。[20](P280)從中世紀的“十字軍”東征,一直到19世紀,歐洲的基督教徒始終將信奉伊斯蘭教的穆斯林視為“異教徒”和“非我族類”的惡勢力,直到20世紀50—70年代,穆斯林世界掙脫了歐洲殖民主義的統治,獲得民族獨立以后,這兩種宗教及其影響下的民眾的敵對關系,才有所緩解。但是,兩個種族和兩種宗教文化之間的長期對立,最終形成了兩個種族之間的敵對心態。從20世紀60年代一直到21世紀初,由于歐洲國家實施的多元文化主義政策,伊斯蘭教文化和習俗,在歐洲大陸迅速擴展。僅以清真寺的發展為例,“1971年全西歐的清真寺已達607座,1981年增至2124座,1991年又增至4845座,1995年更增至6000座左右。其中,穆斯林人數集中的法國、德國和英國在1991年,分別就有1500座、1000座和600座清真寺。而荷蘭、希臘、比利時等也分別有400座、400座和300 座左右的清真寺”[21]。這引起了一些國家政要和學者的擔憂。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在1978年就曾強調英國民眾“真的非常害怕自己的國家會被來自不同文化的人們所淹沒”[22]。進入21世紀,特別是“9·11”以后,歐洲國家的政府和民眾對伊斯蘭教及其影響的民眾——穆斯林族群的敵視再度從人們的心理中喚起。甚至一些伊斯蘭教的文化與生活習俗,如穆斯林婦女戴頭巾,也被西歐國家的國民看作是蔑視人權、不尊重婦女的充分體現。因此,西歐國家的政府通過立法,禁止穆斯林婦女佩戴頭巾。2004年9月,法國正式實施“頭巾法案”。2011年4月,法國政府正式頒布了“布卡禁令”,該令規定,從4月11日起,在法國,女性將被禁止戴穆斯林頭巾前往公共場所,包括在街頭散步、乘公共汽車、前往銀行、圖書館、商店、醫院、學校、博物館以及電影院等。除了在家里或者宗教場所之外,任何地方戴面紗都屬違法[23]。時任總統薩科奇公開表示:“伊斯蘭頭巾不是一個宗教標志,而是婦女受到壓制的標志。我鄭重地宣布,伊斯蘭頭巾在我們的領土不受歡迎。”[19](P136)“他們認為實施這樣的法律是為了捍衛共和國純潔性,并體現其基本價值觀,即共和國所有公民一律平等,徹底實現政教分離,以此打擊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實現穆斯林移民與法國社會一體化的社會目標。” [24]俄羅斯總統普京,也明確支持在學校禁止穆斯林婦女戴頭巾的做法。[25]由此引發了歐洲國家穆斯林族群和穆斯林社團的強烈反對。顯然,歐洲國家已經陷入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所描繪的伊斯蘭文明與基督教文明的對立與沖突之中,歐洲多元文化主義的文化與社會根基正在被摧毀。
三、歐洲終結多元文化主義何以可能?
曾經盛極一時、廣為贊譽、取得輝煌成就的歐洲多元文化主義,而今正遭受著穆斯林族群人口膨脹、伊斯蘭極端主義分子恐怖主義襲擊和伊斯蘭教影響日益擴大的強有力的沖擊。對此,歐洲主要國家的政要紛紛對多元文化主義政策提出了嚴厲的批評,并主張終結實施多年的多元文化主義政策。人們不禁要問,歐洲多元文化主義還能走多遠?
首先,歐洲多元文化主義政策的倒退。發生在歐洲國家的系列爆炸案和槍擊案,震醒了陶醉在歐洲多元文化主義美夢中的西歐各國政要,他們紛紛表示,放棄多元文化主義政策。德國、英國、法國、荷蘭等國的領導人直言不諱地相繼宣布本國多元文化主義政策的失敗。德國總理默克爾于2010年10月時明確指出:德國構建多元文化社會、讓擁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一起生活的努力“徹底失敗”。因此,穆斯林移民需要努力融入德國社會,學習德語。顯然,德國今后將更加重視以基督教價值作為核心的“德意志主導文化”[19](P135)。2011年2月,英國首相卡梅倫也明確表示: “在國家多元文化主義的原則之下,我們鼓勵不同的文化獨立發展,甚至獨立于主流文化,導致一些年輕的英國穆斯林走向個人極端主義思潮,英國因此也面臨著極端主義的威脅。如果我們要打敗這個威脅,現在是將過去的失敗政策翻過去的時候了。”因為,多元文化的舊政策導致了族群隔離,助長了伊斯蘭極端主義。[19](P136)2011年2月10日,法國總統薩科齊也宣布:法國的多元文化政策已經失敗。他說:“這(文化多元主義)是個失敗,當然我們必須尊重差異,但我們不想要……一個各種團體并存的社會。”“法蘭西國民無法接受生活方式的改變,例如失去男女平等……讓小女孩失去上學的自由。”“我們的穆斯林公民,與其他公民一樣,當然可以信奉他們的宗教。”但“在法國,不想看到人們在大街上用明顯的方式祈禱”[26]。來到法國的新移民必須讓自己認可法國所崇尚的普適價值。2011年6月,荷蘭內政與王國關系大臣認為,“隨著政府移民政策的變化,荷蘭原有的多元文化社會模式將成為歷史”。認為現在有必要采取措施防止各族人民間的隔閡逐漸擴大,這就是重新推廣以荷蘭本土社會價值觀為核心的文化社會政策。[27]由此可見,歐洲國家的多元文化主義政策出現了全面危機,堅持對外國移民實施主流同化的社會政策主張似乎成為主流。
其次,全面終結歐洲多元文化主義政策何以可能。盡管西歐國家的政要紛紛宣布終結實施數十年、曾引以自豪的多元文化主義政策,但實際上,完全放棄多元文化主義政策而回到單一文化主義的同化移民政策的老路上,根本就行不通。一方面,無論是歷史上,還是在現實社會中,每一個國家的文化,都不再是單一民族的、同質的、純粹的一元文化,而是多民族的、異質的多元文化。即使在二戰以前或者穆斯林族群移民歐洲之前,無論是英國、法國,還是德國、荷蘭,都是多民族、多族群文化的統一體。正如蓋瑞斯·詹金斯所言:“正如從來不存在某些本源性的‘英國民族一樣,很顯然也從不存在某種‘純正的英國文化。……每一次移民和侵略——包括凱爾特人、羅馬人、盎格魯-撒克遜人、斯堪的納維亞人和法國諾曼人等——都會添加新元素。這些文化自身也從其他文化吸取營養,就像羅馬文化和希臘文化之間那樣。如此看來,試圖回溯到某個‘根本性的文化是不可能的:文化總是早已經‘不純粹。”[22]上述結論在我們討論法國、德國、荷蘭的本土文化時也同樣有效。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多元文化主義從其根源上來看,并不是當代社會的產物,而是歷史上的常態。因此,當代西歐國家政要試圖放棄多元文化主義政策,而重新回到歐洲國家單一民族的純粹本土文化的路上,無論如何,都是不可能實現的。另一方面,放棄多元文化主義政策,實施以往曾經實施的對外國移民的同化政策,也是不可能實現外國族群,尤其是篤信伊斯蘭教的穆斯林族群與西歐國家主流文化的社會融合的。從歷史上看,傳統的移民國家如澳大利亞、加拿大,非傳統意義上的現代移民國家如西歐國家,對待外國移民,都曾采取過嚴厲程度不同的同化主義的移民政策。但實踐證明,在擁有眾多族群、多種族、多宗教文化并立的國度,這種同化主義的移民政策無法實現外國移民與移民國主流社會融合的目標。從這個意義上看,在目前多民族、多族群、多文化、多宗教同時并存,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的歐洲國家,面對著日益強大的穆斯林族群和伊斯蘭教,完全終結多元文化主義政策,實施同化主義政策,實現穆斯林族群與歐洲國家族群的融合以及伊斯蘭教與基督教的完全融合,都是根本不可能的。
最后,新型多元文化主義政策是解決歐洲國家族群分離、民族分裂和宗教沖突的唯一現實路徑。實施多年的現行的多元文化主義政策之所以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最重要的原因是:
其一,現行的多元文化主義政策暗含著歐洲國家主流民族的基督教“核心文化”與少數民族穆斯林的伊斯蘭“邊緣文化”之分,并給予了區別對待。西歐國家從來就沒有平等對待主流族群與外來族群以及分屬于上述不同族群的宗教文化,在多元文化主義的政策下,充滿了對日益壯大的穆斯林族群及其篤信的伊斯蘭教文化的歧視。從族群的視角來看,歐洲國家的民族優越感和排外情緒始終存在。穆斯林族群在教育、就業、社會參與和政治參與等方面始終處于被歧視的邊緣位置,盡管他們出生和成長在這個國家,可以說流利的英語、法語、德語和荷蘭語,但他們屬于被排斥于主流社會之外的二等公民。從族群篤信的宗教來看,盡管在歐洲國家建立了數以千計的穆斯林清真寺,但其建設的資金來源和在清真寺中布道講經的伊瑪目,普遍來自于同樣信奉伊斯蘭教的其他阿拉伯國家如阿聯酋、科威特、伊拉克等,而不是歐洲國家。在這種背景下,篤信伊斯蘭教的歐洲穆斯林如何從歐洲國家獲取民族身份和國家公民身份的雙重認同呢!
其二,歐洲的穆斯林族群不應當拒絕融入歐洲國家的主流社會,在篤信和捍衛的伊斯蘭教偉大的同時,同樣接納偉大的基督教的存在,而不是將其視為水火不容的異教。歐洲國家的穆斯林沒有融入歐洲國家的主流社會,除了遭受歐洲國家的種族歧視以外,也與自己的“自我封閉”、自覺與歐洲國家的主流社會“隔離”緊密相關。另外,穆斯林所信奉的、謀求拯救世界的伊斯蘭教極大地激發了穆斯林信徒的宗教感情,信徒們也都視它為不容置疑的真理。正因為如此,以捍衛伊斯蘭教為名的一切行為似乎也都是合理的。但這背后隱藏的是穆斯林對伊斯蘭教信仰的惡性膨脹的自尊、缺乏對信奉基督教的“異教徒”的宗教寬容和對基督教同樣拯救人類和世界的肯定。基于此,傳統的多元文化主義政策必須變革和創新——創建新型的多元文化主義政策。
新型的多元文化主義政策,將“不是一種文化擁有優于另一種文化的特權,而是平等地對待所有的文化,將其視為更大的社會的一部分,這些文化因素只會有助于社會的發展,而不會對社會產生有害的影響。少數民族和主體民族都應該拋棄自身文化中的狹隘因素,以一種寬容的態度尊重彼此的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念。促進多元文化的發展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多民族共生,不僅不會導致文化根基的喪失和社會的分裂,相反能促進文化上的認同感”[28]。顯然,這種新型的多元文化主義政策,具有三個鮮明特點:一是確立對待不同文化的平等性和不同文化的社會進步性;二是堅守不同民族文化與宗教都應具有的寬容精神;三是擴展不同文化的共生和認同根基。只有堅持和實施這種新型的多元文化主義政策,歐洲國家才能面對民族、族群、宗教和文化的多樣性的不可逆轉的現實,恰當地處理主體民族與少數民族(尤其是信奉伊斯蘭教的穆斯林族群)、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之間的關系,才能實現歐洲國家族群和諧共處、多元文化共同繁榮的宏偉目標。
毫無疑問,歐洲地區的人種、族群、文化和宗教的日趨多樣性,已經成為歐洲國家必須面對的、不可更改的社會現實和發展趨勢,這就注定了單一同化主義政策必將失敗。盡管傳統多元文化主義面臨著嚴峻挑戰,但不斷完善和豐富的新型多元文化主義依然是歐洲國家消除主體民族與包括穆斯林族群在內的外來族群的分裂狀態,實現基督教、伊斯蘭教及眾多文化的共同繁榮的唯一現實路徑。
參 考 文 獻
[1] J.Klaus Bade,Europa in Bewegung,Migration vom Spaeten 18.Jahrhundert bis zur Gegenwart. Muenchen: Verlage,C.H.Beck,2002.
[2] 趙萬智:《從頭巾到長袍:法國穆斯林女性服飾政治化背后》,載《中國穆斯林》2010年第5期.
[3] 楊洪貴:《多元文化主義的產生與發展探析》,載《學術論壇》2007年第2期.
[4] 洪霞:《當代英國的穆斯林問題》,載《南京大學學報》2006年第2期.
[5] Christian Joppke. Immigration and the Nationstate: the United States, Germany, and Great Britain. New York:Oxford, 1999.
[6] 安東尼·史密斯:《全球化時代的民族與民族主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
[7] Geoffery Bolton. The Oxford History of Australia : the Middle Way,1942—1995,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8] 里查德·懷特:《創造澳大利亞》,楊岸青譯,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
[9] Timothy M. Savage. “Europe and Islam: Crescent Waxing, Cultures Clashing”, i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7,No. 3, Summer 2004.
[10] European Muslim Network, Profile of the United Kingdom, http: / /www.euromuslim.net/ index.php/islam - in-europe/country-profile, 2009.
[11] Melanie Phillips.Londonistan.San Francisco: Encounter Books,2006.
[12] Thilo Sarrazin.Deutschlandschafft sich ab: Wie wir Unser Landaufs Spiel Setzen.Deutsche Verlags-Anstalt; Auflage,2010.
[13] Christopher Caldwell, “Islamic Europe?”Oct. 4, 2004, http: / /www. weeklystandard. com /Content/Public /Articles/000/000 /004/685ozxcq. asp.
[14] 張星慧:《歐洲推行多年的多元文化已經失敗?》,載《中國青年報》2011年7月30日.
[15] 董玉潔:《多元文化主義在歐洲:一場游戲一場夢》,載《世界知識》2011年第16期.
[16] 李環:《淺析歐洲的“伊斯蘭挑戰”》,載《現代國際關系》2009年第9期.
[17] 丁剛:《文化融合影響全球政治》,載《環球時報》2005年8月3日.
[18] In Great Britain, Muslims Worry about Islamic Extremism, August 10, 2006.
[19] 張娟主編:《恐怖主義在歐洲》,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2.
[20] 宋全成:《歐洲移民研究:20世紀的歐洲移民進程與歐洲移民問題化》,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7.
[21] M. A.Kettani. Challenges to the Organization of Muslim Communities in Western Europe. Netherlands:KokPharos Publishing House, 1998.
[22] 蓋瑞斯·詹金斯:《文化與多元主義》,載《國外理論動態》2012年第6期.
[23] 衛報:戴“穆斯林頭巾”在法國被禁,http://style.sina.com.cn/news/f/2011-03-07/103774819.shtml.
[24] 宋全成:《論法國移民社會問題》,載《求是學刊》2006年第2期.
[25] Putin Backs Hijab Ban in Russia Schools,http://www.onislam.net/english/news/europe/460521-putin-backs-hijab-ban-in-russia-schools.html.
[26] 孫力舟:《薩科齊宣布文化多元主義已經失敗》,載《青年參考》2011年第2期.
[27] 新華網:《荷蘭政府稱將放棄多元文化社會政策》,http://money.163.com/11/0617/23/76PPDV6S00253B0H.html.
[28] 方長明:《歐洲多元文化主義的危機與反思》,載《中南民族大學學報》2012年第4期.
[責任編輯 王雪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