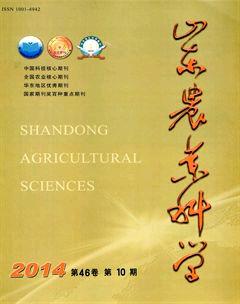不同小麥品種(系)株高及節間長度研究
崔淑佳 潘曉萍 高居榮 等
摘要:對矮稈、中稈、高稈共20個小麥品種(系)的株高及各節間長進行研究,結果表明:矮稈小麥主要是通過縮短不同節間長度來降低株高,特別是基部節間;株高相近的品種(系)同一節間占株高的比例基本相同,株高類型不同的品種(系)其節間比例的變化相對較大;兩個小偃麥矮稈種質31504-1和31505-1株高構成指數IL明顯大于其它小麥,說明其抗倒伏性更穩定,這對小麥株高的遺傳改良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小麥;株高;節間長度;株高構成指數
中圖分類號:S512.103.4文獻標識號:A文章編號:1001-4942(2014)10-0019-04
3討論與結論
倒伏限制了小麥的高產及品質性狀,而倒伏性受多種因素影響,其中株高和莖稈質量是最重要因素[14,15]。株高和各節間構成指數高低可反映出植株抗倒能力的強弱[16],陳曉光等[17]的研究表明,小麥莖稈基部節間長度與抗倒性呈顯著負相關,基部節間比例小的植株具有較強的抗倒性。安呈峰(2008)[13]認為植株高度與株高構成指數呈負相關,植株越矮,株高構成指數IL越大,植株的穩定性越好,越不容易倒伏。
近10年來,河南和山東兩省小麥的產量潛力仍在繼續增長,但兩地的小麥株高變化相對較穩定[18]。育種實踐也證明過分強調株高的矮化,并不能完全解決高產與倒伏的矛盾,反而可能會帶來一些負面影響[11],所以植株并不是越矮越好,一般認為株高在75~85 cm的品種不易發生倒伏且能發揮品種的增產潛力[19,20]。此外,莖稈質量對植株倒伏性的影響也不容忽視[5]。因此,應該研究植株的抗倒伏機制和進行種質的篩選來培育強稈抗倒伏種質[18],以實現小麥的高產、穩產目標。
本實驗室在前期研究中從小麥-偃麥草后代中獲得了一系列矮稈種質系,如31504-1、31505-1等,這些小偃麥矮稈種質系株高均在55 cm左右,多年多點種植表明其株高表現穩定且后期不早衰,在小麥遺傳改良育種中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21~23]。本研究對矮稈、中稈、高稈小麥共20個材料進行株高及各節間長度、比例、構成指數的分析,結果表明:不同株高類型的小麥穗長變化不顯著,各節間的長度變化很大,說明矮稈小麥是通過縮短不同節間長度來降低株高的;但是倒3、倒4、倒5節間長度下降明顯,在株高組成中的比例明顯降低,在不同高度的植株中存在很大差異,推測這些基部節間長度與矮稈小麥株高的降低有關。我們利用矮稈材料與高稈材料構成的分離群體的株高調查結果也得出類似的結論(結果將另文發表)。另外,株高相近的不同材料同一節間占株高的比例基本相同,但株高類型不同的小麥材料其節間比例的變化相對較大。
一般認為株高構成指數大,植株抗倒能力強。本研究分析了不同株高類型材料的株高構成指數IL及各節間構成指數,結果表明植株的抗倒性與株高構成指數IL正相關,驗證了上述結論[14]。且本實驗室新選育的兩個小偃麥矮稈種質31504-1和31505-1株高構成指數IL明顯大于其它矮稈小麥,說明其抗倒伏性更穩定,這對小麥矮化育種及遺傳改良具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1]
Hedden P. The genes of the green revolution[J]. Trends in Genetics,2003,19(1):5-9.
[2]李杏普,蘭素缺,李孟軍. 小麥矮稈基因[M]. 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10.
[3]康蘇花,蘭素缺,李杏普,等. 小麥矮稈基因的研究進展[J]. 河北師范大學學報, 2010,34(1):93-97.
[4]Kelbert A,Spaner D,Bfiggs K G,et a1. The association of culmanatomy with lodging susceptibility in modern spring wheat genotypes[J]. Euphytica,2004,136:211-221.
[5]閔東紅,王輝,孟超敏,等. 不同株高小麥品種抗倒伏性與其亞性狀及產量相關性研究[J]. 麥類作物學報,2001,21(4):76-79.
[6]楊學舉,彭俊英,李宗智. 小麥株高與早衰及倒伏關系的研究[J]. 農業新技術,1990, 8(1):17-18.
[7]姚金保,馬鴻翔,姚國才,等. 小麥抗倒性研究進展[J]. 植物遺傳資源學報,2013, 14(2):208-213.
[8]安呈峰,王延訓,畢建杰,等. 高產小麥生育后期影響莖稈生長的生理因素與抗倒性的關系[J]. 山東農業科學,2008(7):1-4.
[9]姚金保,任麗娟,張平平,等. 小麥株高構成指數的遺傳分析[J]. 江蘇農業學報,2011, 27(5):933-939.
[10]劉和平,程敦公,吳娥,等. 黃淮麥區小麥倒伏的原因及對策淺析[J]. 山東農業科學, 2012,44(2):55-56.
[11]張志強,付晶,王奉芝,等. 小麥抗倒性研究進展[J]. 安徽農業科學,2013,41(5):2020-2022.
[12]魏燮中,吳兆蘇. 小麥植株高度的結構分析[J]. 南京農學院學報,1983(1): 14-21.
[13]安呈峰. 高產小麥發育后期基部節間與倒狀的關系[D]. 泰安:山東農業大學,2008.
[14]王勇,李朝恒,李安飛,等. 小麥品種莖稈質量的初步研究[J]. 麥類作物,1997,17(3):28-31.
[15]劉唐興,官春云,雷冬陽. 作物抗倒伏的評價方法研究進展[J]. 中國農學通報, 2007,23(5):203-206.
[16]朱新開,王祥菊,郭凱泉,等. 小麥倒伏的莖稈特征及對產量與品質的影響[J]. 麥類作物學報,2006,26(1):87-92.
[17]陳曉光,王振林,彭佃亮,等. 種植密度與噴施多效唑對冬小麥抗倒伏能力和產量的影響[J]. 應用生態學報,2011,22(6):1465-1470.
[18]何中虎,夏先春,陳新民,等. 中國小麥育種進展與展望[J]. 作物學報,2011,37(2): 202-215.
[19]趙倩,梁新明,姜鴻明,等. 小麥矮化對產量及抗倒性的影響[J]. 萊陽農學院學報,1999,16(3):168-171.
[20]徐相波,張愛民,李新華,等. 小麥矮源的利用和矮稈基因的研究進展[J]. 核農學報,2001,15(3):188-192.
[21]石濤,王洪剛,何方,等. 小麥矮稈新基因的SSR標記[J]. 山東農業科學,2008(8):1-5.
[22]Chen G L,Zheng Q,Bao Y G,et al. Molecular cytogenetic identification of a novel dwarf wheat line with introgressed Thinopyrum ponticum chromatin[J]. Indian Academy of Sciences,2012,37(1):1-7.
[23]陳桂玲. 小麥-長穗偃麥草矮稈種質系的遺傳分析與矮稈基因標記定位研究[D]. 泰安:山東農業大學,2011.
摘要:對矮稈、中稈、高稈共20個小麥品種(系)的株高及各節間長進行研究,結果表明:矮稈小麥主要是通過縮短不同節間長度來降低株高,特別是基部節間;株高相近的品種(系)同一節間占株高的比例基本相同,株高類型不同的品種(系)其節間比例的變化相對較大;兩個小偃麥矮稈種質31504-1和31505-1株高構成指數IL明顯大于其它小麥,說明其抗倒伏性更穩定,這對小麥株高的遺傳改良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小麥;株高;節間長度;株高構成指數
中圖分類號:S512.103.4文獻標識號:A文章編號:1001-4942(2014)10-0019-04
3討論與結論
倒伏限制了小麥的高產及品質性狀,而倒伏性受多種因素影響,其中株高和莖稈質量是最重要因素[14,15]。株高和各節間構成指數高低可反映出植株抗倒能力的強弱[16],陳曉光等[17]的研究表明,小麥莖稈基部節間長度與抗倒性呈顯著負相關,基部節間比例小的植株具有較強的抗倒性。安呈峰(2008)[13]認為植株高度與株高構成指數呈負相關,植株越矮,株高構成指數IL越大,植株的穩定性越好,越不容易倒伏。
近10年來,河南和山東兩省小麥的產量潛力仍在繼續增長,但兩地的小麥株高變化相對較穩定[18]。育種實踐也證明過分強調株高的矮化,并不能完全解決高產與倒伏的矛盾,反而可能會帶來一些負面影響[11],所以植株并不是越矮越好,一般認為株高在75~85 cm的品種不易發生倒伏且能發揮品種的增產潛力[19,20]。此外,莖稈質量對植株倒伏性的影響也不容忽視[5]。因此,應該研究植株的抗倒伏機制和進行種質的篩選來培育強稈抗倒伏種質[18],以實現小麥的高產、穩產目標。
本實驗室在前期研究中從小麥-偃麥草后代中獲得了一系列矮稈種質系,如31504-1、31505-1等,這些小偃麥矮稈種質系株高均在55 cm左右,多年多點種植表明其株高表現穩定且后期不早衰,在小麥遺傳改良育種中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21~23]。本研究對矮稈、中稈、高稈小麥共20個材料進行株高及各節間長度、比例、構成指數的分析,結果表明:不同株高類型的小麥穗長變化不顯著,各節間的長度變化很大,說明矮稈小麥是通過縮短不同節間長度來降低株高的;但是倒3、倒4、倒5節間長度下降明顯,在株高組成中的比例明顯降低,在不同高度的植株中存在很大差異,推測這些基部節間長度與矮稈小麥株高的降低有關。我們利用矮稈材料與高稈材料構成的分離群體的株高調查結果也得出類似的結論(結果將另文發表)。另外,株高相近的不同材料同一節間占株高的比例基本相同,但株高類型不同的小麥材料其節間比例的變化相對較大。
一般認為株高構成指數大,植株抗倒能力強。本研究分析了不同株高類型材料的株高構成指數IL及各節間構成指數,結果表明植株的抗倒性與株高構成指數IL正相關,驗證了上述結論[14]。且本實驗室新選育的兩個小偃麥矮稈種質31504-1和31505-1株高構成指數IL明顯大于其它矮稈小麥,說明其抗倒伏性更穩定,這對小麥矮化育種及遺傳改良具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1]
Hedden P. The genes of the green revolution[J]. Trends in Genetics,2003,19(1):5-9.
[2]李杏普,蘭素缺,李孟軍. 小麥矮稈基因[M]. 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10.
[3]康蘇花,蘭素缺,李杏普,等. 小麥矮稈基因的研究進展[J]. 河北師范大學學報, 2010,34(1):93-97.
[4]Kelbert A,Spaner D,Bfiggs K G,et a1. The association of culmanatomy with lodging susceptibility in modern spring wheat genotypes[J]. Euphytica,2004,136:211-221.
[5]閔東紅,王輝,孟超敏,等. 不同株高小麥品種抗倒伏性與其亞性狀及產量相關性研究[J]. 麥類作物學報,2001,21(4):76-79.
[6]楊學舉,彭俊英,李宗智. 小麥株高與早衰及倒伏關系的研究[J]. 農業新技術,1990, 8(1):17-18.
[7]姚金保,馬鴻翔,姚國才,等. 小麥抗倒性研究進展[J]. 植物遺傳資源學報,2013, 14(2):208-213.
[8]安呈峰,王延訓,畢建杰,等. 高產小麥生育后期影響莖稈生長的生理因素與抗倒性的關系[J]. 山東農業科學,2008(7):1-4.
[9]姚金保,任麗娟,張平平,等. 小麥株高構成指數的遺傳分析[J]. 江蘇農業學報,2011, 27(5):933-939.
[10]劉和平,程敦公,吳娥,等. 黃淮麥區小麥倒伏的原因及對策淺析[J]. 山東農業科學, 2012,44(2):55-56.
[11]張志強,付晶,王奉芝,等. 小麥抗倒性研究進展[J]. 安徽農業科學,2013,41(5):2020-2022.
[12]魏燮中,吳兆蘇. 小麥植株高度的結構分析[J]. 南京農學院學報,1983(1): 14-21.
[13]安呈峰. 高產小麥發育后期基部節間與倒狀的關系[D]. 泰安:山東農業大學,2008.
[14]王勇,李朝恒,李安飛,等. 小麥品種莖稈質量的初步研究[J]. 麥類作物,1997,17(3):28-31.
[15]劉唐興,官春云,雷冬陽. 作物抗倒伏的評價方法研究進展[J]. 中國農學通報, 2007,23(5):203-206.
[16]朱新開,王祥菊,郭凱泉,等. 小麥倒伏的莖稈特征及對產量與品質的影響[J]. 麥類作物學報,2006,26(1):87-92.
[17]陳曉光,王振林,彭佃亮,等. 種植密度與噴施多效唑對冬小麥抗倒伏能力和產量的影響[J]. 應用生態學報,2011,22(6):1465-1470.
[18]何中虎,夏先春,陳新民,等. 中國小麥育種進展與展望[J]. 作物學報,2011,37(2): 202-215.
[19]趙倩,梁新明,姜鴻明,等. 小麥矮化對產量及抗倒性的影響[J]. 萊陽農學院學報,1999,16(3):168-171.
[20]徐相波,張愛民,李新華,等. 小麥矮源的利用和矮稈基因的研究進展[J]. 核農學報,2001,15(3):188-192.
[21]石濤,王洪剛,何方,等. 小麥矮稈新基因的SSR標記[J]. 山東農業科學,2008(8):1-5.
[22]Chen G L,Zheng Q,Bao Y G,et al. Molecular cytogenetic identification of a novel dwarf wheat line with introgressed Thinopyrum ponticum chromatin[J]. Indian Academy of Sciences,2012,37(1):1-7.
[23]陳桂玲. 小麥-長穗偃麥草矮稈種質系的遺傳分析與矮稈基因標記定位研究[D]. 泰安:山東農業大學,2011.
摘要:對矮稈、中稈、高稈共20個小麥品種(系)的株高及各節間長進行研究,結果表明:矮稈小麥主要是通過縮短不同節間長度來降低株高,特別是基部節間;株高相近的品種(系)同一節間占株高的比例基本相同,株高類型不同的品種(系)其節間比例的變化相對較大;兩個小偃麥矮稈種質31504-1和31505-1株高構成指數IL明顯大于其它小麥,說明其抗倒伏性更穩定,這對小麥株高的遺傳改良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小麥;株高;節間長度;株高構成指數
中圖分類號:S512.103.4文獻標識號:A文章編號:1001-4942(2014)10-0019-04
3討論與結論
倒伏限制了小麥的高產及品質性狀,而倒伏性受多種因素影響,其中株高和莖稈質量是最重要因素[14,15]。株高和各節間構成指數高低可反映出植株抗倒能力的強弱[16],陳曉光等[17]的研究表明,小麥莖稈基部節間長度與抗倒性呈顯著負相關,基部節間比例小的植株具有較強的抗倒性。安呈峰(2008)[13]認為植株高度與株高構成指數呈負相關,植株越矮,株高構成指數IL越大,植株的穩定性越好,越不容易倒伏。
近10年來,河南和山東兩省小麥的產量潛力仍在繼續增長,但兩地的小麥株高變化相對較穩定[18]。育種實踐也證明過分強調株高的矮化,并不能完全解決高產與倒伏的矛盾,反而可能會帶來一些負面影響[11],所以植株并不是越矮越好,一般認為株高在75~85 cm的品種不易發生倒伏且能發揮品種的增產潛力[19,20]。此外,莖稈質量對植株倒伏性的影響也不容忽視[5]。因此,應該研究植株的抗倒伏機制和進行種質的篩選來培育強稈抗倒伏種質[18],以實現小麥的高產、穩產目標。
本實驗室在前期研究中從小麥-偃麥草后代中獲得了一系列矮稈種質系,如31504-1、31505-1等,這些小偃麥矮稈種質系株高均在55 cm左右,多年多點種植表明其株高表現穩定且后期不早衰,在小麥遺傳改良育種中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21~23]。本研究對矮稈、中稈、高稈小麥共20個材料進行株高及各節間長度、比例、構成指數的分析,結果表明:不同株高類型的小麥穗長變化不顯著,各節間的長度變化很大,說明矮稈小麥是通過縮短不同節間長度來降低株高的;但是倒3、倒4、倒5節間長度下降明顯,在株高組成中的比例明顯降低,在不同高度的植株中存在很大差異,推測這些基部節間長度與矮稈小麥株高的降低有關。我們利用矮稈材料與高稈材料構成的分離群體的株高調查結果也得出類似的結論(結果將另文發表)。另外,株高相近的不同材料同一節間占株高的比例基本相同,但株高類型不同的小麥材料其節間比例的變化相對較大。
一般認為株高構成指數大,植株抗倒能力強。本研究分析了不同株高類型材料的株高構成指數IL及各節間構成指數,結果表明植株的抗倒性與株高構成指數IL正相關,驗證了上述結論[14]。且本實驗室新選育的兩個小偃麥矮稈種質31504-1和31505-1株高構成指數IL明顯大于其它矮稈小麥,說明其抗倒伏性更穩定,這對小麥矮化育種及遺傳改良具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1]
Hedden P. The genes of the green revolution[J]. Trends in Genetics,2003,19(1):5-9.
[2]李杏普,蘭素缺,李孟軍. 小麥矮稈基因[M]. 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10.
[3]康蘇花,蘭素缺,李杏普,等. 小麥矮稈基因的研究進展[J]. 河北師范大學學報, 2010,34(1):93-97.
[4]Kelbert A,Spaner D,Bfiggs K G,et a1. The association of culmanatomy with lodging susceptibility in modern spring wheat genotypes[J]. Euphytica,2004,136:211-221.
[5]閔東紅,王輝,孟超敏,等. 不同株高小麥品種抗倒伏性與其亞性狀及產量相關性研究[J]. 麥類作物學報,2001,21(4):76-79.
[6]楊學舉,彭俊英,李宗智. 小麥株高與早衰及倒伏關系的研究[J]. 農業新技術,1990, 8(1):17-18.
[7]姚金保,馬鴻翔,姚國才,等. 小麥抗倒性研究進展[J]. 植物遺傳資源學報,2013, 14(2):208-213.
[8]安呈峰,王延訓,畢建杰,等. 高產小麥生育后期影響莖稈生長的生理因素與抗倒性的關系[J]. 山東農業科學,2008(7):1-4.
[9]姚金保,任麗娟,張平平,等. 小麥株高構成指數的遺傳分析[J]. 江蘇農業學報,2011, 27(5):933-939.
[10]劉和平,程敦公,吳娥,等. 黃淮麥區小麥倒伏的原因及對策淺析[J]. 山東農業科學, 2012,44(2):55-56.
[11]張志強,付晶,王奉芝,等. 小麥抗倒性研究進展[J]. 安徽農業科學,2013,41(5):2020-2022.
[12]魏燮中,吳兆蘇. 小麥植株高度的結構分析[J]. 南京農學院學報,1983(1): 14-21.
[13]安呈峰. 高產小麥發育后期基部節間與倒狀的關系[D]. 泰安:山東農業大學,2008.
[14]王勇,李朝恒,李安飛,等. 小麥品種莖稈質量的初步研究[J]. 麥類作物,1997,17(3):28-31.
[15]劉唐興,官春云,雷冬陽. 作物抗倒伏的評價方法研究進展[J]. 中國農學通報, 2007,23(5):203-206.
[16]朱新開,王祥菊,郭凱泉,等. 小麥倒伏的莖稈特征及對產量與品質的影響[J]. 麥類作物學報,2006,26(1):87-92.
[17]陳曉光,王振林,彭佃亮,等. 種植密度與噴施多效唑對冬小麥抗倒伏能力和產量的影響[J]. 應用生態學報,2011,22(6):1465-1470.
[18]何中虎,夏先春,陳新民,等. 中國小麥育種進展與展望[J]. 作物學報,2011,37(2): 202-215.
[19]趙倩,梁新明,姜鴻明,等. 小麥矮化對產量及抗倒性的影響[J]. 萊陽農學院學報,1999,16(3):168-171.
[20]徐相波,張愛民,李新華,等. 小麥矮源的利用和矮稈基因的研究進展[J]. 核農學報,2001,15(3):188-192.
[21]石濤,王洪剛,何方,等. 小麥矮稈新基因的SSR標記[J]. 山東農業科學,2008(8):1-5.
[22]Chen G L,Zheng Q,Bao Y G,et al. Molecular cytogenetic identification of a novel dwarf wheat line with introgressed Thinopyrum ponticum chromatin[J]. Indian Academy of Sciences,2012,37(1):1-7.
[23]陳桂玲. 小麥-長穗偃麥草矮稈種質系的遺傳分析與矮稈基因標記定位研究[D]. 泰安:山東農業大學,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