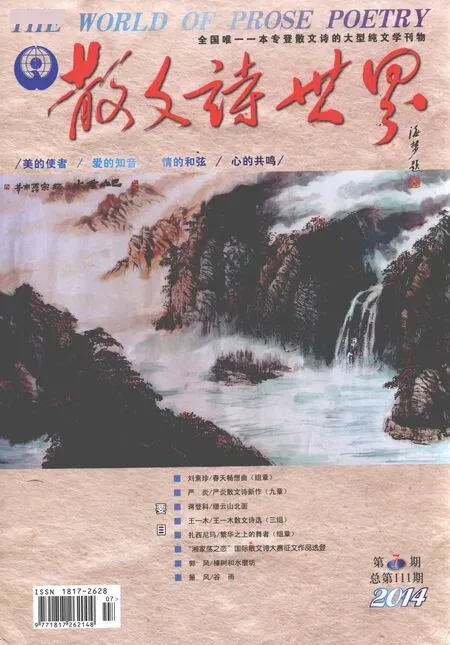虛掩的村莊(組章)
四川 許 星
虛掩的村莊(組章)
四川 許 星
◎ 關于端午
在塔山,沒有一條河流可以直通端午。它們不認識屈原,也不了解兩千多年前的那個典故。只有一些很小的溝渠在五月枯黃的陽光下,期待一場甘霖與這個節日一起擺渡起航。
我想起年少時某些熟悉的往事,那個與塔山一山之隔的觀音橋或者簡家店,莊稼拔節的聲音、綠滿田疇的秧苗、守望的玉米林和母親艾香一樣的微笑,在五月的故鄉搖曳和歌唱。
而在塔山,我卻看到了與母親一樣的艾香與菖蒲,像一杯鄉愁吹散了我滿懷心事和不忍提及的憂傷。雖不再有雄黃與朱砂點我前額,但在嬌妻攤開的粽葉中,我感到愛情的雨水,正一點點打濕我孱弱的身體和迷茫。
在塔山,我將告別許多陳舊的歲月,只對這個節日保守著屬于自己的感動和秘密,因為它的蔥綠、崇高和敬意,像我水上花開的詩句,在每一片貧瘠的土壤、甚至每個早上或者黃昏快樂地發育、成長……
◎ 與妻書
月光傾瀉下來,靜靜地照著你,照著有些發白的彩虹城和愛情已經遲到的窗口。我想起很久前的那個初春,我們是怎樣與一條穿過正午的河流相遇。
你微微膽怯的目光,躲在黃昏的影子背后,觸摸我憂傷的詩句和失落在另一個地方的疼痛。你說我是船你就是帆,你是水我就是岸,我們以蓮的姿勢,傾聽和守望睡夢之外的片片寧靜。
我無法忘記,那些鍵盤和電話的手指總點中我的琴聲、一滴傷心淚或者柔腸,在你倔強甚至剛烈的沖動里痛并快樂。所以,我們常常熱衷于與水溝通,讓身體矮下來再矮下來,不讓太陽陷入一片昏黑。然后像炊煙一樣站起來,喝茶漫步、聊天,像藤和樹一樣熱愛所有的生活。
月光傾瀉下來,靜靜地照著你和我……
◎ 母親的目光
第一次感動母親的目光,是在馬年的正月初二,一壺春酒喝醉了一個家族。他們都說了些什么我不知道,也記不住了。我只記得那天母親非常高興,她不多的話語像一抹清泉,把我溫潤和流淌;她安靜的目光像一根紅線,緊緊拉扯著兩個斷線的風箏,在破碎的天空穿針引線。生怕一松手,那些花開的云彩就跟著春天走了。
母親苦累了一輩子,一男五女就是她全部的家產。父親我沒有見過,據說他當年也走得很匆忙,母親堅強的目光讓我想起自己的父親母親,因為操勞成疾離開了膝下八個弟妹,我們就像走失的羊群,至今都未能圓滿一方水土。其實這完全是我們的罪過,所以,我在蹚過一條小河穿過一片竹林去祭奠這個陌生的父親時,我對母親蒼老的目光充滿了一個準女婿的深深敬意。
春天的陽光很暖和,春天的萬物開始復蘇。我們一步步緊跟在母親的身后,像一株株剛剛萌芽的幼苗,在母親的呵護中盛開成她生命里最美的花朵……
◎ 虎 哥
耿直、豪爽、仗義,還富有男人的情感,這就是我對虎哥的最初印象。其實,虎哥并不屬虎,他的名字里也與虎絲毫不相干。只是,他為了朋友的正義可以找猛虎拼命,為了父母和兄弟姊妹的人格與尊嚴不遭侵犯,他可以裹著睡衣打著赤腳、拖著菜刀,掄起他鐵錘一樣的拳頭,在寒冬的暗處讓某些浮腫的聲勢頂禮膜拜、跪地求饒。當然,虎哥也曾為了自己的所愛去亮劍十里長坡,用一個男人最本真的偉岸,俘獲了表妹花朵般的春心和蕩氣回腸的一世情分。
在我心里,虎哥還是個能掙錢也很顧家的男人。他的某種境界早已超越了我詩歌的意象,比彩虹城更出彩比涪江的河水還淵源流長……
◎ 那個小女孩
看見那個小女孩,我就想起父親母親、兄弟姐妹,想起一些過去了很久的人和事。在破敗的月光下尋找一粒種子取暖,與瘦弱的村莊一起流浪,或者很遲鈍的生活。
所不同的是,那個小女孩完全沒有我生世一樣的過錯,她的出現純屬一場意外。因為不懂愛情,那個丟下她出走的女人可能會隱瞞自己不雅的青春,在男人的浪尖上繼續風吹楊柳,卻始終無法抹去身體的愧疚和一個女人良心的黑夜。對孩子的父親而言,夫妻不過是一場沒有結句的戲,所以走與不走、走多少個他同樣并不在意。他陶醉于激情的鍵盤和那些誘惑的謊言,像落日的余暉,攪動著另外一個冬天的情景和早已扭曲的窗欞。當然這一切,那個小女孩全然不知,依舊撒嬌、貪玩、調皮,甚至還時不時唱一些大人都要臉紅的情歌像小鳥,棲息在爺爺婆婆孱弱的枝頭。
看見那個小女孩,我的眼淚總忍不住流出來。想起那個小女孩,我的心里就很疼很痛……
◎ 我看見莊稼站起來
透過鏡頭之門,我看見大姐和被風撲倒的莊稼在陽光下站起來。憂傷漫過她的額頭,像一片跌倒的鳥鳴,漫過整個村莊。
在大姐的手里,那些倒下的禾苗與孱弱貧窮的生活,也都堅強地站起來,站成一棵樹的偉岸或者河水的秀美。大姐的微笑像一張網,失落與重生,子孫與丘陵就是她心得的全部。大姐常說,莊稼人的前途在農村,只有自己站起來你才能真正理解泥土、花朵以及水和糧食的某些含義,才能真正擁有屬于自己的快樂和希望。
透過鏡頭之門,我看見黑夜肥沃的影子,掛滿了早晨的枝頭。我看見塔山與天空一起無悔地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