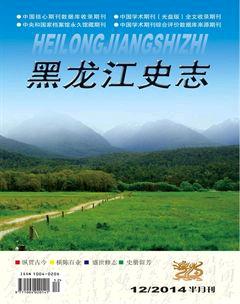從“貞惠”“貞孝”公主墓志看渤海國的女子教育
郭小龍
[摘 要]渤海國作為崛起于東北的地方民族政權,通過不斷的向唐朝學習,迅速由奴隸制末期發展至封建社會,創造了燦爛的文化,并且建立起了較為完善的教育制度,渤海國的女子教育作為渤海國教育體制的一部分,不僅為本國女子接受教育提供了保障,而且對后世遼金女子教育有著重大影響。
[關鍵詞]貞惠;貞孝;墓志;女子教育
前言
建國前的渤海人曾經十分落后。有史籍記載其“無文墨,以言語為約”(1),“無屋宇,并依山水掘地為穴,架木于上,以土搜之,狀如中國之壕墓,相聚而居。夏則出隨水草,冬則人處穴中”(2);“婦人服布,男子衣豬狗皮,俗以溺洗手面,于諸夷最為不潔”(3);“死者穿地埋之,以身襯土,無棺斂之具”(4)。但是,渤海族卻是一個善于學習的民族。渤海建國后不久,渤海第一代王大柞榮就曾多次向唐朝遣使學習先進的統治制度。文王大欽茂即位后,更是積極地“遣使求寫《唐禮》及《三國志》、《晉書》、《三十六國春秋》”(5)等,全面引進儒家經典,學習中原地區的先進思想與文化。
貞惠、貞孝公主分別是唐代渤海國王大欽茂的二女兒和四女兒,兩位公主的墓和墓志是考古界的重大發現,尤其是兩塊墓碑是現今唯一發現的渤海石刻文字,是研究唐代渤海國歷史的重要考古資料。貞惠、貞孝兩公主墓志是典型的駢體文,墓志對仗工整,用典貼切,辭藻華麗,文字簡練,與中原地區漢文學的共同點很多,反映出渤海文學同中原地區漢文學的相互交流和吸收情況。從這些文字中,我們可以看出墓志作者有著較高的中原文學造詣,進而推斷出當時渤海國唐化程度已經很高。該墓志通篇宣講了儒家思想和封建倫理道德,再加上對兩位公主生平事跡的記載使其成為了研究唐代渤海國女子教育的重要資料之一,通過把這篇墓志和唐朝的女子教育的一些資料結合、對比研究,可以了解唐代渤海國的女子教育形式,教育內容等相關問題。
一、渤海國女子教育的形式
渤海國雖然向唐朝學習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教育體系,但無論是中央、地方官學,還是私學都只對男性開放,尚未形成對于婦女的公共教育形式。除宮廷、寺觀等特殊地方外,社會上還未出現“女學”、“女塾”等公共教育場所。從目前所見文獻記載看,民間無論貴族仕宦還是庶民百姓人家,婦女教育基本上都是通過家庭教育形式實施的。家庭教育中,除少數皇室貴族人家有延師教習者外,大多是由父母等家中長輩執教。
(一)宮廷皇族的女子教育
皇室女性的教育對象主要包括皇后、妃嬪、公主等地位高貴的婦女。皇后、嬪妃一向被視為遵循婦禮的典范,她們大多出身于名門世家,因此她們中的很多人入宮之前就具備較高的文化素質和良好的婦德修養。公主作為宮廷女性的重要成員之一,同宮廷其他婦女一樣,總體上來說都受到過較好的道德修養和文化教育。她們雖然不能同太子諸王一樣常置有侍讀官,但是宮中會有通曉詩文、德才兼備的“女師”作為公主們的老師,教以婦德及才藝。
在貞惠公主墓志中有這樣一句:“早受女師之教,克比思齊,每慕曹家之風,敦詩悅禮。”(6)首先“早受女師之教”顯然是指公主幼年時期就已經開始接受教育,而“女師”則有可能有兩種含義,一是教育女子的老師,再就是女老師,無論“女師”的含義是二者中的哪一個,都表明了渤海國的宮廷女子教育已經形成了一定的規范和制度。而下一句中的“曹家”是指東漢著名女性班昭,班昭常出入宮廷,擔任皇后和妃嬪們的教師,“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7),因為她的丈夫曹世叔的緣故,她從夫姓,被稱為曹大家。墓志中通過引用“曹大家”不僅表明公主對集博學和婦德于一身的班昭的向往和敬慕,同時也說明了像班昭這樣博學多才,又有節行法度的女性成為了當時女性的學習典范。
同時期的唐朝宮廷女教制度比較系統和完善,初唐時期宮中即設有內文學館:“宮教博士二人,從九品下。掌教習宮人書、算、眾藝。初,內文學館隸中書省,以儒學者一人為學士,掌教宮人。武后如意元年,改曰習藝館,又改曰萬林內教坊,尋復舊。”這些教育機構負責著后宮內人的教育。另外宮中還有專門的女學士在負責后宮傳授文化,如宋若昭“自憲、穆、敬三帝,皆呼為先生,六宮嬪媛、諸王、公主、駙馬皆師之,為之致敬。”(8)渤海國大行唐化政策,在教育方面也全面仿照唐朝制度,渤海國在上京創建了中央教育機構胄子監,在地方置博士、助教執掌學政負責地方、各類學校的儒學教育。由此可見渤海國在女子教育方面肯定也會學習唐朝制度,只不過不可能像唐朝一樣完備,但從貞惠、貞孝公主墓志當中的內容看,渤海國對于宮廷女子教育還是非常重視的。
(二)普通家庭的女子教育
渤海國雖然是由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但在其政權下不僅生活著靺鞨人,還有漢人、高麗人等諸多民族,雖然在建國初期靺鞨人并不具備很高的文化素養,但和他們一起生活著的漢人和高麗人卻是受到過良好的教育,因此靺鞨人必然在文化上受到他們的影響和熏陶,自然而然的漢人和高麗人對子女的家庭教育也會被靺鞨人效仿和學習。此外,靺鞨作為少數民族還保留有一些母權社會的遺風,女子本身有較高的社會地位,有利于她們接受教育。
古代教育本身有很強的階級性,而女子由于社會角色的原因,她們根本沒有接受學校教育的權力和機會,只能接受不成體系的家庭教育。這里的普通家庭實際要分兩種情況:第一種是與皇族相比而顯得普通的達官權貴家庭,第二種則是真正的普通下層民眾家庭。達官權貴家庭一般生活富足,有能力為自己的女兒邀請到專門的教師教授學業,而下層民眾家庭則大都由父母或者其他長輩對女兒進行教育。
二、渤海國女子教育的內容
(一)道德與知識的教育
我國古代正統女教的內容是圍繞著“四德”之教展開的,《周禮·天官·九嬪》載:“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所以,女子為學“正潔于內,志于四德”(9),渤海國效法唐朝,深受儒家文化影響,在婦女思想教育方面也一定是向唐朝看齊的,無論是貴族、士大夫階層,還是普通的下層民眾都對此十分重視。這一點在貞惠、貞孝公主的墓志中十分明顯。
首先從兩位公主的謚號來看,貞惠、貞孝都是以封建道德標準作為行為規范封贈的。其次墓志中記錄了兩位公主的生平事跡,在她們的生活軌跡中,我們也能看到兩位公主對儒家封建道德實踐。例如,大欽茂的兩個女兒——貞惠公主和貞孝公主的丈夫均先于公主死去,而兩位公主卻被要求“學恭姜之信矢,銜祀婦之哀凄”,銜悲守志,終身不再嫁。盡管兩位公主內心悲痛欲絕,但也只能是“出織室而灑淚,望空閨而結愁”,因為只有這樣,她們才能做到完全“六行孔備,三從是亮”。而“標同車之容儀,葉家人之永貞”則反映出公主通曉為婦之道,恭順事夫,讓家庭關系保持著歡樂和睦。最后,在墓志中將兩位公主和許多古代著名的“有德之婦”進行類比,用以贊揚兩位公主的“婦德昭昭”,如:班昭、其姜杞婦等。
對于婦女學習文化,古來一直有提倡婦女知書以明禮的觀念。班昭就曾批評:“教男而不教女”之弊,認為若要婦女明了“事夫禮義”。就應該令其與男子一樣讀書學習。從出土的石刻和各種文獻記載來看,渤海國應是使用漢字,但中原文化作為渤海國的一種“舶來品”,顯然不是所有人都有學習的機會。貴族、士大夫之家普遍有能力對女兒進行文化教育。女孩多一般自七八歲左右便開始讀書識字、學習詩禮。但普通平常家庭則大都無力為之。是故其時上層社會婦女有文化者眾多,平民婦女則比較少。從貞惠、貞孝公主的墓志中看,她們從小就有專門的老師進行教育,因而可以做到“敦詩悅禮”,并且讀書的范圍也不僅限于儒家正統女子教育的最基本讀物《論語》、《女誡》、《列女傳》之類,對詩書文化也有所涉獵。
(二)生活技能和藝術的教育
“夫婦人之事,存于織纴組紃、酒漿醯醢而已”(10)。我國古代社會女子的主要任務除了傳宗接代、服侍家人以外,還要學習基本的勞動技能,能夠操持家務,勤儉持家。在女子生活技能這樣一方面,各個階層都比較重視,只不過貴族、士大夫階層的女子多停留于表面學習,并不一定要親身實踐。但是下層民眾則必須參加各種社會勞動,所以會更加重視這一方面的教育。
墓志中提到兩位公主“留情組紃”,十分注重對女工的學習。另據史書載,最晚從漢代開始,穢貊族系的居民就已經懂得“養蠶”和“蠶桑作帛”(11)。到了渤海國時期則出現了“顯州之布”、“沃州之綿”、“龍州之綢”等著名產品,而且產量頗具規模,“東丹國初建,約歲貢粗布十萬端,細布五萬端于契丹”(12)。由此可見,學習采桑麻、繅絲織布必定是渤海國女子必修課。此外,除了養蠶繅絲織布以外,準備飯食、教育子女等也是渤海國女子必須學習的生活技能。
渤海國作為一個以少數民族為主建立的國家,他的人民保有少數民族能歌善舞的優秀傳統,歌舞已經融入到了他們的日常生活之中。兩位公主的墓志中記載有:“蕭樓之上,韻調雙鳳之聲”。而且在貞孝公主的墓室中發現了非常精美的“樂伎”壁畫,其中就有一名男扮女裝的樂伎。這些人使用的樂器有拍板、箜篌、琵琶,顯然都是從中原傳入的樂器,這表明渤海國在音樂方面受唐朝的影響很大,因此可以推斷渤海國應該也出現過類似唐朝“教坊”的機構對女性進行音樂方面的教育。舞蹈方面,靺鞨人每逢舉行重大活動時都會載歌載舞,在渤海亡國之后也沒有消亡,依然在其遺裔中流傳著。“歲時聚會作樂,先命善歌善舞者數輩前引,士女相隨,更相唱和,回旋宛轉,號曰‘踏錘”(13)。
結語
渤海國作為東北地區的一個少數民族政權,通過全面的“憲唐”政策,在文化教育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渤海國的女子教育作為其教育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整個渤海國的文化教育的發展有著重大的貢獻。渤海女子和男子一樣用自己的辛勤勞動推動了渤海國整個社會的發展和進步,渤海國女子本身的社會地位較高,有利于她們取得更多的教育機會。渤海國作為繼高句麗之后崛起于東北地區的又一個擁有高度文明的地方政權,將中原文化進一步引入東北,繁榮了東北地區的文化。它的女子教育的形式內容對周邊的民族以及之后的遼金都有著重大的影響。
但是,對于渤海國的女子教育不能過度的拔高,盡管渤海文化在當時已達到相當繁榮的程度,而且有了較完整的教育制度,但這種教育制度對渤海社會的影響從深度和廣度上看都是有限的。從階級上看,名門貴族的女子獲得教育的機會較多;從地域上來看,在統治中心地區(也就是五京地區)女子受教育的現象應是頗具規模,但在其社會經濟發展還很落后的邊遠地區則影響甚微;從教育的內容上來看,名門貴族的女子往往可以獲得倫理思想、文化藝術等一系列較完整的教育,但下層社會的女子則只能接受為婦所需的一些倫理思想和各種生活、生產技能而已。
所以從整體上而言,渤海國女子教育雖然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對社會的進步做出了應有的貢獻。但由于渤海國本身經濟、文化的限制,這種教育的社會基礎比較薄弱,教育形式和內容不夠完善。
參考文獻:
[1](唐)房玄齡等:《晉書·四夷傳》,[M],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
[2](后晉)沈昫等:《舊唐書·北狄傳》,[M],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
[3](唐)魏征等:《隋書·東夷傳》,[M],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
[4](后晉)沈昫等《舊唐書·北狄傳》,[M],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
[5](北宋)王溥:《唐會要·華夷請經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
[6](劉宋)范曄:《后漢書·列女傳·曹世叔妻傳》,[M],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
[7](后晉)劉昫等:《舊唐書·列傳第二》,[M],卷52,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
[8](北齊)魏收:《魏書·列女傳序》,[M],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版。
[9]《契丹國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31頁。
[10]金毓黻:《渤海國志長編·上編》,[M],北京:社會科學戰線雜志社,1988年版。
[11]魏國忠等:《渤海國史》,[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2]高世瑜:《唐代的婦女教育與道德觀》,[J],浙江學刊,2010年,第3期。
[13]周志明:《渤海石刻文獻研究》,[D],東北師范大學,2012年5月。
注釋:
(1)[唐]房玄齡等:《晉書》,《四夷傳》,[M],卷97,中華書局,1975年版,2584頁。
(2)[后晉]沈昫等:《舊唐書》,《北狄傳》,[M],卷199下,北京:中華書局,第5358頁。
(3)[唐]魏征等:《隋書》《東夷傳》,[M],卷81,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1821頁。
(4)[后晉]沈昫:《舊唐書》,《北狄傳》,[M],卷199下,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5358頁。
(5)[北宋]王溥:《唐會要》,《華夷請經史》,[M],卷36,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667頁。
(6)周志明:《渤海石刻文獻研究》,[D],東北師范大學,2012年5月。
(7)[劉宋]范:曄《后漢書》,《列女傳·曹世叔妻傳》[M],卷84,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2785頁。
(8)[后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列傳第二》[M],卷52,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2198頁。
(9)高世瑜:《唐代的婦女教育與道德觀》,[J],浙江學刊,2010年,第3期。
(10)[北齊]魏收:《魏書》,《列女傳序》,[M],卷92,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977頁。
(11)[西晉]陳壽:《三國志》,[M],卷30,《東夷·穢傳》,轉引自魏國忠等《渤海國史》,第361頁。
(12)金毓黻:《渤海國志長編·上編》,[M],社會科學戰線雜志社,1988年版,401頁。
(13)《契丹國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3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