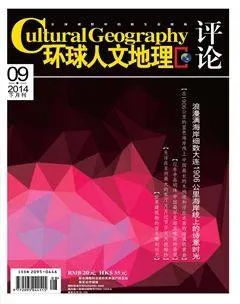海子詩中鄉土靈魂的形成原因初探
劉鵬
摘要:海子嘗試通過詩歌的方式來拯救這個欲望化、精神家園荒蕪的時代。本文以海子的鄉土靈魂的形成原因未切入點,從四個方面解析海子鄉土靈魂成因及鄉土靈魂所體現的詩性精神。
關鍵詞:海子;鄉土靈魂
在中國當代詩壇上,海子是一個神話。從1985年至1989年的5年中,海子創作了數萬行的詩作。細細解析海子詩歌中鄉土靈魂的意象成因,我們可以看到海子對鄉土中國的關注。他對鄉村的描寫,充滿著美好的回憶,但又夾雜著傷感的復雜情緒,海子筆下的鄉村,體現了詩人對生命本真的關注,是詩人詩性精神的彰顯。他將“麥子”“村莊”“土地”等鄉村特有的意象引入詩歌,他用初始的風格,描繪出人類精神家園中古老的幸福,誠摯而不事雕琢,善良而平和,他企圖用詩歌喚醒被金錢、地位所異化的人們,拯救當代人類走出人文精神失落、物質化、欲望化的生存狀態。
一、最初萌生
1964年,海子出生于安徽省懷寧縣高河查灣。海子在農村生活了15年,鄉村文化在海子心底留下了深刻烙印,他在潛意識中眷戀著傳統農業文明。對于鄉村,海子有著深厚的情感。但是海子的童年生活并非如他所抒寫的那樣溫馨、美麗,而是充滿著辛酸,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中國農村,生活極其艱辛。他要從家里背著糧到學校食堂入伙,周末的時候還要到到生產隊干農活掙工分。海子過早地嘗遍了尚無法完全理解的生存困擾,以至于在后來創作大量抒寫糧食和土地的詩歌。麥子、土地、村莊也成了他詩歌的主要意像。如:“《麥地》、《我,以及其它的證人》” 等詩歌,字里行間滲透著詩人對家園的精神追懷以及對故土的深切懷念。
對于每個人而言,故鄉就是他的土地,因此“詩人的天職是還鄉,還鄉使故土成為本源之處”。15年的農村生活所貧困所帶來的創傷在海子的內心烙下了深深的印痕,這種對鄉村眷戀、悲憫而痛苦的復雜情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其鄉土靈魂的最初萌生。
二、抒寫赤子對鄉土的感恩
作為一個出生于農村的都市浪子,海子的內心充徹著對鄉土的感恩。在他筆下,鄉村及土地,如同生養他的慈母嚴父,如同柔情似水的愛人,如同情同手足的弟兄,面對土地的賜予,他意識到個人的卑微渺小,作為農民的兒子,海子在農村生活了15年,因心中的大地和受“人,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之上”理論的啟示,使他自然將鄉土當作生命與藝術激情的源泉。如其《詢問》、<<詩人葉賽寧>>、<<麥地>>、《五月的麥地》詩歌,平靜的語氣掩飾不住心中隱隱的疼痛和酸楚淚水,正是這麥地和光芒的情義,給予他以生命的激情,西川在評論海子與麥子及土地的聯系時有一段精彩的論述:“每一個接近他的人,每一個誦讀過他的詩篇的人,都能從他身上嗅到四季的輪轉、風吹的方向和麥子的成長。泥土的光明與黑暗,溫情與嚴酷化作他生命的本質,化作他出類拔萃、簡約、流暢又鏗鏘的詩歌語言,彷佛沉默的大地為了說話而一把抓住了他,把他變成了大地的嗓子[3]懷著一顆感恩之心,詩人用詩歌報答這份厚重的情義,有誰能像海子這樣虔誠地面對自己的土地和父老鄉親呢?把鄉土當做圣殿來頂禮膜拜,海子為人們呈現了一曲曲動人的感恩之歌。也正是他的這種感恩的赤子之心使其詩歌具有鄉土靈魂。
三、與城市生活的格格不入
在繁華的都市,來自農村的海子顯得格格不入,城市生活的孤獨、困頓時刻都在沖擊著他的內心,海子鄉土靈魂的產生與他所處的社會環境有著密切的聯系。生命的卑微,城市生存的艱難讓他的內心無法安寧,他需要一個支撐。為此海子以都市浪子的姿態不斷回到有著“麥地”、“蘆花”的村莊。“在中國新詩史上的所有詩人中,沒有一個能像海子那樣對糧食和胃給予了那么多刻苦銘心的書寫,并把它釘子一樣鍥成詩歌的詞根。”似乎只有在鄉村自然的庇護下,海子才能真正感受到自己生命的歸屬,才能于城市的逼迫中保持生命的靈性與純樸,得以精神上的安慰。
在這種客觀環境的擠壓下,海子眷戀鄉土自然、排斥工業文明和城市文明的情緒使海子萌發了“我要回家”的強烈愿望,詩人的情感天平自然而然地向未被現代文明侵染的鄉村和自然傾斜,并把之作為靈魂的家園和棲息地,于是,一種想要逃離城市、回歸鄉土的濃厚情感便出現在了海子的詩歌中,遍布麥子、村莊、谷物、河流等意象。他的這種對鄉土的憶念之心一直推動著其鄉土靈魂的形成。
四,經濟制度的改革對其影響
上世紀80年代中期,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市場經濟正在迅速沖破舊有計劃經濟的僵硬型態,拓展著自己的空間。經濟體制的轉變,調侃性的大眾文學蓬勃興起。而海子是農村的兒子,他迷戀泥土,對于伴隨著時代發展而消亡的某些東西,他自然傷感于心。海子的友人西川回憶海子:“1989年初,海子回了趟安徽。這趟故鄉之行給他帶來了巨大的荒涼之感,‘有些你熟悉的東西再也找不到了,他說,‘你在家鄉完全變成了個陌生人”。由此可見,海子是清高、孤傲、正直、不合流俗的。這種精神特質使其對現實社會產生了強烈的抵觸,《祖國(或以夢為馬)》中“我要做遠方忠誠的兒子/和物質的短暫情人”“只有糧食是我珍愛我將她緊緊抱住抱住她/在故鄉生兒育女”,海子排斥商品經濟對文學所帶來的沖擊,發誓要做“遠方忠誠的兒子”,海子蔑視著社會現實,只有故鄉才是他的依靠,只有在故鄉才能尋求詩人精神上的依托。也正是這種對于鄉土的眷戀,對工業文明的不適應造就了其獨特的鄉土靈魂。
五,結語
大眾文學的興起和當時社會對詩人的不信任,另一方面是受到壓制的先鋒文學界內部的互不信任、互不理解、互相排斥。這些矛盾使海子深陷痛苦之中,給他帶來沉重的精神打擊,正是這種沖突與對立讓海子把靈魂寄托在虛無縹渺的大地,大地成了他心靈的“故鄉”,如《重建家園》:“用幸福也用痛苦/來重建家鄉的屋頂”“雙手勞動/慰藉心靈”,這是海子理想中的烏托邦化家園,詩人開始祈望初始,用麥子養活生命,雙手勞動收獲幸福。
【參考文獻】
[1]海德格爾著:《人,詩意地棲居》郜元寶譯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版。
[2] 西川編:《海子詩全集》,《懷念》作家出版社 2009 第11頁
[3]燎原著:《海子評傳(二次修訂本)》中國戲劇出版社2011年6月北京第一版 第21頁
[4]金肽頻主編:《海子紀念文集·散文卷》,西川《死亡后記》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第3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