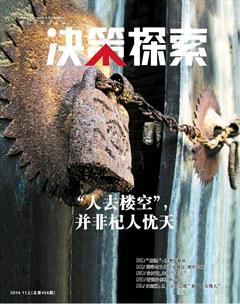返鄉雜記:變局中的農村
張曉陽

中午,老家A村。我坐在老母親身邊,一邊吃著老人家做的面條,一邊聽著她述說鄉鄰的家常里短。某某的女兒離婚了、某某的媳婦不孝順、某某人快不行了。
這一段,我一直對農民生活方式的悄然變化很感興趣,于是問老母親:“村里的人都跑到哪里去了?街上怎么沒見多少人?”
母親說:“在地里干活呢!”
我說:“地不是流轉給別人了嗎?還干啥農活?”
母親說:“給種植大戶打工啊!還有一些有地的村民不想干農活,也會請人干。”
我說:“一天給多少錢?”
母親說:“摘葡萄,一個鐘頭5塊;掰玉米,一個鐘頭10塊。”
我說:“都是咱村人給咱村人干嗎?”
母親說:“是啊。”
母親說的情況,我在其他一些鄉村已有所了解。農村人的生產和以前已經大不一樣了。以前幫別人干農活,誰好意思提錢啊!都是義務幫忙。現在的耕種方式,不提錢不行啦。有這種想法的同時,我明白,對當前的農村大變局而言,我和母親的這段對話,實際上“信息量”很大。
午飯后,我說:“你吃過飯喜歡去打麻將,你去打吧,我不耽誤你。”
母親說:“不去了,沒人,都去干活了,沒人打了。”
我說:“那咱們去大姐家(B村)轉轉吧?”
母親說:“好!”
在去大姐家的半路,遇到我們村的村委副主任正在路邊將自己種的葡萄裝車。副主任年齡比我稍長,是少有的留在村里種地的中年人。
“種了多少畝,老哥?”遞上一根煙,我問他。
“50畝。今年第一年下架,就遇到了連陰雨,前一段葡萄都壞地里了。”
“是,這一段聽說咱縣的葡萄形勢很不好。葡萄能在冷庫里保存不能?”
“冷庫里存不了。一存,口感就不行了。你看我買了這三個大罐,準備釀酒嘞。唉,咱們的葡萄釀酒不行,做鮮葡萄汁應該不錯,可咱不知道咋做。”他撓了撓頭。
“我覺得咱偃師的葡萄現在既然能賣向全國,以后可以大膽地種。種的規模上去了,才能搞后續的加工。如果要做鮮葡萄汁,別自己做品牌,最好和國內的果汁生產品牌企業合作,在偃師建分廠。我原來去過匯源果汁在陜西的生產車間,就建在原產地咸陽市禮泉縣,規模很大。” 我說。
在葡萄地里剛轉了一會兒,就下起雨來。他們忙著裝車,我也就不敢再打攪,繼續上路,往大姐家走。
正走著,路突然由水泥路變成了泥土路。變化就在兩村的交接處。
母親說:“你看B村,就這一小段路,都不舍得修修。”
我笑笑,說:“人家出村不靠這條路,當然不積極了。”
說這話的同時,心中也不是滋味。我知道,一個村,要修一條路,很不容易。而在一定時期內,一個縣把所有農村的路都修了,更不容易。“發展是硬道理”這句話現在放在農村,還非常適用。
剛進入村莊,就看到了B村小學。
我問母親:“這學校咋看著像是廢了?”
母親說:“搬了,搬到C村啦。”
這讓我想起這些年農村的并校問題。農村并校是農村人口大量外流、學生數量銳減的一種選擇。今年夏季我的孩子在鄭州考初中時,真是見識到了農村學生大量涌入城市的中小學去考試的壯觀場面。農村學校的生源快速減少,城市學校的生源高度飽和,這是當前城鄉關系劇烈變化的一個縮影。
到了大姐家門口,敲了大半天門,沒人應。打手機,也不接。正想返回時,大姐突然從一個街口“冒”了出來。
我開玩笑說:“大姐,你怕我蹭你的飯吃,手機也不敢接了!”
大姐說:“啥啊!去地里干了一會兒活兒,下雨了。回來沒事干,就去打麻將了,沒帶手機。”
我說:“姐,既然下雨了,沒事干,別打麻將了,咱們出去轉轉吧。聽說C村有兩個泉眼,離這這么近,從來沒有見過,咱去看看吧?咱這也叫‘旅游啊。”
大姐說:“那有啥看?你要去看,我反正也沒事,走吧!”
當一頭扎進C村時,才發現這個村的泉眼還真不好找。我的車在狹窄的村莊街道上七拐八拐,差點迷了方向。這是個干凈的、人氣還算可以的村莊,能感受到小學和隊部往昔的熱鬧。
我問大姐:“咱們問路遇到的人,咋總是年齡比較大的?”
大姐說:“現在年輕人誰還在村里啊?”
終于,我們到了那處泉眼,它沒有我想象的那么噴涌、活躍, 卻保留有農村少有的神秘和威嚴。這個泉眼實際上是用青石砌護起來的大井筒,直徑有四五米,深不見底。不見泉水流出,但水質很清。泉眼由一棵近百年的皂角樹護衛,正北面還有一個小廟。人們對自然的敬畏,在這里能明顯地感受到。
井旁一戶人家的年輕夫婦正在剝玉米,兩三歲的孩子在旁邊玩耍。我過去和他們嘮了兩句:“兄弟,你們村的地氣很好啊!你看有兩個泉眼,全偃師的村都沒有啊!”
兄弟說:“以前水還往外冒,這幾年旱,水少了。”
我說:“是啊,咱這個泉眼能這樣,估計下邊的水脈不小,今年下雨多了,估計會好點。”
看完了兩個泉眼,開始回家。看到年輕夫婦的孩子,我想起來大姐的外孫女。于是問大姐:“現在農村的小孩子都養得不賴,恁外孫女咋樣了?”
大姐一拍大腿:“哎呀,娃子可憐死了,真受罪了。你不知道,孩子剛生下來9斤,4個月后瘦到8斤啊。”
我知道那個孩子可憐,生下來幾天就開始拉肚子,大夫說腸子有問題。孩子整天拉,最后拉血,我見到時已瘦成皮包骨頭,肚子卻漲得明晃晃的,讓我極為震驚和心酸,感覺孩子可能挺不過去了。這種情況即便在農村,也是很少見。孩子被抱到好幾個大醫院去治療,花了萬把塊錢。
我說:“現在咋樣了?”
大姐說:“好啦!20多斤,胖得跟芝麻轱轆一樣。”
我說:“太好啦!前一段知道好了點,咋治好的?”
大姐說:“說起來我都想噘人!孩子一生下來沒奶,吃奶粉。生病時,一直吃XX牌的奶粉。治了好長時間咋都治不好,后來試著換了奶粉,啥都好啦。孩子治病時我給大夫說是不是奶粉的問題,大夫也沒聽。后來大夫打電話問孩子咋樣了,我把他噘了一頓。”
我對這類問題很敏感:“是不是吃著假的了?”
大姐說:“沒有,別人家孩子吃的都是這個,都沒事。后來化驗了一下,孩子對這種奶粉不適應。”
大姐這樣說,讓我想起很多問題。
送大姐到家,我們開始回家。路上,只有我和老母親在車上,沒人說話。我開著車,看雨刷不停地刷著玻璃上的雨水。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
客觀上講,這些年的農村,村莊、村莊里的人和就業,發生了各自不同的變化。
村:大部分村莊在建設形態上日漸衰落是很明顯的,而且多具有不可逆性。
人:大部分農民的生活相比于自己以前是好了不少,但相比于市民生活的改善程度要落后得多。
業:大部分農業正面臨再次升級的好局勢卻又如此地缺乏全社會的鐘愛和青睞。
在這個農村大變局期,老問題還沒解決好,新問題又大量涌現,恐怕是當前農村的一個真實寫照。我能感受到現在農村的問題,就如同這車玻璃上的雨,剛刷一遍,又來一層。
變局期,我們應該為農民至少做好三件實實在在的事情:一是照顧好農村的老人。“照顧”兩字,需要很多錢。如果沒錢,那就用良心。二是盡一切可能讓農村的孩子有好的學校上。前述兩類人現在正成為農村留守人口的主流。三是認真地對待農村勞動力的就業,讓留在農村土地上的務農中青年有越來越好的經濟收入,看到希望。這些年齡層的人,也將是農村、農業和農民的希望。
個人認為,讓現在留在農村的人各得其所,是現在最需要做的,其他的就別搞太多虛的啦。我知道,這僅僅是最起碼的要求,但恰恰是很起碼的要求,代價和難度往往又是最大的,這個只有親自去做了才知道其中的艱難和曲折。不管怎樣,我們要當好那個雨刷,不停地刷,不停地刷,不停地刷。
(作者系博士、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副教授、偃師市掛職副市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