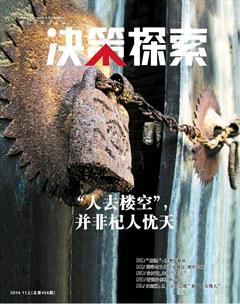未來,誰來種地?
陳穎

10月26日,氣溫驟降至12℃,似乎一夜間冬天就要來了。
李大娘在兒子工作的上海市住了一年多了,這一天,她回到了老家濟源市邵原鎮杏樹洼。回來,是因為那里的吳儂軟語她聽不懂,富麗繁華的大都市也住得不習慣。然而,回到老家,她更是失望:偌大的村子已是空空如也,想找個聊天的人,都要走上幾里山路。
杏樹洼村距市區65公里,地處西部山區,和山西省接壤,散落各處的住戶已是深山不見人。村主任左光明說,村子前后綿延36平方公里,共112戶540口人,如今在村里生活的僅有60余人,一半以上都是像李大娘一樣的老弱病殘。
據資料顯示,不僅在山區,就是平原、丘陵地帶,像這樣的“空心村”在中國也比比皆是,且每天都以20個左右的速度在逐步“萎縮”著。在希望的田野上,那曾經的“微雨重卉新,一雷驚蟄始”的春耕圖已不再,“稻花香里說豐年”的秋收場景已不復,年輕人漸行漸遠,取而代之的是“386199”部隊,即婦女、孩子和老人。
10年、20年之后,當這些老人已垂垂老矣,誰又將接替他們成為農業的后繼者?千種焦慮,萬般愁緒,歸結為一句話:“未來,誰來種地?”
李大娘身體好的時候,種著家里的3畝多地,兒子已在上海定居,他的老伴李大爺到市區打工,可李大娘自去年得了中風后,生活不能自理,老伴只能在家里一邊照顧她,一邊照料田地,農閑時便到村子的養雞場找些零活,每天有100元左右的收入。
他家是杏樹洼村為數不多的還未將土地流轉的幾戶人家之一。其余人家的耕地800多畝、坡地400余畝已經全部流轉給了鄭州的一家源通科技公司。公司在荒坡上種植了杜仲等藥材樹,并建起了養雞場,也就是李大爺打工的地方。
據邵原鎮有關負責人介紹,邵原鎮1.1萬戶,4萬人口,外出務工流出率達41%,耕地總面積3.7萬畝。目前,全鎮共流轉土地2.2萬畝,占全鎮總耕地面積的60%,主要用于發展薄皮核桃、煙草、制種、蔬菜、冬凌草等特色農業。剩余的地塊由于地處山區,水源匱乏,土地條件差,基礎設施薄弱,大多是農民自己種。
距中心城區較近的承留鎮是虎嶺產業集聚區所在地,從業人員達到5.2萬人。該鎮黨委書記高東風說:“承留鎮人口由3年前的不足2萬迅速集聚到5萬多,與農村確權制度密不可分。西部山區3個鎮的很多農民,把確權后的土地流轉出去,放心地進城務工經商,承包地有流轉費,務工有工資,土地和勞動力資源都活了,兩頭掙。”
作為河南唯一的全域城鄉一體化示范區及新型城鎮化綜合改革試點市的濟源市,大力推進農村產權制度改革,促進生產要素合理流動,保障農民財產權益,探索構建新型農村經營體系。確權頒證使越來越多的農民參與土地流轉,土地向種植大戶集中,各種龍頭企業、農業公司、農民合作社、專業大戶和家庭農場也涌現出來。目前,濟源市農村土地流轉率達83.9%,而河南省流轉率是34.8%(截至今年6月),全國的流轉率是26%(截至2013年年底)。
不可否認,濟源市在農村土地流轉方面走得比較快,效果也比較好。然而,就我國農村的發展實際來看,解決“未來誰來種地”問題,依然需要留在農村的有經驗、有能力的農民家庭來承擔。
從世界各國農業發展的實踐來看,家庭經營仍是最普遍的農業經營形式。因為,農業生產的基本特點是空間分散,且必須對自然環境的微小變化及時做出反應,這使得農業生產的監督成本較高。農戶家庭成員之間的經濟利益是高度一致的,不需要進行精確的勞動計量和監督。較之其他經營方式,家庭經營在農業中具有更好的適應性,不僅能適應以手工勞動為主的傳統農業,也能適應采用先進科學技術和生產手段的現代農業。在我國農業現代化過程中,家庭經營蘊藏著巨大的潛力,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不存在生產力水平提高以后改變家庭經營基礎性地位的問題,家庭經營現在是、將來依然是我國農業最基本的經營形式。
為全面了解河南農村土地流轉的現狀和存在的問題,省地方經濟社會調查隊在全省40個縣(市、區),對600個農戶的土地流轉情況進行了問卷調查。調查結果顯示:近年來農村土地流轉規模逐漸擴大。600個農戶中2010年參與土地流轉的有97戶,流轉面積477.8畝;2014年達到379戶,流轉面積1993.5畝。其中70.7%流轉給了土地經營大戶,流轉給一般農戶的占29.3%。
此次問卷調查,發現當前部分地方土地流轉中存在的主要問題:一是流轉土地“非糧”化日益加重。一般農戶流轉土地的“非糧”比例已經高達40%,而土地經營大戶的“非糧”比例更是從2010年的43.7%快速上升至目前的60%。二是政府組織在土地流轉中服務缺失。被調查農戶中只有41.3%的農戶反映當地鄉或村建有土地流轉服務組織。三是強制流轉土地的現象時有發生。四是不簽流轉合同的現象還大量存在。目前,還有37.2%土地流轉農戶沒有簽訂正規合同。五是“非糧”大戶的趨利行為不斷抬升土地流轉費。調查農戶中近1/4的流轉費已經達到或超過2013年規模種糧畝均凈收益1000元的水平,其后果將進一步加重流轉土地的“非糧”甚至“非農”化。
對此,中農辦主任陳錫文也表示:“現在沒有多少人是愿意到農村租了土地繼續種糧的,很多土地被轉租之后‘非糧化、‘非農化的現象必須要被遏制。”對此,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王小映表示,農村土地流轉不能跑偏,在土地流轉過程中,尤其在推進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過程中,要防止一些工商企業資本以投資農業的名義圈占土地、進行土地投機。對工商企業進入農業尤其是受讓土地要做一些管制,因為農業本身經營效益比較低,公司進入農業并大規模承租、受讓土地,要考慮到底會給農業帶來什么?
對于公司經營農業尤其是受讓土地,政府要進行必要的許可管制。哪些行業、哪些產業可以進入?哪些要限制進入?進入農業的公司需要哪些資質、是否必須有經營農業的經驗?能否受讓土地?對這些都要進行必要的政策規范。有一些領域,比如設施農業、農業科研實驗和養殖業,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和高技術投入,這些投入是農民干不了的,政府可以引導公司進入這些領域。對于糧食生產,應當更多地培育種植大戶、家庭農場和農民專業合作社,讓留在農村的有經驗、有能力的農民家庭由“小農”發展成為家庭農場或種植大戶,進行規模化糧食生產。只有這樣,才有利于防止土地“非農非糧化”,有利于國家糧食安全。
很顯然,土地流轉并不是萬能的辦法。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韓俊也認為,當前,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誰來種地”問題比較突出,許多地方已經具備了發展土地適度規模經營的條件,但必須因勢利導、順勢而為,引導土地有序流轉和集中。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在我國這樣一個人多地少的國家,在推進農業現代化過程中,不能脫離實際,片面追求超大規模經營,盲目崇拜國外的大規模農場,要充分認識實現土地適度規模經營的長期性和復雜性。
他說,據估計,我國目前從事糧食生產的勞動力在1.5億人左右。這就是說,全國糧食生產實現規模化經營,尚需轉移1億左右的農業富余勞動力。我國的基本國情決定,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土地是農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農村土地經營權的流轉和集中必然是一個不平衡的、漸進的長期過程。因此,發展適度規模經營,既要積極鼓勵,也不能拔苗助長;既要避免土地撂荒和經營規模過于碎小,又要防止土地過度集中,人為“壘大戶”。一些發展中國家之所以會在大城市周圍形成大片的貧民窟,就是因為農民失去了土地,只能單向流入城市,即使沒有就業機會也無法再返回農村,結果造成了許多嚴重的社會問題。
由此來看,我國未來一個時期家庭經營仍是最普遍和最重要的農業經營形式。“未來,誰來種地?”在濟源市副市長孔慶賀看來,所謂無人種地的擔憂是相對傳統農業來說的,隨著農村改革進程的不斷深化,特別是農業發展方式的切實轉變,一定會有專業的職業農民的出現,比如家庭農場、種田大戶的增多,勢必會帶動農業專門人才的培養和發展。
中國農業大學農民問題研究所所長朱啟臻也認為,加快我國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最有效的途徑就是培養千千萬萬的職業農民。
目前,我國的農村教育以“智識教育”為主,主要對象也是學齡階段的農村青少年,教學內容以升大學為目的,而最終能夠考上大學的在河南等農業大省不足20%。當前的農村教育,無論在目標、體系建設還是內容設計上,都存在強烈“離農化”傾向。從教學內容來看,“象牙塔中辦學”的農村基礎教育使得農村學生缺乏對農村的認同感,更不熟悉農業的基本知識;從教學形式來看,“就教育而教育”的封閉辦學模式使得農村教育難以承擔農村社區文化中心的重擔。
為此,有專家提出,要針對16歲以下的農村青少年引入“雙元制”教育理念,改革現有的農村義務教育模式和內容,糾正“離農化”傾向。可以在“智識教育”的課程之外,增設勞動技能課程,適當安排適應當地需要的勞動技能和技術教育。培育學生的職業興趣,使得技能課程教育能夠更好地貼近農村生產與經濟發展的需要,并使學生在結束義務教育之后能夠有充分的準備選擇未來的職業生涯,為其將來進一步的職業培訓打下基礎。此外,應在課程設置上,適當增加鄉土教材尤其是結合當地實際情況的自編鄉土教材,使得學生加深對農村、對家鄉的熱愛和了解。在教育目標定位上,培養一批立志農村經濟發展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