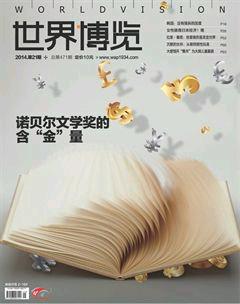明年的奧斯卡,很文藝
風易
導語: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近日公布參與第87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角逐的完整名單。對于中國觀眾而言,中國內地參選作品直到最后時刻才揭曉真容在情理之中。但意料之外的是,這部作品并不是柏林擒熊的《白日焰火》、也不是參展戛納的《歸來》,而是名不見經傳的《夜鶯》。
正文:說到今年代表中國內地"申奧"的《夜鶯》,在中國的國慶節假期期間,就有美國媒體爆料表示該片將會成為代表中國“申奧”。在如今的媒體標題中,《夜鶯》已經和“爆冷”劃上等號,執導此片的法國導演費利普·彌勒也一時間名聲大噪。說到“爆冷”,有趣的是,在本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候選名單中,法國人還創造了一個更大的“冷門”。法國此次的選送作品放棄了去年紅遍世界的金棕櫚佳作《阿黛爾的生活》,而選擇了亮相今年戛納電影節卻反響平平的傳記片《圣羅蘭傳》。外媒一片哀號:“法國人已經自己放棄了今年的奧斯卡獎。”
對于夢想實現“走出去”宏愿的中國電影人來說,誰能獲得參加奧斯卡最佳外語片評選的資格更有一份民族主義色彩。不過,近十年來,中國電影人年年鎩羽而歸,盡管希望不大,但是暢想一番《夜鶯》未來的“爆冷”之路也無妨。《夜鶯》由法國導演費利普·彌勒執導,影片講述了一個矛盾重重的中國家庭中,爺爺與自己的孫女踏上了一段意外不斷又驚喜連連的旅程。導演彌勒在法國的代表作是一部充滿溫情且幽默的影片《蝴蝶》,因此本片也被稱為中國版的《蝴蝶》。
李保田扮演的志根看上去有個幸福的晚年生活,她的女兒倩影(李小冉飾演)是個成功的設計師,她與丈夫崇義(秦昊飾演)結婚多年,有一個聰明伶俐的女兒任幸(楊心儀飾演)。不過,由于志根有一次大意差點讓孫女任幸走失,讓他與自己的女婿之間產生了巨大的矛盾,漸漸長大的孫女與自己越來越陌生。隨著自己年紀的增大,志根希望早日完成和自己逝去老伴的一個約定,把一起養的一只夜鶯帶回她的老家。他并不知道的是,女兒倩影繁忙的工作已經讓她的婚姻岌岌可危,也無法照顧她孫女。結果,倩影在無奈之下沒有經過丈夫同意的情況下,把任幸交給了自己,一同踏上了這段旅途。
事實上,影片看似樸素的題材在中國社會的背景下,非常具有現實主義色彩。隨著故事從現代化的都市北京轉移到平靜的內陸地區,絕妙地建構了一個迅速發展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與一片世外桃源般美景的兩種符號。結合影片在法國上映后超過12萬人次的觀影效果,足見這部“并不中國”的影片的“國際魅力”。像《夜鶯》這樣,一位外國導演代表其他國家角逐奧斯卡,在歷史上也非常罕見。著名的先例包括1975年的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德爾蘇·烏扎拉》,這是日本導演黑澤明所執導的一部由日本與蘇聯合作的電影,代表蘇聯參選。2013年的獲獎影片《愛》的導演邁克爾·哈內克擁有德國國籍,影片則代表奧地利角逐,不過,因為哈內克的父親是奧地利人,因此他的職業生涯其實一直都有德國、奧地利甚至法國的影子。
中國近10年在奧斯卡毫無斬獲
在上世紀90年代,接連4年奧斯卡提名名單中都有華語電影。1991、1992年,張藝謀分別憑借《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接連兩年入圍提名。1993年,陳凱歌的《霸王別姬》入圍,1994年,李安的《飲食男女》代表臺灣也獲得了那年的入圍提名,接連4年奧斯卡提名名單中都有華語電影。然而很快盛景不再,2000年后,只有張藝謀《英雄》曾入圍候選提名名單。至今也只有一部華語片獲得該獎項,2000年,李安代表臺灣參賽的《臥虎藏龍》完成了這一壯舉。
中國內地曾經選送的馮小剛作品《一九四二》盡管有奧斯卡級演員壓陣,但仍然難逃落選命運。近年來,中國內地的“申奧片”選擇已經陷入了“大導名作”的漩渦。張藝謀力邀克里斯蒂安·貝爾,幾乎為了爭奪最佳外語片量身打造《金陵十三釵》一樣鎩羽而歸,證明奧斯卡評委并不好征服。在外語片的評選中,主流商業電影比不上一部故事動人的所謂“藝術電影”。相比較而言,去年代表香港地區選送的《一代宗師》一度入圍9部短提名名單的初選,但最終仍無緣提名更令華語電影界寒心。王家衛作為少數在國際上與李安能夠相提并論的華人導演,藝術上與商業上都代表華語電影工業最高水準的作品仍然難以敲開奧斯卡的大門,讓評論界為未來的華語電影擔憂。
意法是大贏家 亞洲弱勢是常態
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項的設立起始于1947年,前幾年以奧斯卡榮譽獎的形式頒發給一些優異的外國電影,藉以提高世界各地觀眾對奧斯卡的注意。1956年起,最佳外語片成為正式獎項。評獎原則是:其參選影片必須是上一年 10月1日至下一年9月30日在某國商業性影院公映的影片。每個國家只選送一部影片,然后選出5部提名影片。今年,83個國家和地區報名參賽也創造了奧斯卡歷史上的新紀錄。
截至目前,意大利是獲得最佳外語片最多的國家,排名二、三的分別是法國和西班牙。第一部正式贏得最佳外語片獎的影片是費里尼執導《大路》(1956),而他也是問鼎這個獎項次數最多的意大利導演,曾經四次得獎。值得一提的是,瑞典獲得最佳外語片的三部影片《處女泉》、《穿過黑暗的玻璃》、《芬妮與亞歷山大》,均出自導演英格瑪·伯格曼之手。此外,日本影片早期表現不俗,有三部武士片獲獎,那時正值日本武士片輝煌時期,1955年后就很少見到日本影片的身影了,直到2009年獲獎的《入殮師》。華語片方面,曾于上世紀90年代在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項上創造出小高潮,至今只有一部影片獲該獎,是2000年李安代表臺灣參賽的《臥虎藏龍》,此后十幾年年再無收獲。
縱觀歷屆奧斯卡,幾乎很少出現有外語電影獲得最佳影片的提名,從而爭奪至高榮譽。1939年,讓·雷諾阿執導的反戰杰作《大幻影》斬獲奧斯卡最佳影片。但是,最佳外語片的概念在當時遠未被確立。近幾十年,只有《末代皇帝》、《藝術家》等外語片獲得過奧斯卡的最高獎項。2012年邁克爾·哈內克的《愛》也曾獲奧斯卡最佳影片提名,但最后不敵《逃離德黑蘭》。因此奧斯卡最佳外語片這個獎項也在于此——英語片之外的年度最佳,含金量頗高。業內認為,除了最佳影片提名外,最有份量的提名便是最佳外語片。歷數影史上非英語的優秀影片,不少正是通過最佳外語片的橋梁走進了大眾的視野——像《天堂電影院》、《美麗人生》、《竊聽風暴》等等。
本屆:熟面孔VS生面孔
其實同往年一樣,曾經柏林、戛納、威尼斯電影節入圍或獲獎的影片,代表各自國家出征奧斯卡的幾率也比較大,今年代表土耳其出征的《冬眠》、加拿大的《媽咪》等都是這一類影片,雖然這樣的幾率也不算太高而且奧斯卡似乎不喜歡太熟的面孔,但邁克爾·哈內克的《愛》是個例外,它就曾接連斬獲戛納金棕櫚和奧斯卡小金人。除了選擇“熟面孔”出征外,一些國家也往往另辟蹊徑。意大利本次就舍棄戛納評審團大獎《奇跡》,選了2013意大利年度佳片《人力資源》;烏克蘭則舍棄“國際影評人周”最佳影片《過于寂靜的喧囂》,由《帶路者》出征。不過,熟面孔中澤維爾·多蘭的《媽咪》實在是才氣逼人,有人說如果想看他的才華,他的處女作《聽嗎媽的話》前13分鐘就足夠了,這的確不假,他的長鏡頭和特寫鏡頭運用實在太漂亮,影片的色彩也足足夠味。
奧斯卡選擇外語片的路子不同于歐洲三大電影節,既不偏愛大片,也不喜歡太過于實驗性太先鋒的電影,會比較喜歡傳統敘事,但不能太平庸,要有一點新意和亮點,近幾年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伊朗電影《一次別離》,這部電影應該是最典型的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相,融人性視角、人生感悟和文化包裝于一體,非常對奧斯卡的路子。如果是以這個標準來看,波蘭影片《修女伊達》算是一個有力競爭者,影片以絕佳黑白影像美學,直探猶太歷史傷痕。電影講述年輕的修女在發現自己是名猶太人且她的父母死于大屠殺之后,生活發生重要轉變的故事。除此之外,歐洲方面,瑞典的《不可抗力》、挪威《1001 Grams》、德國《姐妹情深》等影片的質量也都值得期待。下面,我們便從申報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83部影片中精選14部逐一解讀,看看今年有哪些外語佳片不容錯過!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