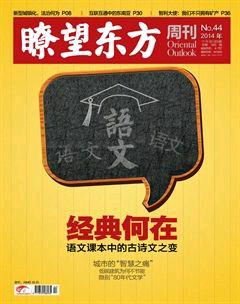王賡武:天下大勢,進退之間
鄭秋軼


兩天之內,王賡武在北京作了兩場演講,接受了3次采訪。在接受完央視英文頻道專訪后,立即從英語切換到普通話,完全聽不出一點“南洋口音”。
他已84歲,工作人員一再限制訪談時間,可是他的狀態很好,始終面色紅潤,笑容可掬,侃侃而談。
王賡武此行是來參加北京大學主辦的“北京論壇”,同時也受邀成為北大“大學堂頂尖學者講學計劃”的一員。他的第一場演講題為《無國界的文明:歷史的教訓》,詳細比較了西方文明、伊斯蘭文明及儒家文明的異同,并闡釋了經史子集等中國經典的形成過程。
第二場演講《南方境外:強進與退讓》,主題也跟“邊界”有關。在他看來,所謂“邊界”不是從來就有的,而是有進有退。他以所熟悉的東南亞為例。
“東南亞這個地區非常有意思,非常復雜。東南亞這個名稱本來是沒有的,二戰時期英國人給了這個名字,才成為一個新的區域。”
在演講中,王賡武多次提到“有意思”這個詞。不管是社會現象還是學術問題,“有意思”似乎是他的出發點和興趣所在。
近年,他對歷史文化、國際關系及城市化等問題都曾發表看法。歷史學家唐德剛認為,這位中央大學的學弟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可能成為另一個顧維鈞,可惜沒去做“更有意思”的事情。
但王賡武不覺得遺憾,“我很幸運,有機會一直呆在大學里,我的興趣在這里。”
進退之勢
1930年,王賡武出生在印尼爪哇島,長在馬來西亞(當時是英屬馬來半島),里面有不同的馬來王國。他長大的地方叫霹靂洲,其實叫霹靂王國,王國的宗教是伊斯蘭教,華人占三分之一。
“我從小就意識到,父母是道道地地的華僑,他們終究會回國的。父親畢業于東南大學,就是后來的中央大學,然后到東南亞教書。他們覺得海外華人不懂得華文,有責任去教他們,傳播中國文化、中國語言。”
因為日本入侵及后來的內戰,王賡武一家滯留馬來亞。他就讀于英國人開辦的英語學校,但在家中卻深受父親的國學熏陶,從《三字經》讀到《古文觀止》、《史記》。
中學畢業后,王賡武到南京中央大學念書。讀到二年級,內戰打到了長江,父母又把他接了回去。
“當時只有18歲,政治問題真的不懂,只知道內戰打得很兇,看到的國內情況也是進進退退。”這是王賡武第一次體會到“進退”的含義。
回到馬來亞,他一直在想這個問題。后來進入新加坡馬來亞大學(國立新加坡大學前身)學歷史,畢業后去了英國。他在倫敦大學讀博期間的研究方向是唐宋歷史。
“在20世紀50年代早期,從事這類題目(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是不可能的,因為那時的冷戰氣氛,使我們讀不到任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的書籍或文獻。”王賡武至今還遺憾“沒有把中國近代史學好”。
1957年,王賡武發現海外華人以及剛脫離殖民統治的人們對祖國的忠誠度出現了嚴重問題。“由于我本身也是海外華人,我知道這對于我的家庭和朋友以及所有在這一地區的炎黃子孫意味著什么。”
他意識到,南洋華僑華人的命運與中國在當代世界的地位息息相關。最終,他的研究轉向了海外華人史和中國近代史。通過迂回的方式,王賡武找回了自己的興趣——19世紀以來的中國歷史。這也使他成為“海外華人研究”的奠基者之一。
從小四海漂泊,能夠體驗到不同的政體、不同的歷史和文化。“我生的地方當時是東印度,長大的地方是英屬的馬來半島。1941年底,日本打到東南亞的時候,我們在日本治下生活了3年8個月。日本打敗了,英國又來了,各種黨派之爭,爭論得很厲害。”
這也讓王賡武再一次感受到那種“退退讓讓”的關系,而這與整個東南亞歷史,與中國和東南亞關系的歷史,值得認真考慮。
“我年輕的時候,荷蘭在東南亞,已經漸漸把所有印尼的島嶼都統一起來,成為它的荷屬東印度,這是相當費功夫的。現在的印尼有17000個島,荷蘭一個小小的國家,居然能夠把它統一起來。”
比荷蘭晚幾十年,英國人也來了。這兩個國家把整個馬來群島分成兩部分,小部分由英國控制,大部分由荷蘭控制。作為東南亞華人,王賡武深深地感受到,天下大勢,只在“進退”二字。
華人角色變遷
在王賡武看來,“華人”這一術語有些含糊不清。“最初的名稱是華商、華工,后來叫華僑,意思就是你們都是中國人,暫時在國外。之前沒有這種概念。”
今天,“移民”在某種意義上取代了華僑和華人的概念。其實從17世紀以來,華人在東南亞的角色就一直很復雜。
“對西方帝國主義政府來說,華商非常有用,他們可以利用華商跟中國經商,鼓勵他們,也幫他們,當然不給他們任何的政權。”王賡武說。
在土著人眼里,中國人地位比他們高,因為當地居民不懂做生意。如此就建立了一種矛盾的關系,華商一面要與本地居民來往、經商,一面要跟荷蘭、英國、西班牙的官員交涉,維持他們的地位。
“為什么華商到現在為止,在東南亞的地位有一種特殊的背景,就是因為他們當時的角色,中間人很難做,上面不信任,下面又恨他們,矛盾非常深,幾百年的故事了。”王賡武分析說。
二戰后,西方殖民地帝國退出,所有東南亞國家都建立了新型國家。“建國的過程中,民族、國籍、權利,矛盾越來越嚴重,因此華商、華工、華人在這些新型國家的地位就成為嚴重的政治問題。”
王賡武認為,國籍的概念也是新的,是中華民國之后才有的。但在二戰之后,這個問題就嚴重了——對東南亞新型國家來說,華人到底是什么國籍?
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講,華人回國非常歡迎,也可以入其他國籍。
“我們年輕一代沒什么選擇,入當地國籍,很多人都認為很自然,但老一輩非常傷心,認為中國把他們放棄了。”
所以,在王賡武看來,20世紀五六十年代,對東南亞華人來說是一個很困惑的時代。endprint
今天的國際形勢當然不同當年,“中國崛起了,又是一個新的變化。東南亞各國,要考慮如何跟中國建立新的關系。”
在海外華人心中,中華文明讓他們自豪。但是,“究竟這種文明的哪些內涵使他們如此驕傲,就不一定十分明了了。”
王賡武認為,國家的財富和力量無疑給了他們極大的自信。然而,在中國之外,“這種文明似乎讓人覺得棱角太硬——人們覺得這是一種展示財富和力量的文明。”
正是這種態度,導致整個20世紀中國都不得不重新定位。“過去被認為重要的東西,在很大程度上被現代性的價值觀所取代,特別是被那些以贏得財富和力量為目標的觀念所取代。”
開放模式與鄉土文化應該平衡
《瞭望東方周刊》:中國應該如何處理和東南亞各國的關系?
王賡武:東南亞國家對中國的看法跟以前完全不同。現在有一種新的契約感,東盟成立的理由就是如何建立一個鼓勵的契約,如何應對中國、美國和印度。它們基本的共識就是,每個小國在這個復雜的全球化經濟里無法生存,在某方面有共同的聲音才能生存。
這種情況下,中國怎樣跟他們建立新的關系,是很重要的問題。
東南亞國家基本的希望,就是能夠有一個獨立、統一的東盟。大家都認為將來的世界、亞洲新型國家的發展,東盟角色重要。它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間,在中國、日本之南,澳大利亞、美國之西,再加上將來印度的發展,東盟站在中間,好處很多。
《瞭望東方周刊》:佛教、伊斯蘭教在東南亞有很大影響,儒家文化在當地為什么影響有限?
王賡武:我也不太了解為什么幾千年來,印度教、伊斯蘭教在東南亞影響那么大,而中國那么悠久的歷史,非常健全偉大的文明,卻沒能影響到東南亞。這是個很有意思的問題。
這可能跟中國本身的儒家思想有關。儒家思想不贊成打出去,沒有傳教的意識。大概因為儒家是與農業經濟、鄉村生活結合在一起的,家的概念太重了,限制了活動范圍。
儒家思想是中國各個朝代意識形態的中心。儒家思想和政權關系密切,因此沒有一個獨立性思想的自由,并不能真正用思想去說服人家。
越南跟儒家有密切關系,朝鮮和韓國也有特殊的關系,他們是自愿的,非常仰慕中國的文化,派了許多精英人才來中國學習。日本根本就沒有完全接受儒家思想,最初非常仰慕唐朝長安帝國的概念,也學習中國,但唐朝時儒家地位還沒有那么高,還有佛教、道教。最早日本建立國家的過程,基本上不是以儒家為主的,還是以佛教為主。
《瞭望東方周刊》:關于中國的城市化,你曾指出“西安綜合征”、“上海綜合征”的問題,這種城市“綜合征”現象說明什么?
王賡武:中國的鄉土觀念非常深,我認為到現在為止還是如此。中國跟外國接觸是廣州帶頭的,廣州跟外國關系最少2000年了,但并沒有受外國文化多少影響。可是上海不同,上海開埠在1840年,60年之后,整個城市以及上海人的概念,已經很西化了。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開放以上海為基本模式,也受日本、韓國、新加坡和港臺地區的影響。
前幾個月我到重慶去,重慶要在嘉陵江北部建立一個很大的發展計劃,一開口就說,這是學浦東,就是上海模式。
我到西安,感到當地的鄉土文化非常強,很保守,原有中國的許多概念,還在那里體現。
這使我重新考慮:中國開放的模式都是同一個模式,但原有的鄉土文化并沒有被完全廢掉,仍舊非常堅強地保留著。所以這兩個勢力應該平衡,不能夠忽略一個或者另一個。
我前兩年到河南鄭州、洛陽、開封、登封,也有這種感覺——地方性的鄉土文化很強,并不接受上海模式。這不是對立的問題,而是平衡的問題。
兩方面中國都需要。一方面代表進步的思路,向外面學習,尤其科學、技術、經濟方面。另一方面,自己的文化可能在鄉土里才能保存。如果能做到平衡的話,就能夠推動整個社會進步。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