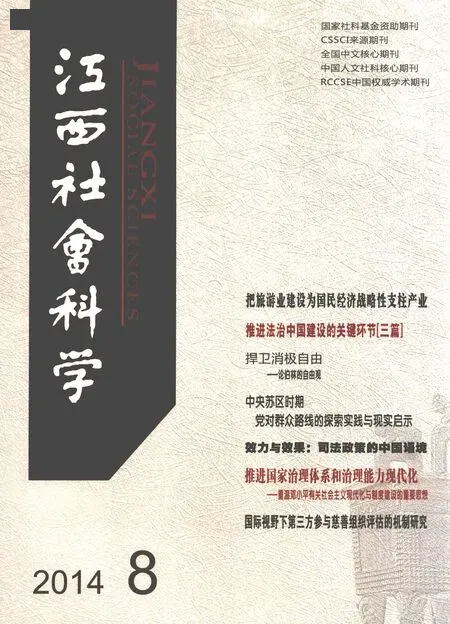基于嵌套Logit 模型下的工資集體談判分析
■張才明
一、文獻綜述
集體談判工資論認為,與其說工資決定于其他什么因素,還不如說工資決定于勞動力市場上勞資雙方力量的對比。在工業化發展的初期,工資談判是在廠商和勞動者個人之間個別進行的。由于工人無法遏制自己相互之間的競爭,因而無法抵抗工資下降的趨勢。工人只能組織起來,通過工會代表自己的更高利益與雇主和雇主集團做斗爭。與此同時,雇主方面通過資本積聚和集中,不斷形成大型廠商和廠商集團,從而遏制了雇主之間的競爭,勞資雙方的談判采取了規模日益擴大的集團化方式。集體談判的主要特點,是由于工會有效地遏制了工人之間的競爭,使自己成為勞動供給的壟斷者,并力圖使勞動市場成為賣方壟斷市場。
曾以勞動經濟學者身份登上倫敦經濟學院講臺的當代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翰·希克斯提出過一個集體談判過程的模式,比較準確地描述了勞資雙方的行為軌跡。Katz 研究了集體談判的分權化趨勢,Hubler 和Jirjahn 研究了德國的集體談判和工作委員會對工資和生產率的影響,Kahn 研究了集體談判和行業內工資結構的關系,Budd 和Na 研究了集體談判協議對于工會會員工資增加的影響。
目前,國內學術界對集體談判制度的討論,基本上集中在如何完善集體談判制度的法律基礎,以及如何促成政府推動和增強工會力量等方面。張抗私認為,只有改革現行的工會制度以及加大組建工會的力度,才能建立起符合時代經濟特點的勞動關系協調理論。但實際情況是,目前我國工會組織的職能正在轉變過程中,集體談判機制要達到理論上的目標仍有一定的距離。而吳紅列認為,我國工會的特點使得工會委員更傾向于在結構內部協調雇員與管理方的利益分歧,而不是代表工會成員與管理方談判。程延園認為,我國集體協商機制建立的現狀是:集體協商機制還沒有形成一個社會共識,談判環節缺位,集體協商機制尚未充分發揮作用;集體談判制度發展不平衡,一些企業和地區嚴重滯后。董保華曾在對我國勞動爭議協商機制的調查報告中,分析了我國集體合同簽訂率、履約率和集體合同爭議率以及集體勞動爭議率之間的數據比對,得出通過工會簽訂的集體合同大都流于形式的結論。這間接佐證了集體談判機制的運行效果,即通過工會與資方進行的集體談判制度亦大都沒有真正發揮實效而流于形式。任小平對我國工資集體談判的制度進行了反思和探討,并基于事實數據基礎提出了集體政策與方法的改進建議。
從我國開始推行集體協商制度以來,集體協商制度就引起國外學者的關注,如著名管理學家Malcolm Warner 和產業社會學家Simon Clarke。他們基本從工會角色的角度出發,論述具有“中國特色”的集體協商制度。Clarke 等人的研究表明,推行集體協商制度是黨和政府為穩定社會秩序而建立和諧勞動關系的需要。他在2005年再次闡述,中國工會推行的包括集體協商制度在內的多項工作,都是在黨的領導下,并為完成黨和政府建立和諧社會總目標的。因此,在集體談判的過程中少有工人參與,也較少存在真正的談判過程。工會的非獨立性,特別是在企業一級,工會依附于管理者的地位,使集體協商沒有實質性的意義。因此,Clarke 進一步提出,中國將西方通用的集體談判替換為具有中國特色的“集體協商”(collective consultation),并非是意識形態上的模糊,而是精準地反映了集體談判在中國的實際含義,即企業工會作為行政的附庸無法開展真正意義的談判。Warner等通過對60 多家國有和合資企業的調查發現,盡管全國總工會大力推行集體協商,并簽訂了相當數量的集體合同,但大多數合同的質量都不高。集體協商制度并非讓工會代表工人去爭取更好的工作條件,其作用僅限于勞動法等法律執行的監督者。Warner 認為,中國工會在改革過程中不斷變革,包括推進集體協商制度等工作,其目的是尋找工會在“和諧社會中的新角色”。因此,工會在集體談判中扮演的角色往往是矛盾的。
二、研究方法與數據處理
(一)研究方法
按照制度約束的差異,將工人工資增長路徑區分為集體工資談判和非集體談判,集體工資談判主導者為工會,而非集體工資談判分個人或廠商主導談判的形式。其中,個人主導一般出現在個人擁有某種特殊技能為廠商所需要的情況,這樣廠商不得不接受工人的個人要求;廠商主導談判通常是廠商固定的工資增長規定或政策。因此,工人工資增長路徑分層次結構如圖1 所示。

圖1 工人工資增長路徑結構
本文使用Mcfadden 提出的嵌套Logit 模型(Nested Logit Model),來分析工人工資增長的路徑問題。嵌套Logit 模型適合分層的決策結構,并且并不需要滿足IIA的假設,即任意兩個層級的概率比與其他層級的存在與否無關。廠商決定是否接受工會主導的集體工資談判,是否采用某種工資增長路徑或方式,取決于工資帶來的效用大小和成本高低。一般假設高工資會使員工更加努力,從而使生產效率提高,但會使成本增加。
按照上文所述,本文將影響廠商選擇工人工資增長路徑因素分為三類。一是信息不對稱因素,主要指廠商發展狀況,具體包括廠商利潤增長率、廠商人均利潤增長率、廠商資產回報率、工資總額與成本占比、工資總額與利潤占比等;二是監督效應,主要指工會力量,具體包括是否有工會組織、工會投入與運營成本占比、是否有獨立董事、工會代表是否是決策成員等;三是廠商聲譽,主要指廠商的市場美譽程度和員工認可程度,包括市場份額變化率、品牌價值增長率、員工滿意率等。
(二)數據收集與整理
本文借助于全國總工會系統平臺,分別面向廠商、工人、工會組織發放調查問卷。發放2000 份調查問卷,收上來1808 份,經過初步處理分析,有效問卷為1758份,其樣本數據描述如下表1 所示。

表1 2008—2012年數據描述
從表1 可以發現,采用集體工資談判的均值和中值要顯著高于采用非集體工資談判的樣本,這說明廠商和員工與工會對采用集體工資談判決定工資增長及額度的認知存在分歧。從反饋的結果可以看出,采用集體工資談判總樣本數不多,但廠商的資產規模和質量、品牌等都顯著高于采用非集體工資談判廠商。
三、實證分析
本文使用嵌套Logit 模型分析影響廠商接受工資集體談判的因素,在技術上,可分別引進信息不對稱、監督效應和廠商聲譽因素變量,以此來研究這些因素與員工工資增長路徑之間的關系,最后全部加入這些變量,以觀察核心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是否影響本文結論。本文使用次序極大似然法估計的概率模型分別表示如下:


模型1 只引進信息不對稱因素,模型2 為只引進監督效應因素,模型3 為只引進廠商聲譽因素,模型4 為全部加入上述三類變量。在上述模型中,Pr 表示廠商工資集體談判和非集體談判的選擇,A 表示概率分布函數,如果接受工資集體談判,則CWN 的值為1。估計結果如表2 所示。

表2 檢驗結果
從實證結果看,反映信息不對稱的變量與選擇集體工資談判部分呈明顯的相關關系。如表2 中模型1 和模型4 所示,廠商利潤增長率與集體工資談判正相關,且兩個變量的系數在5%水平下顯著,而工資總額與成本占比則與集體工資談判負相關,兩個變量的系數為在1%水平下顯著。也就是說,工資總額與成本占比是決定廠商是否接受集體工資談判的最重要因素,工資總額與成本占比越高,選擇集體工資談判路徑的工人工資增長的可能性越小。廠商資產回報率與集體工資談判基本無關。
反映廠商外部監督的變量與選擇集體工資談判也部分呈現明顯的相關關系。如表2 中模型2 和模型4 所示,工會代表是否是決策成員、是否有工會組織兩個變量與集體工資談判高度正相關,且前者變量的系數為在1%水平下顯著,后者變量的系數為在10%水平下顯著。也就是說,工會代表是否是決策成員,是決定集體工資談判能否執行的最重要因素,甚至是選擇集體工資談判的工人工資增長路徑的決定性因素。工會投入與集體工資談判基本無關。
反映廠商聲譽的變量與選擇集體工資談判也部分呈現明顯的相關關系。在表2 中模型3 和模型4 中,員工滿意率與集體工資談判呈現明顯的正相關關系,而品牌價值增長率與集體工資談判在模型4 中在10%水平下顯著正相關。也就是說,只有員工滿意率越高,決定選擇集體工資談判的工人工資增長路徑的可能性越大。市場份額變化率與集體工資談判基本無關。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以2008—2012 年共5 年的調查問卷數據為研究樣本,采用嵌套Logit 模型的方法研究了廠商接受集體工資談判作為工人工資增長的路徑選擇問題。實證研究發現,工資總額與成本占比、工會代表是否是決策成員、員工滿意率等三個指標為核心指標,與集體工資談判具有正相關的顯著影響;廠商利潤增長率、是否有工會組織和廠商的市場占有率則具有相關的一般性顯著影響;在集體工資談判確定的情況下,與廠商資產回報率、工會投入與市場份額變化率等指標基本上無關。
信息不對稱是影響工人工資增長路徑選擇的重要因素,企業的利潤增長率及員工工資總成本占比,基本上決定了廠商是否接受集體工資談判的模式,這個背后的根本原因是,集體工資談判實質上是一個群體對另一個群體的博弈,廠商往往很難主導,大部分是工會作為一個組織出面主導,除非工會主動退讓,廠商才能順利實現既定集體談判目標。因此,從政策層面看,要保障集體工資談判順利進行,必須切實降低企業的總體成本,切實提高企業的利潤率,有必要明確授權工會組織獲知廠商的利潤增長率及員工工資總成本占比情況,以便確定集體工資談判的依據。這樣既能避免工會獲知廠商的機密信息招致廠商的抵觸,又可以順利推進我國集體工資談判的進展。
外部監督是工資集體談判能否順利進行的重要保障,工會代表是否具有廠商一般決策權利,直接決定工會組織在廠商中的話語權。廠商通常建有工會組織,但往往不具有決策授權,本文中的外部獨立董事也具有一定的影響,但工會領導者在廠商組織中的地位至關重要。因此,有必要規定工會領導成為廠商組織中的績效和薪酬委員會成員,這樣既能避免工會干部對廠商的經營活動的干涉,又能發揮工會在工資集體談判中的作用,從而構建和諧的勞資關系。
在目前的環境下,廠商聲譽因素更多是員工的滿意度在驅動工資集體談判進展。因此,在政策上,有必要適當調整廠商績效尤其是國有企業的領導績效指標,增加員工滿意度,積極引導廠商從聲譽內生性上增強在工資集體談判中的主動性。
[1]郭金興.我國勞動爭議的省際差異及其解釋[J].財貿研究,2008,(5).
[2]任小平.中國工會轉型期的訴求責難與制度救濟[J].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學報,2009,(2).
[3]程延園.集體談判制度在我國面臨的問題及其解決[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4,(2).
[5]張才明.信息技術經濟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6]趙曙明.國外集體談判研究現狀述評及展望[J].外國經濟與管理,2012,(1).
[7喬健.工會體制改革與發揮產業工會作用的思考[J].工運研究,2006,(3).
[8]Pun,Ngai.Global Production,Company Codes of Conduct,and Labor Conditions in China:a Case Study of Two Factories.The China Journal,2005,(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