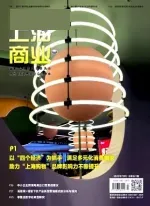山水千嶂幽谷清歌心入畫——武千嶂“沒骨水墨山水”賞析
文/常志康

知名畫家武千嶂的畫,猶如大自然中的山水云霧、清風飄逸、氣和韻暢。他通書法五體,涉油畫,擅長國畫,尤愛山水,得意和成就于潑墨山水。近賞千嶂先生的山水畫作品時,總為隱約的似有似無的東西受感動——“沒骨”?

天人合 墨有道
記得2013年9月的一天,在他的一幅新作前,忽聽得“沒骨水墨山水”的“新名詞”。在中國畫派中還從未出現這樣的沒骨水墨山水畫法,而“沒骨”一詞雖出現于北宋之時,但也僅見用于人物、花鳥,未聽說過用于山水畫。當今畫者若能探索成功,無疑為中國山水畫增添了新的藝術樣式,是對中國畫藝術發展作出的重大貢獻。
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我再一次來到千嶂先生的畫室,品茗中扯上了話題,從北宋山水出現高峰、以線為主的風貌談起劉、李、馬、夏、黃鶴大癡,又評了揚州八怪。當介入“沒骨”的話題時,他頓時神采飛揚、眉宇擴展。
先后入學于南京藝術學院美術系(國畫專業)和華東師范大學藝術系(油畫專業)的經歷,跨越中西畫的通識結構讓他有了較大的思考空間。對畫的狂熱,對畫的敏感,對畫的理解,對畫的探索經常讓他不安。于是,年輕的他開始了大自然之旅。
“一有時間就喜歡到有山有水的地方轉悠,幾乎游遍了中國的大山河川”,“看山山中有水,涉水水里見山,與不少仙人道士接觸、交往,一些說不清的東西總在腦海的土壤里萌芽”,“萌芽了什么,自己也說不清,但又的確像女子懷孕了一樣分明存在。”——這比喻讓我們開懷。“我能體會到女子懷孕是何感覺。”他認真地看著我說,我又大笑。
一個男人如此之深的探究,一定有其雪膚之羨、超人之處。“一直到40歲時的一天,我心中豁然暢朗。”千嶂先生面容神圣、目光凝注,思緒回到了從前。那一天,對他的一生至關重要。他有了一個方向,一個心中的“道”——看不見又分明存在的背后的東西,先前的痛、迷茫一掃而盡。至此,他放下了油畫筆,專注于中國畫,一發而不可收。也是那一天,讓他站在了一個中國畫難以逾越的高度——前人沒有走通的路——沒骨水墨山水畫。
有想法的畫家大多擁痛相依。多次,落筆后久久不能再下一筆,其痛其苦其尷尬如同放好了水的田卻找不到秧苗。夜半里,似有靈感迸發,他跳起來拿起畫筆記錄。一次,對一幅畫起筆后就再也找不到靈感,每日對著那幅畫面發呆,苦不堪言,終于某一日忍無可忍一盆水潑去掉頭就走,三天后,被水“淹”過的畫面竟讓他靈感泉涌,落筆如神。如今,這幅畫《萬壑云煙圖》成了他的至愛和紀念。“酣暢時,心中暢意隨筆而指點江山,那感覺太美了。”他說,“大自然與中國道教的天人合一給了我探尋墨道的鑰匙。”

中國畫的生命是線條,正是這個規則,導致藝術的寬度變窄了,畫家們在盡力研究著,前赴后繼,古往今來,這根線條已達之登峰造極,大師輩出。然而,在墨的表現上卻被忽略了,明顯落后于線條的表現力,之所以存在此弱項,關鍵在于墨的表現力太難。千嶂先生引難而上,認為“在墨里做文章”天地很寬,故傾心于“沒骨”水墨山水畫的表現研究。他將游歷大自然山中有情、水里有意萌芽出來的感悟,集中于“水墨”之間,研究墨在水的作用下所產生的自然效果、將傳統的皴法和自然肌理有意結合、苦苦尋覓著“畫法”之外的語境,探索著將“皴暈兼備”轉化為物我合一的沒骨水墨山水畫。
或許是他行萬里路閱遍山水的原因,他的山水畫自有著通透、虛實、陰陽平衡,往往將作畫時的情緒心境通過筆端與“氣”的融合,“氣場”在潑墨中翻飛,山石在舞動中的剛性,經常會在柔性云霧中得到表現,剛柔相濟,陰陽相合。傾瀉的水墨瞬間山水好像有了生命,呈現著泰山的霸氣,黃山的秀氣,峨眉的仙氣,誘導出了萬千氣象,源源不斷地剝離出了心中理想的丘壑。他作畫時的“無我”、“忘筆”,讓我體悟了他的“氣”,體會到了“沒骨”——精氣神之道。
《巌流噴空晴似雨,林蘿礙日夏云寒》表現了既涌動又播散著大氣場,如置身于萬千氣象、霧行峰現之感,精氣神兼具。
幽谷寂 清歌出

他在山水之中吸吮了大自然中的靈性,在對山水的探尋中反復地體悟“道”的本源與真諦。他在九十年代先后應邀在上海美術館、北京徐悲鴻紀念館、溫州展覽館舉辦個人書畫展、武千嶂藝術研討會,著名書畫家趙冷月贊揚“采眾家之長,充滿了靈氣”,著名書畫家韓天衡也表示“作品生命力強”,并鼓勵他“不斷地調適自己”,中央電視臺、上海電視臺為他拍攝了專題片,畫界、社會都肯定了他。
然而,此時的他反而沉寂了——“在轟轟烈烈辦展之后自我反思,覺得功底尚不足,眼界也尚窄,對一些社會的現象、審美標準的失序、對繪畫評判的亂象不愿融入,為此,我退而作研究,靜閱博覽。在思考中西美術史中漸進找到了深入的東西,自我的境界變得淡而深遠。”

沉寂的幾年中,他將“行萬里路讀萬卷書”古語,用自己的語言換成了“行經典路讀經典書”,重新審視中國山水畫中的真正內涵,認為畫家的思想應該高人一籌,追求一般人看不見的東西,研究人的心靈世界。從陶淵明研究無弦琴無字書中得到了感知,從陸儼少筆筆生發、筆筆相扣中得到了靈感,提出了獨特的情感誘發的創作方法,有效的將心中的“道”誘發出與水墨之 間。“ 沒骨”潑墨貴在追古誦今、心相隨性,但不逾矩,水溢而于情理之中,看似無構圖但畫境入其中,千變萬化語境不同、心緒不同,但出無盡的山水境界。
心中的“道”一旦升華為新的境界,積蓄于他心中的、腦海內的山水活泛了起來,與之對話,輕松對應,心手雙暢,意在筆先,空靈悠遠的萬千姿態盡入畫中,其“語言傾訴”化作了精神層面的東西,也就是他之前“看不見又分明存在的背后的東西”。
《曉暮春煙》看似狂云亂霧,然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下部則猶若一君閑庭信步、靜如處子,一動一靜,相得益彰,盡顯作者表現與寄語之境界。
《幽谷清歌》整個畫面表現形式罕見,只現山的中部橫截的局部,然濃云似雪涌、輕霧在遠散,如歌如訴,在奇中得平衡。我想,這也許正是千嶂先生慕求的淡而深遠的精神意境吧。相信《幽谷清歌》的作品,可以是他曾經沉寂幽谷而清歌出幽谷的紀念。

性情來去“沒骨”天成
千嶂先生是個很有個性的人,好像還不是一般的有個性。
在父輩眼里,他“大逆不道”,在女兒眼里他值得欣賞和尊敬,在學生眼里他博學善教,在朋友眼里他真實倔強,在同行眼里他是一個我行我素的人,在自己眼里他面對任何評論依然堅持自我。他的個性從改名可以看出。
他原名吳志堅,成年后改為武千嶂,中國傳統鮮有成年后改名的,尤其不會改姓。他卻在1992年于上海美術館舉辦畫展時連名帶姓一起改為武千嶂,武即動,千嶂即山,意喻武動山水。
他與“武”非一般緣分。他少年習武。1976年,朋友介紹他為一位形意八卦掌的傳人畫一套拳譜。他不談價錢當即答應,只見那人從地下挖出一鐵箱,取出一套殘缺不全的拳譜,又擺姿勢讓他畫。一個招式重復三次,他很快地完成了。他一天也不多畫,回家關門,照譜偷師習拳,頗獲心得。1992年辦個人畫展時,他同時展出了習拳的照片,請當年讓他畫拳譜的師父觀看,師父驚訝,“偷師能偷到如此神韻”,即納為徒。改姓名曾被父輩視為大逆不道。他說,“武與吳同音,以武命姓當屬必然”。



他精于國畫,又深諳油畫,數次穿越、跳躍于中西畫派之間。早先就讀于南京藝術學院美術系,師從齊白石弟子陳大羽學國畫。由于基礎扎實,再加上聰慧勤奮,在山水畫上有了明顯的成績。1992年,年僅34歲就應邀在上海美術館舉辦了山水作品個展,雖然好評如潮,可是他卻覺得后勁不足,需要給自己補課,為求揚長避短,把自己以前擅長的油畫,移作階梯,去攀登別人沒有的高度。這個時候,他在研究中國山水畫的同時,用油畫進行有意識的嘗試,從印象畫派一直到抽象藝術,試驗將中西文化、畫風作交融。
一位友人好奇:“你一個城市的畫家,為何癡迷于山水畫?”他笑談了一個故事:“初中時,經常一個人爬上石庫門的屋頂曬臺上看落日的云霞,特別是在逆光效果下的云朵,千奇百怪,有時連綿起伏、有時層巒疊嶂、有時高聳入云、有時蒼山如海,這種會動的云山,讓我如癡如醉。”對山的愛就是從那時開始的,心中的山水永遠蕩漾在心里。
近幾年,千嶂先生的山水畫,就像深巷中的陳年老酒,撲鼻而香。當他的國畫作品重新出現在畫界時,有多家專業雜志美術編輯驚嘆“你的作品大變”、“怪不得你不見了,見時換崢嶸!”2004年6月,他的作品《云嶺鐘秀》在“21世紀中國藝術名家名作大展”中獲得一等獎,作品《深林疊嶂聽泉聲》獲“2009年全國山水畫大展成就獎”。
個性的“折騰”折射了他的固執,在中西畫中數次“回轉”,終在游歷、痛苦、索求、閱讀、認知中落定于“沒骨山水”,“也是在悟得了萬物皆有道、五行相依生、放逸山水、中得心源之后”。
“中道”讓他從傳統出、又恰如其分地融入了油畫元素,探索出自北宋至今少有的、獨具個性、較為成熟的“沒骨潑墨山水畫法”。走進他的水墨世界,方能感受到他的水與墨融合后的境——神性、大氣、天成。幅幅水墨,在靜與動、濃與淡、意與韻、陽與陰、天與地、明與暗、光與影融合成了獨特的氣場、心象與詩章。
潑墨成山“沒骨”無意
中國水墨山水畫自唐代吳道子的“白畫”始,經王維的“破墨”、項容的“用墨”發展到王洽的“大潑墨”,使中國水墨山水畫發展為“筆墨積微”、“不貴五彩”、“水暈墨章”的技法。而“心”是中國畫的精神內核,“相”是畫的精神外現,心相是畫的神魂所在,唐代書畫鑒藏家裴孝源所說的“心存懿跡、默匠儀形”即指心相,南宋陳郁也述“寫其形,必傳其神,傳其神,必寫其心,寫形不難,寫心惟難也”。千嶂先生的山水畫僅以水墨為色,絕不用彩,他信老子的“五色使人目盲”,莊子的“形、神、心、身”的“天人感應”關系,在“不同之同,不似之似”間得到了繪事之妙,“用墨”的隨性和水墨潑灑之間盡顯“心相”。他以氣發筆,潑墨成山,濃淡枯潤,一墨融多色,勾皴烘染,無意有意,“沒骨”其中,盡現水墨精華與境界。

作品《暮色千山入,春風百樹香》云中山形時隱時現,聲聲瀑布幽谷而來,而云中有仙氣,氣霧中似乎有些許的愁緒,讓云中瀑布暢泄,仙氣仍自在其中,表達了水在金、木、水、火、土中的最高境界,在以水現氣、巖棲谷隱、師法造化、以氣現人的哲理意味中表達了作者當時的以柔克剛的精神語境。
于2014年作于太行山的《雨中清音》,云、霧氣與山共依共生,山具有的雄偉的大氣象在似與不似之間從畫中隱沒、走出來。其畫法中有借鑒,更多的是“沒骨”潑墨與線的結合恰到好處,不唯美之中見美,潛意識畫法中有“我”的寄托。其畫言、意、氣均足,尤其是由氣場引動的虛實、節奏、韻律表現了陰陽五行的藝術效果,傳遞了由空間到視覺的“天人感應”的關系,“蓋理足則精神,意足則蘊藉,氣足則生動”,陰陽五行的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骨架也隱于了畫中。

《降瑞圖》(2013年作品)可以說是以“大潑墨”的“籠天地于形內,挫萬物于筆端”之勢,表現了筆墨“容勢、明神”的靈動意境的境外之境,虛實相間、心象外觀極點的陰陽互動關系、氣勢宏大,給人以極大的想象空間,云遮蓋了山巒的本真面貌,點綴的略彎但扔挺拔的無根松以閱世之姿,好象在訴說著“山并不會因云霧蓋而不成其山”。這是一幅“沒骨”潑墨到極致的經典山水畫,也是用心在畫、表現豐富內涵、構筑心堤、以畫言志的成功作品。
憑作品達到的“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的境界,畫界同仁已將“沒骨水墨山水”視為他的符號——至高的榮譽。2013年,他被新華網評為“中國十佳最受藏界關注藝術家”。
是什么讓他得以“沒骨”?或許是——高等學校教學科研的磨練,或許是個性獨立、喜拳術、閱中醫,或許是他通書法、涉油畫、擅長國畫最愛山水,天分高、敏思考、又勤奮?依我對他的了解,以上綜合即是他了,只不過,他有時身在俗境,心卻在山徑霧道中“修煉”。他的太太、女兒也受他的影響,喜歡上了轉山、觀霧、看出水、養氣功,自家小花園里時現醫生太太侍候花草的倩影。
他不在意所任中國書畫家協會副會長、中國書法研究院藝委會會員、中國書畫家聯誼會會員、國家一級美術師等,但作為本職美術教研室主任,“他十分認真”,他以獨特視角創造的新型符號教學法——《中國畫可數符號教學法》、《色彩符號教學法》、《游戲符號教學法》系列教材被廣泛應用,《書法數字教學——楷書、行書、隸書》廣受歡迎。
曾經,成功的彼岸在未知的遠方,現在,遠方已在此岸。
藝無止境,唯愿再精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