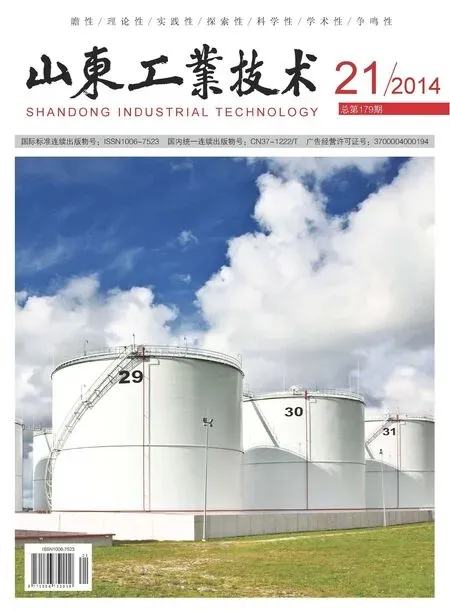山洪泥石流風(fēng)險研究評述
張 婧 ,王 東
(1.西華大學(xué) 能源與環(huán)境學(xué)院,成都 610039;2.四川省交通運輸廳公路規(guī)劃勘察設(shè)計研究院,成都 610041)
1 前言
鑒于災(zāi)害機理研究的不成熟導(dǎo)致工程措施在防治山地災(zāi)害上的局限性,越來越多的科學(xué)家和一些歐洲阿爾卑斯山區(qū)國家傾向于采用“風(fēng)險區(qū)劃”、“風(fēng)險評估”、“預(yù)報和預(yù)警”等非工程措施來降低災(zāi)害帶來的經(jīng)濟損失和人員傷亡[1]。從1987年聯(lián)合國開展的“國際減災(zāi)十年”活動開始,山洪泥石流風(fēng)險分析的研究逐漸興起。
2 山洪泥石流風(fēng)險概念
1992年聯(lián)合國人道主義事務(wù)部給出了自然災(zāi)害風(fēng)險的定義:風(fēng)險是在一定區(qū)域和給定時段內(nèi)、由于特定的自然災(zāi)害而引起的人們生命財產(chǎn)和經(jīng)濟活動的期望損失值,它的定量表達式為[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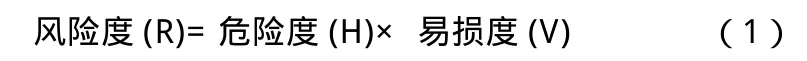
2004年聯(lián)合國開發(fā)計劃署給出的風(fēng)險定義為:自然或人為災(zāi)害與承載體的易損性之間相互作用而導(dǎo)致一種有害的結(jié)果或預(yù)料損失發(fā)生的可能性,其定量表達式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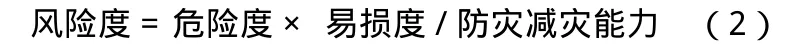
公式(2)認(rèn)為社會經(jīng)濟條件好的地區(qū),采取一定防災(zāi)減災(zāi)措施來提高區(qū)域承災(zāi)能力,能夠有效降低研究區(qū)域的相對損失率。近年來,這一表達式也得到一些研究學(xué)者的應(yīng)用[3-4]。
山洪泥石流風(fēng)險評價是一個典型的綜合分析過程,涉及地質(zhì)構(gòu)造、地形地貌、氣象、承災(zāi)體類型和價值等許多復(fù)雜因素。早期開展的山洪泥石流風(fēng)險評價一般采用數(shù)理統(tǒng)計及分析等方法開展定性或半定量的評價研究[5],主要是因為無法給出易損度的具體數(shù)值。20世紀(jì)90年代以后,隨著遙感、GIS技術(shù)的廣泛應(yīng)用,基于區(qū)域背景資料的風(fēng)險區(qū)劃研究不斷涌現(xiàn)[6],為制作大尺度的山洪泥石流風(fēng)險區(qū)劃圖提供了技術(shù)平臺。唐川[7]和鐵永波[8]等人采用多因子權(quán)重分析法和分類統(tǒng)計法在GIS平臺上生成危險度區(qū)劃圖和易損度區(qū)劃圖,通過疊加得到云南昆明市東川城區(qū)和汶川縣城后山南溝的山洪泥石流風(fēng)險區(qū)劃圖。基于GIS的風(fēng)險區(qū)劃方法操作步驟清晰,一旦掌握可靠詳實的遙感解譯圖片就具有很高的可行性,結(jié)果的呈現(xiàn)也非常直觀。然而圖形疊加采用公式(1)的計算方法,將易損度和危險度看做兩個獨立的變量,這與國外現(xiàn)行的觀點不同。Fuchs[5],Uzielli[9]和Mavrouli[10]等眾多學(xué)者認(rèn)為風(fēng)險度是關(guān)于災(zāi)害i出現(xiàn)的概率Psi,承災(zāi)體j總價值A(chǔ)Oj,與災(zāi)害強度相關(guān)的承災(zāi)體j的易損度VOj,Si和承災(zāi)體j在災(zāi)害i中的暴露度POj,Si的函數(shù),如公式(3)所示。承災(zāi)體的易損度應(yīng)與其遭受災(zāi)害的程度息息相關(guān),而絕非一個常數(sh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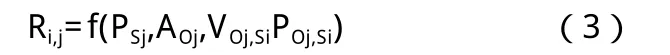
3 山洪泥石流風(fēng)險評估難點
山洪泥石流風(fēng)險評估的重要性雖然得到許多學(xué)者的肯定,但與滑坡、洪水、雪崩、地震等其他類型自然災(zāi)害相比,其研究進展一直相對落后。從公式(1)~(3)可以發(fā)現(xiàn),風(fēng)險的研究實質(zhì)上是危險度、易損度及其兩者之間相互關(guān)系的研究,因此風(fēng)險的評估水平很大程度上決定于這三者的研究層次。本文從五個方面切入,展開對山洪泥石流風(fēng)險評估難點的分析。
3.1 評估范圍的尺度不同,對評估的目的和精度要求不同
在對災(zāi)害進行評估時,首先應(yīng)確定評估的時間尺度和空間尺度。時間尺度可以理解為靜態(tài)或動態(tài)的風(fēng)險評估。前者是指某一特定時期對研究區(qū)域的風(fēng)險評估,主要是反映災(zāi)害可能對地區(qū)產(chǎn)生的影響程度;后者是某一段時期對研究區(qū)域的風(fēng)險評估,而評估時期長則幾十年或者上百年,短則一年或者幾年。動態(tài)風(fēng)險評估的必要性主要是由承災(zāi)體對象價值和人口密度的變化所帶來的。Fuchs等人[11]統(tǒng)計研究發(fā)現(xiàn)歐洲阿爾卑斯山區(qū)自然災(zāi)害的風(fēng)險變化正是由于承災(zāi)體數(shù)量和價值的變化而產(chǎn)生的。我國近年來農(nóng)村經(jīng)濟體加速膨脹,受山洪泥石流危害的山區(qū)農(nóng)村承災(zāi)體價值和人口會迅速提高,風(fēng)險將大大增加。然而,動態(tài)的風(fēng)險評估需要更豐富的資料和更復(fù)雜的分析過程,例如人口密度和經(jīng)濟增長變化規(guī)律、國家政策分析、市場規(guī)律解讀等等,涉及人口統(tǒng)計學(xué)、社會學(xué)、心理學(xué)、政治學(xué)和經(jīng)濟學(xué)等等。
空間尺度是指評估范圍的大小,我國的風(fēng)險評估尚沒有進行這方面的區(qū)分和研究。依據(jù)國外的區(qū)分標(biāo)準(zhǔn)結(jié)合我國的行政劃分等級,山洪泥石流風(fēng)險評估的空間尺度可分為三種:鄉(xiāng)、鎮(zhèn)、縣、市內(nèi)范圍(local scale);省內(nèi)范圍(regional scale);多省范圍內(nèi)或全國范圍(national scale)。不同空間尺度風(fēng)險評估的研究目的、所面向的風(fēng)險決策者或者使用者都有差別。一般來說,隨著空間尺度的加大,風(fēng)險評估對資料要求的詳實程度和評估成果的精度是遞減的。
3.2 評估需要可靠的數(shù)據(jù)來源和強大的技術(shù)平臺支持
山洪泥石流風(fēng)險評估工作需要進行海量數(shù)據(jù)的存儲和運算,因此需要強大的技術(shù)平臺,能夠生成圖像方便決策者比較不同地區(qū)并查詢目標(biāo)風(fēng)險值。另外,在進行風(fēng)險評估之前,數(shù)據(jù)的收集至關(guān)重要,但往往是最耗時耗力。因此,在遙感技術(shù)和GIS技術(shù)平臺出現(xiàn)之前,山洪泥石流的風(fēng)險評估停留在理論和個別案例的研究上,研究成果很少,一般以列表的形式展現(xiàn)不同地區(qū)的風(fēng)險大小,較少應(yīng)用于實踐當(dāng)中。
遙感是以航空攝影技術(shù)為基礎(chǔ),在20世紀(jì)60年代初發(fā)展起來的一門新興技術(shù)。自1972年美國發(fā)射了第一顆陸地衛(wèi)星后,這就標(biāo)志著航天遙感時代的開始。通過解譯遙感數(shù)據(jù),可以很容易獲取研究區(qū)域的地理地質(zhì)特征參數(shù),減輕了繁重的野外調(diào)查工作。遙感數(shù)據(jù)還能夠提供大量的承災(zāi)體類別和數(shù)量,避免了冗長、復(fù)雜的排查和搜集工作。地理信息系統(tǒng)(GIS),又可稱為“地學(xué)信息系統(tǒng)”或“資源與環(huán)境信息系統(tǒng)”,可以在計算機硬、軟件系統(tǒng)支持下,對整個或部分地球表層(包括大氣層)空間中的有關(guān)地理分布數(shù)據(jù)進行采集、儲存、管理、運算、分析、顯示和描述。結(jié)合遙感技術(shù)和GIS技術(shù)系統(tǒng)平臺可以顯著提高山洪風(fēng)險評估的效率,降低評估工作的難度,同時可以實現(xiàn)數(shù)據(jù)的實時更新,直觀地呈現(xiàn)風(fēng)險評估成果。Weichselartner在2001年,就強調(diào)過遙感和GIS技術(shù)對災(zāi)害防治工作的重要性。
3.3 泥石流易損度定量評估困難
泥石流易損度研究作為風(fēng)險評估的重要環(huán)節(jié)起步較晚,而且泥石流本身行為復(fù)雜,承災(zāi)體種類豐富,加之兩者相互作用機制不明,因此還沒有嚴(yán)格的物理和數(shù)學(xué)方程能夠解決此問題。目前山洪易損度定量評估的方法主要有曲線法、多指標(biāo)綜合判斷法和價值核算法[12]。曲線法與災(zāi)害強度一一對應(yīng),但是依賴歷史災(zāi)情的調(diào)查,由于承災(zāi)體類型特別豐富,數(shù)據(jù)較難收集,因此成果較少。多指標(biāo)綜合判斷法和價值核算法適用于大尺度區(qū)域的靜態(tài)評估,對詳細信息的披露少。總的來說,山洪泥石流易損度研究的定量化水平仍然不高。
3.4 泥石流機理研究尚不成熟
由于泥石流機理的研究仍不成熟,理論研究無法為風(fēng)險評估提供確切的特征值。目前在我國流行的多指標(biāo)綜合判斷法的危險度評估忽略復(fù)雜的山洪泥石流機理,考慮對觸發(fā)山洪泥石流有貢獻作用的,現(xiàn)實考察中可獲取的參數(shù),提高了評估的可操作性。指標(biāo)賦值和權(quán)重系數(shù)的標(biāo)準(zhǔn)化處理,保證危險度的取值范圍在0~1之內(nèi)。但是,這種方法同時存在著不足。首先,因子之間的權(quán)重系數(shù)采用灰色關(guān)聯(lián)度方法確定,依賴于所使用的歷史數(shù)據(jù)。歷史數(shù)據(jù)的序列長短,準(zhǔn)確性,多樣性對關(guān)聯(lián)度結(jié)果的影響是客觀存在的。如果泥石流流域物質(zhì)儲備充足,降雨達到一個比較低的臨界條件就會觸發(fā)泥石流;反之物質(zhì)儲備不充足,則流域地質(zhì)地貌特征參數(shù)對泥石流發(fā)生更具有決定性。其次,為消除計量單位對結(jié)果的影響,研究者對研究區(qū)域內(nèi)單元的指標(biāo)數(shù)值進行極差變換。變換后得到的指標(biāo)無量綱數(shù)值并不具有絕對意義,與所在研究區(qū)域內(nèi)該指標(biāo)的數(shù)值序列位置有關(guān),因此可能出現(xiàn)同一單元在不同研究序列內(nèi),有兩個不同的數(shù)值。這樣,區(qū)域單元的危險度一旦脫離所在的比較序列就不再具有參考價值。
3.5 風(fēng)險評估的黑箱模型
一般災(zāi)害的風(fēng)險值是發(fā)生的概率乘上后果,如工程風(fēng)險、地下水風(fēng)險和洪水風(fēng)險等。這些領(lǐng)域的災(zāi)害動力學(xué)機制成熟,基本可以實現(xiàn)災(zāi)害過程的數(shù)值模擬及其參數(shù)的獲求,研究的關(guān)注點在于風(fēng)險發(fā)生的概率,隨機理論被大量引用。現(xiàn)有的泥石流風(fēng)險評估模型(如公式(1)和(2))還沒有將危險度和易損度聯(lián)系起來,而是單獨進行評估相乘得到無量綱的風(fēng)險數(shù)值,屬于黑箱模型。模型不需要考慮泥石流復(fù)雜的動力過程,避免未知的承災(zāi)體易損曲線,操作效率高而且便捷,評估成果直觀易于理解。
但是,黑箱模型沒有考慮泥石流災(zāi)害特征及其與承災(zāi)體的聯(lián)系,一旦脫離評比序列就無法根據(jù)數(shù)值大小做出決策。對于受泥石流威脅的具體地區(qū),如果泥石流危險范圍以外的建筑財產(chǎn)也被當(dāng)做承災(zāi)體,那么就會高估風(fēng)險。泥石流溝可能沖出不同規(guī)模的泥石流,并不是所有的泥石流都會完全毀壞所有的承災(zāi)體。不同的承災(zāi)體易損程度不同,分布在不同位置的承災(zāi)體遭受泥石流的損壞程度也不相同。為了更好的做到減災(zāi)管理,降低因高估風(fēng)險而造成不必要的經(jīng)濟浪費,減災(zāi)工作者需要掌握風(fēng)險分布情況。因此,在對小尺度的已知泥石流高風(fēng)險地區(qū)(村、鄉(xiāng)、鎮(zhèn))進行風(fēng)險評估時,需要建立基于泥石流動力過程的風(fēng)險評估模型,考慮泥石流與承災(zāi)體的耦合作用過程。
4 結(jié)語
綜上所述,由于存在多方面因素的影響,泥石流風(fēng)險評估的研究仍有較大的發(fā)展空間,危險度和易損度的理論研究仍亟待突破。現(xiàn)階段泥石流風(fēng)險評估模型可以對區(qū)域整體損失風(fēng)險作出評估,但不能提供具體的分布信息,對于一個已知高風(fēng)險的區(qū)域而言,難以給出定量化的評價。因此,建議構(gòu)建基于泥石流動力過程風(fēng)險評估模型,緊密聯(lián)系危險度和易損度,得到更適用與小尺度區(qū)域評估的風(fēng)險數(shù)值。
[1]PLANAT. Strategie Naturgefahren Schweiz. Synthesebericht in Erfüllung des Auftrages des Bundesrates vom 20. August 2003 [R]. Bundesamt fürWasser und Geologie, Biel, 2004.
[2]劉希林. 區(qū)域泥石流風(fēng)險評價研究[J].自然災(zāi)害學(xué)報,2000,9(01):54-61.
[3]鐵永波.強震區(qū)城鎮(zhèn)泥石流風(fēng)險評價方法與體系研究[D].博士論文,成都:成都理工大學(xué),2009.
[4]張一凡.西南地區(qū)城鎮(zhèn)地質(zhì)災(zāi)害易損性評價方法研究[D].碩士論文,成都:成都理工大學(xué),2009.
[5]Fuchs S., Heiss K. and Hübl J. Towards an empirical vulnerability function for use in debris flow risk assessment [J]. Nat Hazards Earth Syst Sci.2007, 7: 495-506.
[6]Carrara A., Cardinali M. and Detti R. et al. GIS techniques and statistical models in evaluating landslide hazard [J]. Earth Surface Processes and Landforms, 1991,16: 427-445.
[7]唐川,朱靜.城市泥石流風(fēng)險評價探討[J].水科學(xué)進展,2006,17(03):383-388.
[8]鐵永波.汶川縣城泥石流災(zāi)害風(fēng)險評價研究[J].災(zāi)害學(xué),2010,25(04):43-48.
[9]Uzielli M., Nadim and Lacasse S. et al.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quantitative estimation of physical vulnerability to landslides [J]. Engineering Geology,2008(102): 251-256.
[10]Mavrouli O. and Jordi.C. Vulnerability of simple reinforced concrete buildings to damage by rockfalls [J].Landslids. 2010, 7: 169-180.
[11]Fuchs S., Keiler M., and Zischg A. et al.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avalanche risk in settlements considering the temporal variability of damage potential[J]. Nat Hazards Earth Syst Sci., 2005,(05): 893-901.
[12]張婧.山洪泥石流災(zāi)害動力過程試驗研究及風(fēng)險分析[D].成都:四川大學(xué)博士論文,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