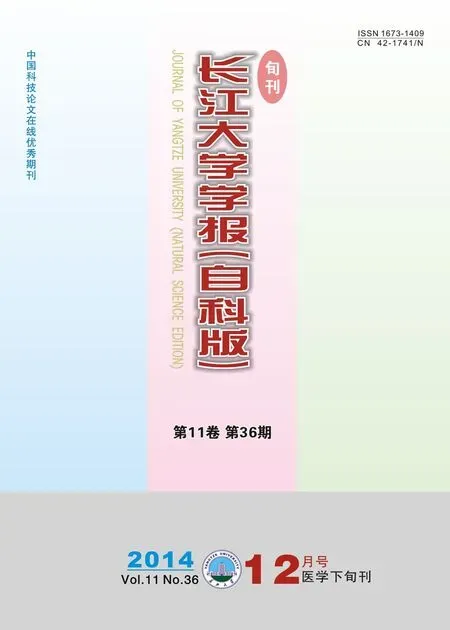單純西藥與中西醫結合治療妊娠期肝內膽汁淤積癥療效比較
楊蕾(公安縣中醫醫院婦產科,湖北 公安 434300)
妊娠期肝內膽汁淤積癥(Intrahe Patic Cholestasis of Pregnancy,ICP)是一種與妊娠相關的疾病,多發生于妊娠中、晚期,以皮膚瘙癢和黃疸為特征,伴有膽汁酸、肝酶等生化指標異常,主要危及圍產兒。可引起胎膜早破、胎兒窘迫、自發性早產、孕期羊水胎糞污染甚至發生不能預測的胎兒突然死亡,新生兒顱內出血,新生兒神經系統后遺癥等[1-2]。本病臨床上亦無一致公認的特效藥物。近20年來,很多學者致力于ICP的發病機制研究[3-4]。目前其確切的發病機制尚未十分明確,但是根據大量的流行病學調查、臨床觀察及實驗室工作研究,提示雌激素水平過高可能是誘發ICP的原因[5]。因其對圍產兒的危害很大,現已廣泛地引起婦產科臨床重視。公安縣地處長江中下游,是此病的高發地區。我們于2010年1月至2014年5月,開展了單純西藥治療和中西醫結合治療,并比較兩組治療方法的療效,現將結果報道如下。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從2010年1月至2014年5月,逐月選取在公安縣中醫院住院部婦產科住院且符合條件的ICP患者125例作為研究對象。入院病人孕28周后,采用前瞻性對照研究,在進入研究前未行任何治療,入選后不用其他影響肝功能和瘙癢癥狀藥物。按照隨機分組的原則,分為中西醫結合治療組(62例)和單純西藥組(63例)。
1.2 方法
1.2.1 治療方法 ①單純西藥組63例患者采用氧氣吸入2次/d,地塞米松每天12mg口服,連用7d,后3d逐漸減量而停藥。注射用丁二磺酸腺苷蛋氨酸,每天500~1000mg,靜脈滴注,共兩周。②中西醫結合組62例患者除采用以上治療外,加用本院協定ICP中藥方“清肝利膽退黃飲”,1劑/d,兩周為1個療程。
1.2.2 觀察指標 ①臨床瘙癢癥狀:采用Ribalta制訂的標準進行瘙癢評分。無瘙癢為0分;偶發瘙癢為1分;間斷性瘙癢無癥狀波動為2分;間斷性瘙癢有癥狀波動為3分;持續性瘙癢4分。②膽汁酸及轉氨酶指標,采用島津全自動生化分析儀測定。③住院分娩后觀察兩組的分娩孕周、剖宮產、羊水污染、圍產兒死亡情況。
1.3 統計學分析
使用SPSS 10.0統計軟件對所得數據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基本情況
中西醫結合組62例,單純西藥組63例。中西醫結合組患者年齡21~26歲,平均年齡(24.11±0.45)歲。單純西藥組患者年齡20~25歲,平均年齡(24.06±0.41)歲。兩組患者既往均無手術史和心血管、肝膽疾患。兩組患者在年齡、戶籍、文化程度、孕次方面無統計學差異(P>0.05),具有可比性,見表1。

表1 兩組患者基本情況比較
2.2 兩組患者總有效率比較
兩組患者經過2個療程的住院治療后,中西醫結合組顯效49例,好轉10例,總有效59例,總有效率95.16%;單純西藥組顯效9例,好轉18例,總有效27例,總有效率42.85%。統計分析表明,中西醫結合組無論是顯效、好轉、總有效率均顯著優于單純西藥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
2.3 兩組患者觀察指標比較
從兩組患者皮膚瘙癢評分(P<0.05)、谷丙轉氨酶(P<0.05)、谷草轉氨酶(P<0.01)、血總膽汁酸(P<0.01)4項觀察指標來看,結果中西醫結合組均明顯優于單純西藥組,皮膚瘙癢減輕快,其他3項生化指標下降快,兩組之間4項觀察指標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見表2。

表2 兩組患者觀察指標比較
2.4 兩組患者妊娠預后變化
從兩組患者妊娠預后變化情況來看,結果中西醫結合組基本都在孕38周后分娩,剖宮產率僅為29.03%,羊水污染率也僅為12.90%,圍產兒無死亡病例。而單純西藥組的分娩孕周平均為36周,剖宮產率達61.90%,羊水污染率也達50.79%,且發生1例圍產兒死亡。中西醫結合組與單純西藥組各項指標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1),見表3。

表3 兩組患者妊娠預后比較
3 討論
ICP是發生于妊娠中晚期的特發性疾病,其病因及發病機制不明。目前婦產科臨床上,對本病尚無特殊的治療方法,現多以對癥與保肝治療為主。由于該病顯著地增加了剖宮產機會,圍產兒發病率和死亡率也一直居高不下[6]。我院將孕婦收住院治療ICP的目的,就是緩解因膽鹽潴留于皮膚深層而刺激皮膚感覺神經末梢引起的全身瘙癢癥狀,恢復正常的肝功能,降低血中膽酸的濃度,從而降低因高膽酸血癥所致的胎兒宮內窘迫及死胎發生率、改善妊娠的結局。
文獻報道[7-8],治療ICP的常用藥物主要有:地塞米松、S-腺苷基 L-蛋氨酸(S-Adenosyl-LMethionine,SAMe)即商品名思美泰、熊去氧膽酸(簡稱UDCA)、考來烯胺(消膽胺)。還有2種正在試用的藥物:Epomeidol和瓜耳豆膠。EPomeidol是一種萜類化合物,可通過恢復肝細胞質膜的流動性,逆轉雌激素誘導的膽汁淤積,可以明顯改善瘙癢,未發現明確的毒副作用,但生化指標改善不明顯。瓜耳豆膠是一種凝膠形成的纖維,可促進腸道排泄,減輕瘙癢癥狀,阻止膽汁酸水平的升高,但無法改善膽汁淤積。
本研究中兩組病例西藥均選用地塞米松+思美泰。地塞米松口服,12mg/d,連用7d,后3d逐漸減量而停藥。丁二磺酸腺苷蛋氨酸,500~1000mg/d,靜脈滴注,共兩周。多數患者的癥狀及肝功能均可以明顯好轉,與文獻報道基本相符[9]。在本研究中,尚未發現以上藥物對孕婦及胎兒產生副作用。
中醫理論認為ICP屬濕熱內蘊、營衛不和、氣滯血行不暢[10]。在我國古代醫籍中無此病的專論,散見于“妊娠身癢”、“妊娠黃疸”,且多屬陽黃。《婦科秘方》認為:“婦人胎產遍身生瘡,此癥乃因內受風熱之故”。本研究中兩組病例經本院中醫專家會診,據病癥的臨床表現,通過分析疾病的癥狀、體征來推求病因,認為ICP的發病可能與濕邪、七情內傷、飲食、勞逸、體質等因素有關。主要病機為氣血失調、濕邪蘊脾,黃疸形成的關鍵是濕邪為患。治療易從濕入手,從肝、膽、脾深入來辨證論治ICP,參考有關文獻[11-12]并制定了協議中藥處方清肝利膽退黃飲。中西醫結合組除使用上述西藥外,使用清肝利膽退黃飲,每日1劑,兩周為1個療程。
中西醫結合組使用中西醫結合治療ICP,收到了滿意的效果。與單純西藥治療的單純西藥組比較,皮膚瘙癢減輕快,谷丙轉氨酶、谷草轉氨酶、血總膽汁酸3項生化指標下降快,兩組之間4項觀察指標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從兩組患者妊娠預后變化情況來看,中西醫結合組與單純西藥組各項指標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充分說明中西醫結合治療ICP,可以顯著改善母兒預后,剖宮產率的明顯下降,亦可大大減少圍產兒患病率。
[1]徐瑋瑋,楊璐.妊娠期肝內膽汁淤積癥治療進展[J].中國醫學創新雜志,2014,11(16):137-140.
[2]毛小英,何曉燕.中西醫結合治療妊娠期肝內膽汁淤積癥118例療效觀察[J].浙江中西醫結合雜志,2014,24(5):445-446.
[3]雷玲,李力.妊娠期肝內膽汁淤積癥發病機制研究進展[J].國際婦產科學雜志,2008,35(5):23.
[4]杜巧玲,段濤.膽汁酸與妊娠期肝內膽汁淤積癥發病機制關系的研究進展[J].中華婦產科雜志,2013,48(2):14.
[5]李亞男.妊娠期肝內膽汁淤積癥患者脂質過氧化物及雌激素水平改變及臨床意義[J].中國婦幼保健,2013,28(23):14.
[6]鄧文秋.妊娠期肝內膽汁淤積癥的妊娠結局及治療進展[J].吉林醫學,2013,34(2):330-331.
[7]劉佳,侯莉莉.妊娠肝內膽汁淤積癥的藥物治療進展[J].現代中西醫結合雜志,2012,21(10):63.
[8]袁海英,王建霞,姜靜霞,等.中醫藥治療妊娠期肝內膽汁淤積癥療效觀察[J].山東醫藥,2012,52(39):41.
[9]金方,李艷芳,金克勤.思美泰結合中藥茵白湯治療妊娠肝內膽汁淤積癥[J].浙江中醫藥大學學報,2010,34(2):29.
[10]安利紅,張霞暉.中醫體質分型與妊娠期肝內膽汁淤積癥的關系[J].中國中西醫結合消化雜志,2014,22(3):143-145.
[11]劉小莉.ICP中藥顆粒劑治療肝內膽汁淤積癥120例臨床觀察[J].黑龍江中醫藥,2011(5):5-6.
[12]楊艷芳.妊娠期肝內膽汁淤積癥及其藥物治療[J].醫學信息,2012(2):664-6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