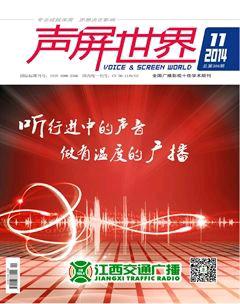論媒體的矯情化傾向
韋聚彬
從汶川大地震、玉樹地震、“7·23”動車事故到雅安地震,再到今年的馬航MH370失聯飛機報道,宣傳式煽情作為國內媒體報道重大災難事件的標準新聞框架,逐漸定型。在這個框架下,公眾的情感趨向左右著新聞事實的挖掘和報道,媒體用一種悲情、自傷、自憐的氛圍將整個報道環境包裹起來,“××挺住,××不哭,我們都是××人”之類的口號一時響遍大江南北。這類口號固然空洞無物,但讓媒體既表達了類似于“政治正確”的道德立場,又輕易俘獲了公眾的好感。這個運作立場,筆者稱之為“矯情化”。
電視節目矯情化的蔓延
媒體的矯情化表現,因災難報道而起,也在災難報道中展示得最集中最明顯。在電視節目中,不單是災難報道,近年來已有蔓延到其他節目類型的趨勢。
歌唱秀綜藝節目中,經常見到觀眾如癡如醉潸然淚下的鏡頭,帶動收看的觀眾們也為之情動,很快有人質疑“有那么值得感動嗎?”最終證明這些人大都是花錢雇傭的“落淚帝”。綜藝節目的選手們也大都有一段感人至深的奮斗歷程,在經過電視手段的精心包裝后,更讓觀眾為之動容,現場氣氛被醞釀到了最高點。可惜,不少網民“爆料”,這些所謂的“追夢音樂人”大都是二三流的職業歌手,平時混跡于舞廳酒吧謀生。就像相親節目的女嘉賓一樣,一旦身份存在造假嫌疑,故事的煽情程度便大打折扣,反落入矯情的質疑中。
電視劇早已是矯情重災區。這兩年抗戰電視劇中出現很多夸張、雷人的虛構場景,因此被網民稱為“抗日神劇”。在這些抗日劇中,甚至有真皮沙發搬上戰場耍酷、嬌俏尼姑殺敵的夸張情節。至于矯情的最高峰,莫過于赤裸少女面向抗日戰士行禮的畫面了。
矯情之風也蔓延到紀錄片中。《舌尖上的中國》第二季還未播完已經飽受非議,例如矯情的文案風格。這種偏抒情的表達力圖尋找隱藏在各種普通食物的制作過程和進食行為背后的人文情懷,由此揭露中國百姓對食物的眷戀、感恩、滿足之情。事實上,或許那只是普通的一道食材、一頓飯而已。《舌尖上的中國2》將“吃”這個較為私人的情感體驗引申和擴展到更社會化的層面,和深沉的說教聯系起來,就已經難免要陷入矯情的窠臼。
媒體矯情化的成因
媒體的矯情化源流追溯起來,有其深層原因和表層原因。
深層原因,與國內電視媒體的定位與屬性息息相關。作為國家精神文明建設的一個機構以及執行黨政行政指令的宣傳機構,輿論導向是電視機構生存的立足點,也是節目基調的出發點。輿論導向的要求,就是傳遞正能量,以正面報道正面宣傳為主,要以電視媒體為“喉舌”,“幫忙而不添亂”。將電視節目的基調進行矯情化處理,可以有效避開節目中的細節追問,而直接跳躍到情緒鼓動層面,將團結、溫暖、頑強、英勇、愛國等正面情緒擴散開來,在受眾中渲染這些情緒所包含的“正能量”,符合電視媒體“喉舌”的工具屬性和娛樂導向的功能屬性。煽情主義、娛樂化等其他傳播手法由于目的都在于吸引收眾更關注事件細節,所以只能成為輔助,而不能完成把控輿論導向的重任,
矯情化展示了國內電視媒體和其他媒體在新媒體背景下巧妙而高超的傳媒適應技巧。相比過去的傳播環境,受眾接觸資訊的渠道更為多元,形成價值觀的因素更為豐富,對新聞事件的判斷也更有主見。因此,過去那種粗暴、直接、生硬的說教手法已然失效。矯情化手法從人性本位出發,關注受眾的內心感受,勇于充當受眾情緒的宣泄口,俘獲受眾的好感是必然的,輿論引導的效果事半功倍。
表層原因,是媒體新聞專業主義的缺失。媒體的管理層、創作者將新聞媒體擬人化、人格化,使之成為注入自然人情感的“小我”,表面上拉近了與受眾的心靈距離,使之更加“可親”“可近”,卻放棄了作為社會瞭望者、觀察者、記錄者和監督者的“大我”。
矯情化的表層原因來自于深層原因。媒體為了規避風險,隔靴搔癢地抒情一番是明哲保身的自選動作。久而久之,這已經成為媒體在報道敏感事件特別是重大災難事故時的慣性思維和行動模式。面對災難,媒體將主要精力用于報道如何調動人力、物力抗災救災,全國人民如何萬眾一心,災區群眾如何不畏艱難與天災抗爭等等,把救援者及其救災行動作為報道主體。今年馬航MH370事件,由于事件發生在國外,媒體本來不必要采用矯情化的應對策略,無奈新聞專業精神的長久缺失,導致挖掘細節的能力有限,唯有以“無招勝有招”。
由于矯情化以正面情感為皈依,相當于在新聞事件中占領了道德高地,幾乎立于不敗之地,使得這一手法屢試不爽,即使有所異議,也會淹沒在強大的公共道德譴責聲浪中。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南方周末》用5月22日和5月29日兩期的“大地震現場報告”“大地震現場再報告”,共42個版面推出超過100篇報道,涉及震災救援、醫療急救、學校之殤、重建之思等等,因報道對震災現場人性弱點的真實描述,以及坍塌的學校建筑反思,引發網絡激辯。反對者指責《南方周末》“劍走偏鋒”“帶著有色眼鏡看世界”,狼狽之余,使其他新聞機構更加堅定了矯情化的處理手法。
媒體矯情化的危害
矯情化雖然是以感性代替理性、以口號代替行動,但也不能一概予以否定。災難會自然催生出社會一種眾志成城的情感氛圍,災難越大,這種凝聚力也越大,悲壯的情懷會使人們站到一起去感受彼此的溫度。而且災難之初,在災害中感到無力的人們,也需要情感的表達去尋找一種力量支撐。很多時候并不是災難中的人需要這種情感支撐,而是遠在千里之外的人,借助這種表達來釋放自己的焦慮。這不是中國特有,每個社會面臨災難的時候,國家和社會都會本能地被動員起來,媒體會表現并推動這種情感凝聚。
這是媒體矯情化的社會心理基礎。事實上國內從官方到媒體到民眾,真正開始有意識地思考如何應對災難,也是近十年的事。2008年汶川大地震時,有聲音批評國內民眾只知道旁觀和祈福,卻沒有專業的民間救災行動。于是到2013年雅安地震時,赴災區救援的民間團體蜂擁而至,卻又招來“嚴重影響救災效率”“救援力量盲目涌入阻礙救援”等非議。民眾已不滿足于情感上投入救災,開始訴諸行動,雖尚待規范和引導,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媒體矯情化的處理模式已經受到挑戰。
損害媒體公信力。今年馬航MH370事件從發生至3月20日,在自媒體上,@人民日報發布相關微博達到287條,@央視新聞發布409條,@新華視點發布183條,信息密度峰值甚至達到10分鐘更新一條,不可謂不多,可惜幾乎全是轉發、轉載境外媒體的消息。真正原創的,就只有“北京,晴。MH370,等你回家”之類的祈禱和呼喊。一條廣泛傳播的微信就寫道:“馬航事件新聞戰——幾乎所有的干貨都是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路透、BBC等英美媒體挖出來的。CNN司法口記者找到國際刑警坐實假護照;WSJ(《華爾街日報》)挖掘羅羅(生產和維護引擎的英國羅爾斯羅伊斯公司)引擎線索,后披露折返;NYT(《紐約時報》)認定西拐,很可能從美政府線人處拿到雷達數據;ABC第一時間披露眾包搜索;BBC等最后找到衛星公司,讓我們知道了8:11。它們的報道真正對馬來西亞政府形成了壓力,體現了媒體的力量所在。反觀中國媒體,除了搬運外媒,就只會一遍遍喊著‘馬航,我們等你回家,為你祈禱作蒼白廉價的煽情。”兩相比較,報道含金量不可同日而語,直接損害了媒體的公信力。
損害新聞專業精神。雅安地震中,某女記者多次打斷醫生搶救病人過程,耽誤時間,采訪災民時竟然還問他們今天喝到粥開不開心,這種情景在災難報道中已經不止一次地出現,輿論批評媒體冷漠、不懂得人文關懷。這是媒體太貼近報道主體的緣故,而矯情化則是另一種極端——與報道主體過度疏離。小情小調式的無休止的煽情和心靈雞湯,事實上損害了媒體的新聞專業精神。
矯情化看似在情感上與受眾親密無間地融合在一起,從另一個角度看就是在新聞事實上與受眾保持距離。在馬航MH370事件剛剛傳到國內時,@財經網、@人民日報發出微倡議《請給家屬們一個安靜空間》,@新華視點、@央視新聞、@環球時報等積極響應,@鳳凰網亦跟進轉發,微博微信上掀起了一輪針對“無良記者”“嗜血媒體”的聲討。這種看似正義的媒體采訪倫理,隱藏著一個更大的新聞專業精神悖論:媒體的缺席難道不就是最嚴重地違背媒體倫理?電視媒體、平面媒體和網絡媒體竟然罕有地意見一致,為了突顯“人文關懷”而不惜放棄媒體職責。在《舌尖上的中國2》中,制作方已經承認了多處畫面和情節的造假。例如,為拍攝出自貢鹽工揮汗如雨的鏡頭而用水壺灑水“造汗”、藏族小伙攀上高樹取蜜實際并沒有爬高等。盡管節目組認為并沒有違背原則,要表達的“意義”也達到了,但他們沒有意識到這正是“只管結果、不管過程”“只問意義、不問細節”的思想在作怪,犯了新聞專業精神之大忌。
媚俗、媚眾與人禍。一定程度上,矯情化的處理模式是媒體在回應公眾的情感期待。2008年《南方周末》關于汶川地震的那組報道,中性、客觀、帶有距離感的筆調及其背后冷峻的社會制度的思考,顯然讓很多受眾感到難以接受。眾怒難犯,國內媒體的溫情手法愈來愈純熟,顧不上報道與記錄客觀的真實了。長此以往,媒體將陷入媚俗、媚眾的媒體倫理誤區。這里的媚俗、媚眾,與我們以往所批評的綜藝節目里的媚俗、媚眾有所區別。后者指的是電視節目迎合受眾的低級趣味和社會上的不健康風氣,前者指媒體對公眾感性化情緒的過分迎合。
矯情化報道模式的一個重要觀點是:媒體不應去關注、報道和揭露新聞事件里包含的負面信息,將此類報道視為“污蔑”“有色眼鏡”“心理陰暗”“添亂”等。結果是,人性的軟弱、利益的沖突,恐懼逃避的行為,以及可能存在的瀆職、腐敗,都被媒體有意回避和忽視了。這是諱疾忌醫式的報道理念,本應得到糾正的某些工作失誤被掩蓋住,在下一次事故中重復上演。從這個角度看,媒體要對這樣的“人禍”負上一定責任。
結語:理性的曙光
在公眾迷茫時,媒體要保持清醒;在公眾焦慮時,媒體在刨根問底;在公眾需要答案時,媒體第一時間做出解釋——這是現代大眾媒體的職業使命。考慮人心凝聚力,考慮鼓舞士氣,情感化的新聞表達有重要的社會意義,只是媒體在回應了人們的情感需求后,應繼之以事實、理性和邏輯,因為這是最令人信服的媒體專業表現,是公眾對新聞媒體的天然期待。新聞價值應該成為媒體報道策略中最大的決定因素,而非首先考慮如何安撫公眾。
值得欣慰的是,對于矯情化的報道模式,無論是公眾還是媒體,都已經表露出厭煩,不少媒體人也進行了自我批評和反思。理性、客觀、冷靜的媒體風格和專業的媒體素養,是我們值得期待的未來。
(作者單位:廣東廣播電視臺)
欄目責編:邵滿春
參考文獻:
1.部分資料來自新浪微博、騰訊微博、微信及鳳凰網、人民網、FT中文網等網絡媒體。
2.王 卉:《災難報道中的新聞倫理——基于汶川大地震的案例分析》,《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8(9)。
3.陳力丹,毛湛文:《期待理性而專業的災難報道——蘆山和汶川地震媒體報道比較》,《新聞愛好者》,2013(6)。
4.郝 洪:《我們需要什么樣的災難報道——從〈南方周末〉震災報道引發的爭議談起》,《新聞記者》,2008(7)。
5.陳力丹,李志敏:《復雜信息傳播中的公眾心理與傳媒的職責——以“馬航失聯事件”為例》,《新聞愛好者》,2014(4)。
6.王傳寶,王金禮:《新聞煽情主義的倫理批判》,《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