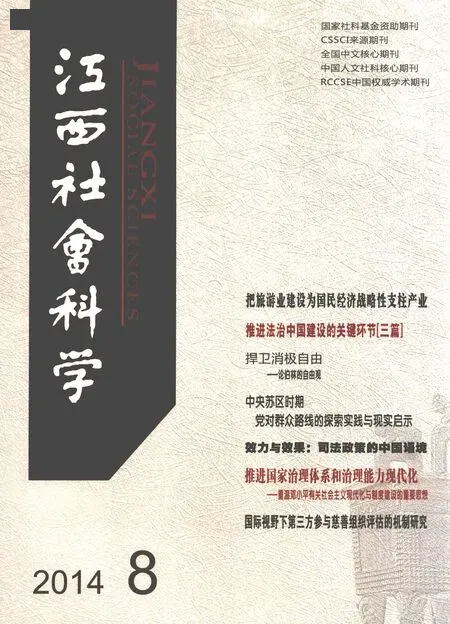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的合理性
■張 敏
一.交往理論的淵源
(一)交往理論的歷史形態(tài)
17 世紀(jì)英國經(jīng)驗(yàn)論的代表人物洛克在分析認(rèn)識(shí)論問題時(shí)直接走向交往問題,他認(rèn)為,人作為社會(huì)動(dòng)物,需要相互溝通并達(dá)成理解,否則社會(huì)便不能帶給人安慰和利益。這一歷史淵源使很多學(xué)者將交往理論的源頭追溯至洛克。休謨繼承了洛克的觀點(diǎn),他把交往理解為一種“共感”,即認(rèn)識(shí)上的溝通,它能夠使人們的心靈之間彼此成為“相互反映的鏡子”[1](P635)。康德的“絕對命令”是人們在交往中必須遵守的道德律令,它反對功利主義的交往意識(shí),將交往由對立引向統(tǒng)一。在馬克思那里,交往理性的意義變得空前豐富:“為了不致喪失已經(jīng)取得的成果,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實(shí),人們在他們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適合于既得的生產(chǎn)力時(shí),就不得不改變他們繼承下來的一切社會(huì)形式。——我們在這里使用‘Commerce’一詞是就它的最廣泛的意義而言,就像在德文中使用‘Verkehr’一詞一樣。”[2](P532)馬克思始終把交往問題放在人類社會(huì)歷史發(fā)展的重要位置上,但哈貝馬斯對馬克思的交往理論存在著不同的看法。例如,馬克思在表述生產(chǎn)力與生產(chǎn)關(guān)系、經(jīng)濟(jì)基礎(chǔ)和上層建筑的關(guān)系時(shí),強(qiáng)調(diào)勞動(dòng)、生產(chǎn)實(shí)踐在社會(huì)歷史中的重要作用,但“物質(zhì)利益的難事”則使馬克思轉(zhuǎn)向?qū)φ谓?jīng)濟(jì)學(xué)的分析。哈貝馬斯并不承認(rèn)馬克思建構(gòu)社會(huì)歷史理論的基本材料——生產(chǎn)實(shí)踐,他認(rèn)為,這種材料無法支撐現(xiàn)代資本主義社會(huì)科學(xué)技術(shù)意識(shí)形態(tài)形式的摩天大廈,哈貝馬斯要以一種交往理性代替實(shí)踐理性,以交互性、規(guī)范性為原則重建歷史唯物主義。
(二)交往的合理性維度
對韋伯“合理性”思想的批判與改造,是哈貝馬斯交往理論可能性的理論前提。韋伯的“合理性”思想主要從合理性的工具性視角批判技術(shù)意識(shí)形態(tài)的背離效應(yīng),在哈貝馬斯看來,這種從工具合理性出發(fā)的批判理論無法解決這種背離效應(yīng),他本人則要建立一種更加合理的“合理性”,以解決現(xiàn)代性的諸多背離效應(yīng)。
在分析交往合理性之前,我們除了要了解交往合理性的理論演變外,還要把握它的時(shí)代歷史背景,這些都是產(chǎn)生合理性交往的理論前提。交往合理性的生成背景可以概括為兩點(diǎn)。第一,生存論的理性主義。兩次世界大戰(zhàn)的陰霾以及資本主義世界的技術(shù)理性使哲學(xué)轉(zhuǎn)入生存論視野,第一代法蘭克福學(xué)者已經(jīng)從啟蒙理性、心理機(jī)制和性格結(jié)構(gòu)等理性主義視角揭示了非理性主義的幽靈個(gè)體的生存境遇。無獨(dú)有偶,存在主義的代表,如海德格爾、薩特等從生存論的理性主義層面同樣揭示了這一時(shí)代特征。所以,對于第二代法蘭克福學(xué)派代表的哈貝馬斯來講,其歸宿必然是關(guān)注人之生存境遇以及現(xiàn)代性的悖論。第二,主體際性理論范式。近代哲學(xué)發(fā)展了主觀主義、先驗(yàn)主義的哲學(xué)路向,但這些路向依然無法脫離主客體二元思維模式的窠臼。笛卡爾的“我思”、康德的“人為自然立法”、費(fèi)希特的“絕對自我”等,都力圖超越這種思維范式。然而,隨著時(shí)代衍生的科學(xué)信仰危機(jī)以及學(xué)理層面的認(rèn)識(shí)論追溯,孤立的、絕對的、自由的單向度主體觀念逐漸被消解在語言學(xué)、交往哲學(xué)、后現(xiàn)代主義等哲學(xué)語境下,科學(xué)技術(shù)等意識(shí)形態(tài)的獨(dú)立化和系統(tǒng)化也正日漸滲入生活世界之中,對作為生活世界的“意義世界”的社會(huì)、文化、個(gè)性施行無情的“殖民”,這一切都迫使哈貝馬斯反思傳統(tǒng)的哲學(xué)理論范式,從而在語用學(xué)、闡釋學(xué)的助推下生成了以平等、協(xié)商、意見一致為基礎(chǔ)的交互性理論范式。由于這種理論范式的對象是雙向度的主體,所以,可以把這種理論范式稱為“主體際性”的理論范式。
二、交往行為合理化得以可能的條件
哈貝馬斯把行為分為四種類型:即目的性行為、規(guī)范調(diào)解行為、戲劇性行為、交往行為。這四種行為有各自的活動(dòng)領(lǐng)域,它們側(cè)重于不同的“世界”,其內(nèi)涵以及與交往行為的關(guān)聯(lián)性是理解交往行為合理性的前提,分析這些行為的類型能凸顯交往行為的意義。
目的性行為,也稱工具性行為,是主體利用工具介入客觀世界從而實(shí)現(xiàn)目的的行為。哈貝馬斯認(rèn)為,從亞里士多德的“形式—目的因”開始,哲學(xué)、社會(huì)學(xué)等學(xué)科就已將目的性行為固定化,作為研究自身領(lǐng)域基本問題的行為方式。
規(guī)范調(diào)解行為通常發(fā)生在群體之內(nèi),與單獨(dú)的個(gè)體行為并無關(guān)聯(lián)。在群體內(nèi),成員遵守共同的規(guī)范,接受共同的價(jià)值標(biāo)準(zhǔn),在此基礎(chǔ)上進(jìn)行各種活動(dòng)。
戲劇性行為是指行為者將社會(huì)成員看作自己的觀眾,在這些觀眾面前表現(xiàn)自己的主觀行為。這種行為同樣與單獨(dú)的個(gè)體沒有關(guān)聯(lián)性,但也并非是一種群體性行為,而是針對互動(dòng)的參與者而構(gòu)成的行為,參與者彼此互為觀眾,互相表演,相互吸引。
交往行為是以符號(hào)和語言為媒介,通過對話和協(xié)商達(dá)成主體間理解一致的行為,它遵守主體間相互認(rèn)同的規(guī)范,這些規(guī)范決定著雙方的交往行為,把持著行為者之間的互相期待。
哈貝馬斯認(rèn)為,四種行為類型各有自身關(guān)聯(lián)的“世界”。目的性行為與客觀世界相關(guān)聯(lián),它通過工具介入客觀世界,實(shí)現(xiàn)自己的計(jì)劃和目的;規(guī)范調(diào)解行為對應(yīng)社會(huì)世界,不可否認(rèn),社會(huì)關(guān)系的世界充滿了各種群體性的規(guī)范,主體間也是基于這種規(guī)范而建立交往行動(dòng)的,同時(shí),規(guī)范性行為為交往行為提出了正當(dāng)性和有效性要求;戲劇性行為與主觀世界相關(guān)聯(lián)。交往行為與生活世界相關(guān)聯(lián),生活世界是交往行為運(yùn)行其中的境域。“交往行者不可能走出其生活世界境域。他們本身作為闡釋者憑籍言語行為屬于生活世界。”[3](P194)生活世界是以文化、社會(huì)和個(gè)性為構(gòu)成要素的,也就是說,生活世界是這些要素的境域和視野。生活世界的這三個(gè)要素相互關(guān)聯(lián),形成復(fù)雜的意義關(guān)系。
(一)交往合理化的有效性要件
哈貝馬斯非常注重奧斯丁以言表意行為和以言行事行為的區(qū)分,并在一系列假設(shè)和圖表的推演下得出了合理交往的有效性要求:“一個(gè)交往過程的參與者以達(dá)到理解為指向的活動(dòng)只能在下述條件下進(jìn)行:參與者在其言語行為中使用可領(lǐng)會(huì)的句子時(shí),需通過某種可接受的方式提出三項(xiàng)有效性要求:(1)對一個(gè)被陳述的陳述性內(nèi)容或被提及的陳述內(nèi)容的存在性先決條件,他要求真實(shí)性;(2)對規(guī)范或價(jià)值——在一個(gè)給定的關(guān)聯(lián)域中,這些規(guī)范或價(jià)值將證明一個(gè)施行式建立起來的人際關(guān)系為正當(dāng)——他要求正確性(或適宜性);(3)對被表達(dá)的意向,他要求真誠性。”[4](P67)這些有效性要求是反思理性對交往理性提出的要求,即要求理論理性展現(xiàn)真理性,實(shí)踐理性產(chǎn)生真誠性,審美理性表達(dá)正確性。這三種有效性就是哈貝馬斯交往行為合理性的一般原則。“與有目的理性的行為不同,交往行為是定向于主體際地遵循與相互期望聯(lián)系的有效規(guī)范。在交往過程中,言語的有效性基礎(chǔ)是預(yù)先設(shè)定的,參與者之間所提出的并且相互認(rèn)可的普遍有效性要求使一般負(fù)載著行為的交感成為可能。”[4](P121)我們可以從以下四方面闡述這種合理性的內(nèi)涵。
第一,作為一種主體際的交互性行為,交往的合理化首先體現(xiàn)平等的交互性原則,也就是說,交往行為的合理化首先體現(xiàn)為一種道德實(shí)踐方面的合理化,而不是工具行為的合理化。
第二,交往行為是在社會(huì)規(guī)范的框架內(nèi)運(yùn)動(dòng)的行為,在主體間意向表達(dá)的真誠性以及某種交往儀式下得以鞏固發(fā)展。這是一種在主體道德原則之外的規(guī)范框架下的主體間的理性行為。
第三,語言和符號(hào)成為交往行為的基本行為,它是主體間溝通交流的媒介,主體間在普通語用學(xué)的基礎(chǔ)上通過語言和符號(hào)的媒介作用相互協(xié)調(diào)彼此意見,從而建立順暢的交往關(guān)系,實(shí)現(xiàn)交往行為的理性化。
第四,交往行為合理性的最顯著的衡量標(biāo)準(zhǔn)是主體間是否達(dá)成理解的一致性,這是交往最終的意義所在,也是主體間性的意義所在。
綜上所述,交往行為的合理化是一種以道德為原則的,彼此間在一定社會(huì)規(guī)范框架內(nèi),在語言和符號(hào)的中介作用下所達(dá)成的主體間協(xié)調(diào)一致、相互理解的合理化行為。這種合理化克服了韋伯式的目的合理化的單向度局限性,將合理化概念推向更高的層次,避免了從工具手段獲得單向度的真理時(shí)遺失主體性的價(jià)值尺度。同時(shí),這種合理性也展現(xiàn)了哈貝馬斯本人對從德國古典哲學(xué)沿襲下來的自我意識(shí)主義的抗衡,力求以主體間的對話機(jī)制來形成獨(dú)特的認(rèn)識(shí)論視角。
三、交往行為合理化的補(bǔ)充性要件——“生活世界”
(一)生活世界與世界的關(guān)聯(lián)
在哈貝馬斯之前,許多哲學(xué)家的論述都涉及生活世界。笛卡爾試圖在科學(xué)領(lǐng)域之外的生活世界中尋找客觀有效性要求,胡塞爾也借助現(xiàn)象學(xué)的手段追蹤日常生活中被遺忘的隱性知識(shí),他將生活世界理解為原初的、前科學(xué)的意義世界,以此來反駁測量、邏輯、數(shù)學(xué)等科學(xué)的實(shí)證客觀主義。海德格爾同樣深刻剖析生活世界,他從生存論視角分析了“此在”的生存體驗(yàn)以及與他人的主體間結(jié)構(gòu)。他與胡塞爾對生活世界的理解存在著共同性,即都是批判對科學(xué)世界的理性化、客體化、技術(shù)化的異化狀態(tài)。實(shí)際上,哈貝馬斯沿用了胡塞爾和海德格爾的“生活世界”概念,繼續(xù)將生活世界作為主體間合理交往以克服系統(tǒng)的殖民化弊病:“生活的走向以及同生活走向的持續(xù)聯(lián)系,構(gòu)成精神科學(xué)結(jié)構(gòu)中的第一個(gè)基本特征;然而,精神科學(xué)的基礎(chǔ)卻是經(jīng)歷、理解和生活經(jīng)驗(yàn)。生活和精神科學(xué)賴以互存的這種直接關(guān)系,在精神科學(xué)中導(dǎo)致了生活的傾向和這些傾向的科學(xué)目標(biāo)之間的矛盾。”[5](P169)哈貝馬斯進(jìn)而將“世界”和“生活世界”這兩個(gè)概念理解為“對象的論題化”和“創(chuàng)造性活動(dòng)的可能場所”,二者對應(yīng)于不同性質(zhì)行為的活動(dòng)場合,必須嚴(yán)格區(qū)分。“世界”是目的理性行為以工具為媒介追求利益和目的的外在環(huán)境,而“生活世界”是交往理性在相互理解的條件下的一種交互性的意義場所,為合理交往提供文化、個(gè)性、社會(huì)層面的背景要素,在言說、符號(hào)等交互性媒介下以傳統(tǒng)的力量支撐交往行為,為交往者提供交往資質(zhì):“言語者和聽者從共同的生活世界出發(fā)就客觀的、社會(huì)的和主觀的世界中的某物達(dá)成相互理解。”[3](P192)但是,哈貝馬斯并沒有像胡塞爾那樣對生活世界進(jìn)行意識(shí)層面的分析,而是與理解和語言相關(guān)聯(lián),為交往的合理性服務(wù)。
(二)生活世界對交往合理性的補(bǔ)充功能
哈貝馬斯提出了合理交往的三個(gè)有效性要件,交往行動(dòng)在遵守這些要件的基礎(chǔ)上進(jìn)行相互理解的、協(xié)商的交往。那么,判定交往行動(dòng)最終是否有效、是否合理就需要一定的判定標(biāo)準(zhǔn),因此,哈貝馬斯以生活世界理論來完成這一評(píng)判任務(wù)。哈貝馬斯認(rèn)為,生活世界似乎是交往雙方在其中相遇的先驗(yàn)場所,交往行為雙方可以利用生活世界的背景材料來指引交往的協(xié)調(diào)開展,也就是說,交往者運(yùn)用“三個(gè)世界”(客觀世界、社會(huì)世界、主觀世界)的文化樣態(tài),批判地整合交往的內(nèi)容,從而獲得交往間意義的真理,協(xié)調(diào)行動(dòng),達(dá)成共識(shí),最終保證交往的有效性。具體來講,哈貝馬斯從兩個(gè)視角闡述了生活世界對有效交往或合理交往的作用。
1.生活世界的結(jié)構(gòu)功能。哈貝馬斯改造了帕森斯的結(jié)構(gòu)功能主義,將文化、社會(huì)和個(gè)性的不同意義網(wǎng)交織成一種穩(wěn)定的網(wǎng)式結(jié)構(gòu)。“我無論是在肉體之中,還是作為肉體,一直都是在一個(gè)主體間所共有的世界里,集體共同居住的生活世界就像文本和語境一樣相互滲透,相互重疊,直到相互構(gòu)成網(wǎng)絡(luò)。”[6(P79)這一復(fù)雜的“意義”網(wǎng)絡(luò)可以為主體間傳遞信息和真誠提供大量的社會(huì)化的評(píng)審資源,而主體間的真誠、規(guī)范交往也能起到維護(hù)并整合社會(huì)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文化本身是一種始終生成的行為結(jié)果,它往復(fù)循環(huán),最終在人的交往功能下形成一股新的力量,其積極方面為人類的自我同一性產(chǎn)生綿延不斷的知識(shí)場,交往者不斷提升交往資質(zhì),從而使交往能夠保持一種歷史的延續(xù)性。被這種新的文化力量拋在身后的文化則形成另一種力量——傳統(tǒng),它滲透在客觀世界、主觀世界以及社會(huì)世界當(dāng)中,同樣為主體間交往的統(tǒng)一性提供有效的前理解性支撐,它能夠保持交往行為資質(zhì)的最低限度,或者說,能夠保證交往行為資質(zhì)不至退化。
2.生活世界的傳承功能。哈貝馬斯在伽達(dá)默爾那里吸收了解釋學(xué)的論點(diǎn):“在情境相關(guān)的視角里,生活世界表現(xiàn)為不可動(dòng)搖的存儲(chǔ)庫,交往參與者為了合作的解釋過程可以利用這些自我理解力和堅(jiān)定信念。”[6(P124)也就是說,生活世界為交往提供理解的源泉,這正是伽達(dá)默爾所謂“前理解”的文化層面,為交往情境提供可選擇的規(guī)則和手段。第一個(gè)交往話語中的理解引用了生活世界存儲(chǔ)庫的資源,而這種成功的話語理解產(chǎn)物必將對下一個(gè)理解產(chǎn)生效果。從這種意義上講,生活世界具有傳承性功能,而這種傳承功能無疑是建立在對生活世界本身的自明性的基礎(chǔ)之上的,哈貝馬斯將這種自明性表述為“絕對的自明性”、“總體化力量”、“背景知識(shí)整體論”。所以,在這種意義上,哈貝馬斯將生活世界理解為“交往行動(dòng)者‘一直已經(jīng)’在其中運(yùn)動(dòng)的視野”[3](P166),“這種生活世界構(gòu)成了一種現(xiàn)實(shí)的活動(dòng)的背景”[3](P171),是在傳承的意義上講的。
四、結(jié)語
哈貝馬斯闡述的交往合理性有充足的論據(jù),也有一定的評(píng)判標(biāo)準(zhǔn),他不但充分考察了交往合理性的前提條件,而且從生活世界的視角補(bǔ)充說明了交往的合理性問題,為交往行動(dòng)者在理解協(xié)商的基礎(chǔ)上實(shí)現(xiàn)交往提供了理論基礎(chǔ)。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對“主體間性”及交往問題的理解不能過于片面。我們知道,當(dāng)代哲學(xué)已經(jīng)從不同視角考察“交往行為”,例如,胡塞爾現(xiàn)象學(xué)的意向性理論分析,也具有交往性的哲學(xué)維度;哲學(xué)解釋學(xué)和語言哲學(xué)從語言、意義、心理的層面考察交往問題,而吉登斯則從現(xiàn)實(shí)日常情境的角度揭示了主體間交往的構(gòu)成性條件。所以,對主體間性以及交往問題的理解不能陷入一種固定化模式,需要從不同層面進(jìn)行探討。
[1](英)大衛(wèi)·休謨.人性論[M].關(guān)文運(yùn),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0.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德)尤爾根·哈貝馬斯.交往行動(dòng)理論(第2卷)[M].洪佩郁,藺青,譯.重慶:重慶出版社,1994.
[4](德)尤爾根·哈貝馬斯.交往與社會(huì)進(jìn)化[M].張博樹,譯.重慶:重慶出版社,1989.
[5](德)尤爾根·哈貝馬斯.認(rèn)識(shí)與興趣[M].郭官義,李黎,譯.上海:學(xué)林出版社,1999.
[6](德)尤爾根·哈貝馬斯.后形而上學(xué)思想[M].曹衛(wèi)東,付德根,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