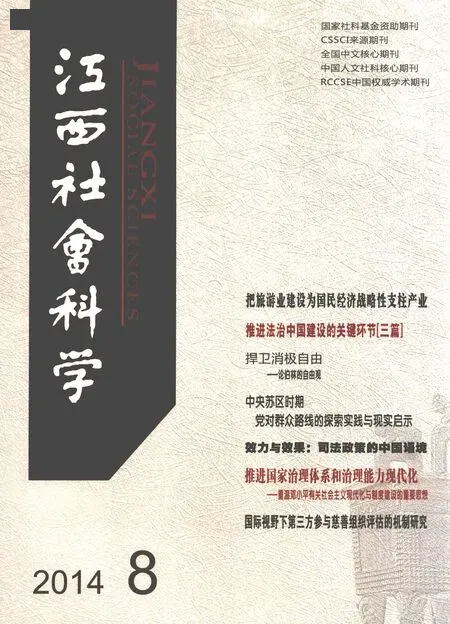釋良琦與玉山雅集考論
■李舜臣
玉山雅集,是指元季在江蘇昆山文人顧瑛的私邸——玉山草堂舉行的文人集會。“其園池之盛,圖史之富,與夫餼館聲伎,并鼎甲一時;才情妙麗,與諸人略相酬對,風流文雅,著稱東南。”[1](卷二十《棲逸第十二》,P744)處亂世中的文人功名幻滅、進退失據,沉溺于湖光山色、醇酒美色,固然有違正統的價值取向,卻也符合“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常理。可是,向以“清凈”、“無為”而著稱的釋子、仙道亦廁身座中,與文人一起征歌選色、斗酒競詩,卻實在值得玩味。據統計,先后參與玉山雅集的僧侶有三十余人,而尤以釋良琦的聲名最著。明人李日華即云:“玉山草堂中諸詞客每有倡和,必琦為發端,諸公雅推重之。”[2](卷三,P705)釋良琦不僅參加了玉山雅集的大部分活動,而且詩藝高超,在逞才斗技中絲毫不亞于其他文人。同時,以釋良琦為代表的釋子的加入,不僅使玉山雅集具備了多元的文化色彩,更體現了元末“狂禪”之風的盛況,反映了佛教世俗化進程日益加劇的趨勢。①
一、釋良琦的生平及其雅集活動
釋良琦的碑傳材料,未見存世。顧瑛所編《草堂雅集》為其立有小傳:“釋良琦,字元璞,姑蘇人。自幼讀書,學禪白云山中,性操溫雅,澹然無塵想。詩聲尤著江湖間。與楊鐵崖、郯九成累過余草堂,超然物外人也。”[3](卷十六,P1134)良琦嘗主持吳縣天平山龍門禪寺、浙江云門寺,故又有“龍門山釋”、“云門翁”、“山澤臞者”、“云門山樵”之號。良琦的生卒年,未可確考。《式古堂書畫匯考》卷四十六“松雪二墨羊逸筆并題卷題識”,收有他撰于洪武十七年(1384)七月十九日的題識[4](第829 冊,卷四十六,P21);另卷六“晉王羲之七月帖”,有他撰于洪武十七年八月的題識[4](第827 冊卷六,P262)。據此可知,至遲洪武十七年八月,良琦依然在世。
楊維楨撰有一篇《琦上人孝養序》,是了解良琦生平、志趣的重要文獻:
琦上人,吳之儒氏也。自幼落發為浮屠(于)天平山中,壯游四明雪竇,見石室禪師,深器之,俾職記室。后浮游淮、湘間,以肆其輕世之志。未幾,丞相府以東土名宿所推,俾主毗陵龍興禪寺。留不期月,忽自默曰:“出家以能脫俗而去,使俗高而慕之,以為不可及也。奈何又掛名官府,罷送迎道路,覆為俗所厭邪?且余母耋矣。”即飄然荷包笠,尋先人舊廬于蠡澤之上,而先廬敝矣。今將筑屋一區,以養其母而終其天年。計未知所出,首以其事告予,蓋上人嘗以儒行為余友者也。……至正八年秋七月序。[5](卷十,P473-474)
文中既云“尋先人舊廬于蠡澤之上”,則其祖籍或在江西。良琦自幼出家,師事石室禪師。石室禪師,即石室祖瑛,臨濟宗居澗系下四世孫。元末釋來復所編《澹游集》卷二亦謂良琦“嗣法育王石室瑛禪師”[6](卷上,P230),可與之互證。良琦嘗以丞相府之命主持龍興禪寺,卻無逢迎之意;顧瑛所稱“超然物外”,于此亦可得證實。值得一提的是,石室祖瑛的師弟笑隱大?亦有《次韻石室贈琦上人》一詩,其中有“感子遠訪尋,氣肅蟄聲閉”[7](卷一,P532)句,蓋亦為良琦此次訪祖而作。
除以上材料外,我們所知良琦的信息,多源于《玉山名勝集》、《玉山紀游》、《草堂雅集》等文獻中。這些文獻頗翔實地記錄了他歷次參與雅集的情形和詩作。
良琦與顧瑛之交,至遲不晚于至正七年(1347)。是年八月,良琦從吳興至昆山,受吳克恭之托,將趙孟頫之子趙雍所臨《五花馬圖》贈予顧瑛。并撰詩云:“王孫昨在水晶宮,貌得龍眠八尺驄。為言持寄玉山去,當與桃源五馬同。”[4](第829冊,卷四十六《趙仲穆臨李伯時鳳頭驄圖并題》,P45 -46)是年雅集尚未開始,但良琦與顧瑛即有交誼。
良琦首次出現于雅集座中,是在至正八年(1347)三月三日。是日,他因耳聞上月十九日楊維楨、顧瑛等人的雅集盛況②,遂與朋友剡韶從吳興至玉山,顧瑛為之“張樂置酒,清歌雅論”,并命良琦撰詩,“人言不減楊侯雅集時”。[8]
至正九年(1348)夏,良琦與會籍道士于立至玉山,適逢吳克恭亦館于此,酒酣之余,賦詩無虛日。時炎雨既霽,涼陰如秋,座中姬小瓊英、翠屏、素真三人侍坐,以杜甫“暗水流花徑,春星帶草堂”之韻,拈鬮賦詩,所作之詩皆清麗奇古,與玉山名勝相得益彰。[8](卷三“吳克恭分題詩序”,P42)次日,楊維楨與吳克恭臥酒不起,良琦與于立則于東廡池上,復聯句若干。[8](卷二“于立聯句引”,P24)
隨時日之推移,玉山雅集在東南的聲望日增,良琦的詩名亦大振。至正十年(1350)正月,陳基造訪玉山,稱:“予于玉山隱君別三四年間,其與會稽楊鐵崖、遂昌鄭有道、匡廬于煉師、苕溪郯九成、吳僧琦元璞,日有詩酒之娛,而其更唱迭和之見于篇什者,往往傳誦于人。”[8](卷三“ 陳基序”,P44)這年五月,良琦與吳克恭、于立等人再訪玉山,儼然已為座中核心,十八日的唱和詩序即由他所撰。
至正十年,是玉山雅集最為繁盛之時,良琦頻繁地往還吳興、玉山兩地。他先后與楊維楨、于立、吳世顯等人在芝云堂、秋華亭、漁莊等名勝歡會宴飲,直至七月十五日,方離玉山,泛舟下婁江。然半月后,又還玉山,與顧瑛、袁華、于立、王祎、趙元等宴于芝云堂。八月十九日,詞人張翥代祀歸抵吳門,顧瑛宴于草堂,良琦亦在座中。
作為元末江南文人的大型集會,玉山雅集的成員相對松散,地點亦不拘限于昆山一地,還包括顧瑛領銜的吳越諸地的宴集活動。因此,袁華還特地編有《玉山紀游》,輯錄顧瑛等江南文人的紀游之作。良琦也經常參與此種外游活動。例如,至正十年八月二十二日,良琦即邀請顧瑛、于立至天平山唱和。[9](于立《與客游靈巖山中雜詠詩并小序》)至正十一年正月至三月間,又與顧瑛、郯韶等至蘇州虎丘。五月二十八日,顧瑛與楊維楨、葛元哲諸人至錢塘西湖同祭道士張雨,次日,又與良琦、袁華、顧佐、馮郁、張渥等泛舟湖上,置酒張樂以娛,并以蘇軾詩“山色空濛雨亦奇”分韻賦詩。良琦為此次西湖之游撰序:“吁,自《伐木》詩廢,交道久缺,而況于今時哉!仲瑛之于朋,交死生交,情能盡其義,可謂善與人交者也。”[9](“游西湖分韻詩并序”,P488)
秀美山水與醇酒美色,令顧瑛、良琦等人終日流連其中,玉山恍若一方凈土,與世隔絕。然而,覆巢之下,焉有完卵?隨著元末社會動蕩的加劇,這樣的生活逐漸發生了變化,甚至連寓處方外的良琦亦感覺到一絲隱憂。至正十二年五月,良琦過玉山,所作《夏五月過玉山草堂見婁江諸故人漫興之作遂繼詠》中就寫道:“梅風發時海寇去,相見要令懷抱開。”這年的重陽節,蕭景微至玉山,顧瑛、袁華等人雖與其“觴詠笑樂”,但以“滿城風雨近重陽”分韻賦詩,分明有深意在。[8](卷三“蕭景微序”,P45)至正十四年底,顧瑛應都萬戶納麟哈剌公之命,督守西關,繼舉知州事;次年,顧瑛攜其母避兵于吳興商溪,后兵入草堂,劫所藏書畫而去。倉皇慘淡之際,顧瑛遂祝發以謝世緣,玉山雅集亦逐漸歸于消歇。
至正十七年二月,釋良琦過玉山,與顧瑛登芙蓉渚遠眺。良琦有詩曰:“避地去年因共難,臨池今日喜同閑。晴沙草接春簾外,落日鳥鳴芳渚間。詩卷一朝歸趙璧,野亭百里見吳山。已知金粟真成隱,約我釣船長往還。”詩下注曰:“去年春,予與玉山主者避難于霅上,家之舊藏書畫多失去。今年二月,予自松陵放舟過玉山中,時芙蓉之渚之軒新成,主人與予登眺其上,洗人心目,不覺人情暢然,與去年難中不同也。”[8](卷五,P90)即記載了近年紛紜動蕩的世事。是年二月廿二日,良琦又泛舟玉山,并以書招陸仁同至,葛元素亦至,“各以道路蕪梗,暌離隔歲,慰藉問勞,握手敘契闊,語剌剌不能休”,眾人遂留數日,以詩酒慰藉心頭的煩憂。廿八日,釋良琦欲歸吳江,仲瑛止其行,又張筵于柳塘春,飲酒賦詩為樂。席間,顧瑛說:“今日得與諸君合并,不知良晤又幾何時,因思古人折柳贈別之意,不能不戚然于懷也,諸君能無言乎?”[8](卷六,P99)顧瑛此番感言,后竟成讖語。自此之后,良琦再無出現于雅座中。而顧瑛與其友朋的集會,雖仍堅持了數年,但所吟多類如“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的慷慨悲調。
綜上所述,從至正九年到至正十七年,良琦參加了玉山草堂大部分的雅會活動,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經常首倡賦詩,定題分韻,并撰寫詩序,堪稱是座中的核心之一。
二、釋良琦的詩風與詩藝
黃溍《〈玉山名勝集〉序》曾總結過玉山雅集的詩歌創作:“而凡氣序之推遷,品匯之回薄,陰晴晦明之變化叵測,悉牢籠摹狀于賡唱迭和之頃。雖復體制不同,風格異致,然皆如文繒貝錦,各出機杼,無不純麗瑩縟,酷令人愛。”[8](卷首,P2)玉山文人并非一個嚴格意義的文學流派,僅因著顧瑛的人脈及玉山諸名勝而吸引了一時勝流,他們從未發表過明確的詩學主張,所以詩風異致,各出機杼。但就他們的座中酬贈來看,因處大體相近的情境,風格差略相近。這種風格即黃溍所指出的“純麗瑩縟”。
釋良琦是比較能代表玉山詩風的詩人之一,這主要是因為他長期浸淫玉山,與顧瑛等人往還密切,詩歌大多圍繞玉山名勝和宴集而作。良琦之詩,今所見約115首,其中《玉山名勝集》、《外集》49首,《玉山紀游》15首,《草堂雅集》51首。前二種多為他雅集中的唱和、題詠、分韻之作;后者則是他寓處寺院、山林所作,以題畫(15首)、懷人(12首)、贈答(16首)為主。
從總體上看,良琦的詩很少直接闡釋佛理。但讀《草堂雅集》中的篇什,仍約略可見其僧人的品性,因為他比較擅長通過對景致的描寫以傳達自己的心境和情感,而這種心境是禪僧所特有的。例如《夏日招張師圣文學(二首)》之二:
云深巖寺古,復此涼雨積。樹密聽猿啼,苔深斷人跡。觀理閑慮遠,懷君苦情役。觴酒對幽花,徘徊候山屐。[3](卷十六,P1135)
前四句純寫景物,似無關主旨。實際上詩人通過古寺、涼雨、密樹、啼猿、青苔等意象的描寫,烘托出了自己闃寂悠閑的心境,以此而想到了尚在塵囂中服“苦役”的朋友。再如,《春夜宿海云寺》一詩寫春夜海云寺的清幽的情境:“山閣花霧暝,池館綠陰初。復此涼夜長,禪影流碧疏。素友愜清會,境寂鐘磬余。”[3](卷十六,P1134)表達了詩人的林下隱幽之趣和參禪悟玄的風致,是比較典型的中唐皎然、靈一等詩僧的風格。
“清”無疑是良琦詩風的底色,也是大多僧詩的主導風格。但在這種底色之下,又有不同的審美內蘊。作為古典詩學中的重要范疇,“清”具有廣泛的包容力,可以與其他語匯構成諸多美學內涵不同的復合概念,如“清苦”、“清新”、“清奇”、“清麗”、“清疏”等等。[10]如果說《草堂雅集》中的良琦詩歌尚顯示出“清新”的特征,那么,當他置身于觥籌交錯、笙歌曼妙的玉山筵席之上時,詩風就顯得較為“清麗”,甚至是“綺縟”。③這一點,最為直觀的體現就是他對意象的選擇和描寫。通觀他在玉山所撰之作,以下幾種意象出現的頻率比較高:酒、筵席、歌姬、美人、樓臺、絲竹歌樂、花、簾,等等。
一個身著袈裟的釋子,竟如此迷戀朱簾翠繡、紅粉妓妝、錦瑟鸞笙、酥杯春酒,而很少描寫與之相伴的青燈黃卷、古寺佛像、枯樹蒼藤,這的確頗令人驚訝。古代詩僧大多生活山林、寺院,長年食素,生活清寒,故所作往往顯得“清冷”、“清寒”、“清苦”,甚至有所謂的“蔬筍氣”。錢謙益說:“古人以苾芻喻僧。苾芻,香草也;蔬筍,亦香草之屬也。為僧者不具苾芻之德,不可以為僧;僧之為詩者,不諳蔬筍之味,不可以為詩。”[11](卷四十八《后香觀說書介立旦公詩卷》,P1569)良琦以上詩句,顯然不具備這種特征。胡應麟評元詩時曾說:“其詞太過綺縟而乏老蒼。”[12](外編卷六,P230)我以為,此語移作評良琦之詩,亦十分恰當。
《玉山名勝集》、《外集》、《玉山紀游》還收錄了良琦數首題詠玉山名勝的作品。這些詩歌或非作于筵席,但同樣很難見“蒼老”、“清寒”之格。例如,他題碧梧翠竹堂:
舊種竹梧千尺強,清陰碧色護新堂。高岡晴發朝陽氣,淇水春沾湛露香。玉田瑞液生芝菌,金井回瀾宿鳳皇。何意老騎支遁鶴,與君相對坐云床。(《玉山名勝集》卷三)
表達的雖是幽棲歸隱之志,但碧色、朝陽、湛露、玉田、金井,所造成的決非“清老”、“蒼寒”的風格,而更偏向于“麗”。
良琦在元末詩名甚著,與楊維楨、倪瓚、張雨、顧瑛齊名。陳基有詩贊曰:“羨君方外邁詩流,飛錫相從海上游。”[13](卷七《待琦上人不至》)釋良圭對他亦敬慕有加:“龍門山人、玉山主人以詩名著海內,仆景慕久矣。”并作詩云:“二子風流迥不群,詩名海內每傳聞。苦吟杜甫行日午,覓句湯休坐夜分。”從良琦在雅集中所顯示出的詩藝看,他是當得起這個聲名的。
玉山文人的吟詠,一般有分韻、唱和、聯句、口占、分題賦詩、同題集詠等形式。盡管顧瑛對成員的詩藝并沒有嚴格的要求(例如對分韻韻腳的平仄不作限制,分韻之作甚至出現不同的詩體)[14](P54),但若非才思敏捷、技藝高超,亦不能輕易成就。雅集中就常出現詩人未能卒章而被責罰杯酒的現象。釋良琦僅至正十年七月二十九日,與顧瑛、袁華、于立、王祎等于芝云堂以古樂府分題紀勝未能卒章外,其他均能順利完成。這說明他具備了充分的才華以應付諸種詩題。
良琦在斗才競技中亦不落下風。這里以至正十年五月十八日的雅集為例。是日參加雅集的詩人為顧瑛、于立、釋良琦、吳世顯、李立等,以“炯如流水涵青蘋”,分韻賦詩,詩成者四人,分別是:
于立得“如”字:
愛爾玉山溪上居,厭厭共飲思何如。清飚入夜生金氣,瑤漢經天帶玉除。荷露襲衣涼冉冉,桐陰轉戶月疏疏。偏憐坐客多才思,分得新題取次書。
顧瑛得“流”字:
幽人雅愛玉山好,肯作清酣盡日留。梧竹一庭涼欲雨,池亭五月氣涵秋。月中獨鶴如人立,花外疏螢入幔流。莫笑虎頭癡絕甚,題詩直欲擬湯休。
釋良琦得“涵”字:
月照玉山浮紫嵐,樓臺宛近百花潭。魚鱗屋潤波文動,翠羽簾陰水氣涵。竹外瑤笙時一聽,風前玉麈正多談。瀛洲咫尺群仙在,老客滄洲獨我慚。
吳世顯得“青”字:
玉山月色夜冥冥,人在池亭酒未醒。河漢界天龍氣白,竹梧當檻鳳毛青。露臺翠館來仙子,秋水漁莊動客星。明日草堂塵事少,定將詩句刻云屏。
此次唱酬的題旨應是“飲散步月”。應該說,四人之詩均緊扣“月飲”而設色敷染,未能逸出題旨之外。但如何寫“月”及“月中人”,卻明顯有高下之分。我們先揀出四人寫月的最佳之句:
于 立:瑤漢經天帶玉除。
顧 瑛:月中獨鶴如人立。
良 琦:魚鱗屋潤波文動。
吳世顯:河漢界天龍氣白。
于立、吳世顯都是直接描寫“月”,所用語匯“瑤漢”、“玉除”、“河漢”等,均很常見,未見精警;顧瑛“月中獨鶴”,看似平常,卻勝過前二人,因為它關合了“月”和“人”,其超然塵氛之格,自現筆端。良琦“魚鱗屋潤波文動”一句,用“魚鱗”、“波文”喻月華照瀉下華屋之瓦,雖用了前人之典④,但著“潤”、“動”字,則更覺機趣盎然。雅集分韻、拈韻、次韻,往往要求在較短的時間內完成,詩人們難以充分地發揮創造性的構思和豐富的想象,心智更多地用于如何調動已有的經驗去編排詩作,因此這一類詩往往顯得匠氣十足,雷同者多,精警者少。良琦能寫出“魚鱗屋潤波文動”這樣的詩句,可見其詩思之敏捷不亞于座中其他詩人。再從全詩的構思看,良琦的詩也不同于其他三者。于立、顧瑛、吳世顯的意脈流程大體相近:玉山—飲酒—月色—月下景—賦詩,這顯然是分韻唱和詩的普遍模式。良琦的詩前兩聯亦未出此格,關鍵在末二聯,沒有落入“賦詩”窠臼,而是寫座中之客的飄逸風神,體現極謙和的品格。
當然,良琦的詩并非沒有缺陷,他的問題在于他過多地周旋于酒筵歌席之間,因而缺乏變化,此正如胡應麟評元詩所云“其調過于勻整而寡變幻”,這亦是玉山文人常見的毛病。
三、釋良琦參與雅集的文化意義
僧人與文人集會,淵源有自。東晉元興元年(402)七月,釋慧遠即“延命同志息心貞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15](P211 -214),集于廬山般若臺精舍阿彌陀像前,拈香念佛,以祈往西方凈土,名曰“白蓮社”、“蓮社”。慧遠的蓮社不僅具有宗教的性質,時亦“揮翰”、“文詠”,倡導的是“一種將宗教體悟與文詠之才相結合的創作方向”[16]。此后,類似性質的社團大量涌現,如齊竟陵文宣王之“凈住社”、梁僧廌之“法社”、宋之“西歸蓮社”。不過,這幾個社團,純屬佛教性質的社團,與文學關涉不多。自宋代以來,蓮社的性質有所變化,如釋省常主盟的西湖蓮社,釋云逸主修的吟梅社,“學佛之意味并不顯著,其主旨似在與士大夫交往”[17](P158 -160),實質上都是僧人與文士共同結成的詩社。
玉山雅集,因有釋良琦、釋自恢等三十余名僧人的參與,也具有一定的宗教色彩。顧瑛等人還曾多次悠游寺院,稱“結習未除閑未盡,焚香且對佛前燈”[18](《和繆叔正燈字韻》),甚至一度祝發出家。不過據現存的史料看,顧瑛、良琦們談禪證道、拈香念佛的場景并不多見。玉山雅集更多是征歌選色、山水佳興、吟詠自娛,“文采風流,照映一世”[19](卷一八八“《玉山名勝集》提要”,P1710)。此種情調,猶如為季世文人搭建了一個斗才競藝的舞臺,園池亭榭、美姬醇酒與豪強并起、民生疾苦構成了一副奇特的景觀。因此,對于玉山雅集的評論向來極為復雜,有人認為他們是尋求感官刺激,醉生夢死,失去了儒家文人的常態,彌漫著頹廢放蕩的情緒;而有的人認為,他們放浪形骸,任情自放,恰恰表現了他們藝術至上的進步的精神。這些評價,見仁見智。不管怎樣,玉山雅集中濃厚的享樂色彩是不容否定的。
論者還普遍認為,玉山雅集同時也是元末文人的精神避難所,文人于此并非一味玩賞風月,飲酒品茗,同樣也關注著時局的變化,甚至玉山雅集的興起、繁盛、消歇亦與元末動蕩時局密切相關。這種認識無疑是正確的。不過我們覺得,相較而言,玉山文人并非有著強烈的干預現實的傾向,他們之所以參與雅集,意在拉開與現實的距離。至正十五年之后,顧瑛等人所流露出的憂生嗟世的情緒,乃是基于玉山直接受到兵燹沖擊使然。事實上,從至正八年起,元末動蕩的政局即已見端倪,但在玉山文人那里見不到絲毫的反映,這體現出他們對現實的漠然。玉山文人獨特的品格,就在于他們的放浪形骸,脫然塵囂,無意功名。盡管釋良琦也寫了“避地去年因共難”這樣的詩句,接下的卻是“臨池今日喜同閑”,可見他們是比較容易遺忘現實的。從這個意義上看,以良琦為代表的元末詩僧參與的玉山雅集,不像清初的遺民僧與文人所結詩社那樣具有較明顯的政治色彩[20]。既不關佛事,又非政事,那么,良琦參與玉山雅集文化意義何在呢?我們覺得還當從他們的詩作及活動中去考察。
至正八年二月十九日,良琦在楊維楨首倡雅集之后,攜剡韶至玉山與顧瑛宴集。隨后即寫詩給楊維楨云:
鐵笛倒吹江上去,聞在玉山仙子家。自喜酒船逢賀監,定將玄易授侯巴。露涼冰椀金莖凍,月滿湘簾玉樹花。人生歡樂何可暮,遲爾龍門望太霞。
詩中表達的全是對楊維楨流風雅志的欣羨。楊維楨亦依韻和有兩首,其中有云:“山公酒醉童將馬,禪客詩成女散花。須信西園圖雅集,佛中脫縛有丹霞。”“丹霞”當指宋代著名禪師丹霞子淳,意謂良琦能不拘禪門戒律而參與雅集活動。“禪客詩成”句,則化用良琦在雅集中的詩句。原詩是這樣的:
玉山窈窕集瓊筵,手撥鹍雞十二弦。巢樹老僧狂破戒,散華天女醉談禪。鵝兒色重酴醿酒,桂葉香深
翡翠煙。最愛碧桃歌扇靜,長瓶自煮白云泉。[8](卷二,P19)“散華天女”,典出《維摩經·觀眾生品》:“時,維摩詰室,有一天女,見諸大人聞所說說法,便現其身,即以天華散諸菩薩、大弟子上。華至諸菩薩,即皆墮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墮。一切弟子神力去華,不能令去。”[21](卷中,P115)本是指天女散花以試菩薩和聲聞弟子的道行。此處既形象地描繪出座中琴妓綽約之身姿,亦顯示出良琦等人“醉中談禪”的疏狂與不羈。像這樣琴伎侍坐、童仆治酒的場景,在良琦所參加的雅集中不止一次。
“越國女兒嬌娜娜,蘭陵酒色凈娟娟”,蘭陵美人、小璚英、小瓊華等人綽約、婀娜的風姿,的確為雅集增添幾分旖旎、綺艷的色彩,故良琦直呼此種筵席為“綺席”。
對于良琦而言,當然不會不知道此種行為乖離佛門的戒律,但他又何以要“狂破戒”?我們以為應從兩方面予以解釋。首先,良琦此種破戒之事,與雅集風尚有直接關系。玉山雅集是“詩酒樂舞一體的集會活動”[22](P63),幾乎無會不飲,無人不飲,即便方外僧道亦是如此。例如,至正十年秋仲十九日,釋福初、釋良琦與張翥、顧瑛、鄭元廌、于立等在玉山宴集,“酒半歡甚”,即席以玉山亭館分題;至正十一年十月廿三日,釋寶月與顧瑛、王濡之、袁華等雅集,“酒酣之際”,郯韶、陸仁泛舸而來,顧瑛復呼酒盡歡。可以說,若非善飲之人,怕是難以躋身于雅座當中。
其次,揆諸僧史,飲酒、狎妓、作綺語的僧人亦在在不少。若六朝釋寶月《行路難》諸詩,即大膽而細膩地描寫了女子的情思;隋代沸大《淫泆曲》、釋法宣《愛妾換馬》、《和趙郡王觀妓應教》,更語含猥褻;宋僧仲殊、慧洪等不僅撰艷詞,甚至還親身踐履,飲酒狎妓,納室同居。對于此類僧人的言行,人們的評價往往莫衷一是:批評者或斥之為不守僧規的窳敗之徒,回護者則從人性角度為之開脫。出現此種涇渭分明的評判,根源在于佛教本身即提供了不同的理據。佛教向來是以戒律精嚴著稱,指定了諸如“五戒”、“八戒”、“十戒”乃至“三百四十八戒”,目的即令僧人止惡從善,摒棄欲望,潔凈身心。但另一方面,佛門也倡導一種似乎相反的觀念,不僅捐棄僧規戒律,甚至還鼓勵僧人放情縱欲。《維摩詰經·佛道品》云:“火中生蓮花,是可謂希有;在欲而行禪,希有亦如是。”[21](卷中,P134)《圓覺經》亦云:“一切障礙即究竟覺……智慧愚癡通為般若,菩薩外道所成就法同是菩提,無明真如無異境界,諸戒定慧及淫怒癡俱是梵行……”[23](P56)此種修行觀念,在大乘佛教特別是南宗禪盛行的時代更得以充分發揮。例如,宋代真凈克文云:“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豬頭,口誦凈戒。趁出淫坊,未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24](P2-3)在佛禪看來,“精持戒律”和“在欲行禪”,實際僅是“外相”,與“真如境界”、“正法眼藏”并無直接關系;若不著此“外相”,虛空自在,色相俱泯,“紅粉佳人”又何嘗不是觸發上上機的“法門”?然而,佛門確有一些不法之徒為放情縱欲,資為理據,為己開脫。
釋良琦飲酒、狎姬、作綺語諸行,是否“具正法眼”呢?因其未留存佛學著作,亦未見他被尊宿印可的材料,故難以遽然論斷。只能從他的詩作略予分析,例如以下這首:
片玉山西境絕偏,秋華亭子最清妍。三峰秀割昆侖石,一沼深通渤海淵。鸚鵡隔窗留客語,芙蓉映水使人憐。桂叢舊賦淮南隱,雪夜常回剡曲船。北海樽中長瀲滟,東山席上有嬋娟。紫薇花照銀瓶酒,玉樹人調錦瑟弦。醉過竹間風乍起,吟成梧下月初懸。一聲白鶴隨歸佩,何處重尋小有天?
此詩撰于至正十年七月六日,時顧瑛“置酒小東山秋華亭上,歌舞少間,群姬狎坐庭中”。全詩主要描繪秋華亭之景,僅第六、七兩聯描寫聲色,但未含輕薄、猥褻之意,反而措辭清雅,與聲色之徒自不可同論。谷春俠曾考證,玉山雅座中的女子多為顧瑛的侍妾,少有妓女,而且氣質典雅,多才多藝,非世俗的佐酒歌妓所及。[22](P67 -68)據此而看,良琦應非一般“浪子和尚”。他迷戀玉山筵席者,主要是清幽的園林、脫俗的人物、雅致的珍玩,而非縱情恣欲。
值得一提的是,在釋良琦的所有詩作,他提及最多的古人不是高僧大德,而是唐人賀知章。例如:“明朝定醉山中酒,去脫賀公頭上巾”;“自喜酒船逢賀監,定將玄易授侯巴”;“賀老狂猶在,袁安瘦不禁”;“雪霽春水動,初回賀監舟”;“也知賀監風流在,不似王猷雪后來”;“風流賀監應相見,醉岸烏紗一解顏”等等。賀知章,自號“四明狂人”,倜儻不羈,而這正是良琦尊崇他的原因。玉山文人向來以“怪”、“迂”、“癖”、“狂”著稱,大多與世不諧,放浪形骸。釋良琦不顧僧戒,縱情詩酒,不僅體現了此一文人群體的特色,而且可稱得上是元末“狂禪”的代表,反映了佛教世俗化進程日益加劇的趨勢。
注釋:
①學術界關于玉山雅集的研究成果,可參看谷春俠《元末玉山雅集研究綜述》(《昆明理工大學學報》2007年第4期)。
②即至正八年二月十九日顧瑛、楊維楨、姚文奐、郯韶、李立、張渥、于立等人在玉山的雅集唱和活動,張渥繪有《桃源雅集圖》,楊維楨撰有《雅集志》,是為玉山雅集之始。
③曾瑩《文人雅集與詩歌風尚研究——從玉山雅集看元末詩風的衍變》(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11頁)亦指出,在玉山筵席之上的良琦詩風,與寓處山林寺院之作有著明顯的區別,“不免沾染上了一些世俗的氣息”,顯示出綺縟的特征。
④屈原《九歌》有“魚鱗屋兮龍堂”句。庾信《溫湯碑》有“秦王余石仍為雁齒之階,漢武舊陶即用魚鱗之瓦”句。韓維《答和叔城東尋春》云:“仰視孤剎起,突兀疑神扶。其下萬華屋,碧瓦魚鱗鋪。”
[1](明)何良俊.何氏語林[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04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明)李日華.六研齋三筆[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86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3](元)顧瑛.草堂雅集[M].楊鐮,祁學明,張頤青,整理.北京:中華書局,2008.
[4](清)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匯考[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827 -82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5](元)楊維楨.東維子集[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22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6](元)釋來復.澹游集[M].續修四庫全書本(第162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7](元)釋大?.蒲室集[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20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8](元)顧瑛.玉山名勝集[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36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9](元)袁華.玉山紀游[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36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0]蔣寅.古典詩學中“清”的概念[J].中國社會科學,2001,(1).
[11](清)錢謙益.錢牧齋全集(第6冊)[M].錢曾,錢仲聯,標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2](明)胡應麟.詩藪[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3](元)陳基.夷白齋稿[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22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4]曾瑩.文人雅集與詩歌風尚研究——從玉山雅集看元末詩風的衍變[M].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15](梁)慧皎.高僧傳[M].湯用彤,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
[16]曹虹.慧遠與廬山文學社團[J].文學遺產,2001,(6).
[17]歐陽光.宋元詩社研究叢稿[M].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18](元)顧瑛.玉山璞稿[M].楊鐮,整理.北京:中華書局,2008.
[19](清)永瑢.四庫全書總目[M].北京:中華書局,1996.
[20]李舜臣.清初嶺南詩僧結社考論[A].人文論叢(2005年卷)[C].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
[21]維摩詰經[M].賴永海,高永旺,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0.
[22]谷春俠.玉山雅集研究[D].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2008.
[23]圓覺經[M].徐敏,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0.
[24]陳自力.釋慧洪研究[M].北京:中華書局,2005.